2024年2月21日发(作者:野色)

第39卷第5期Vo.l39No.5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ZHENGZHOUUNIVERSITY2006年9月Sep.2006《全辽文》与辽代佛教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全辽文》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看,其中完全或者主要是关于佛教内容的共有259篇,占其总数的23%。这些内容既涉及到帝王后妃,也涉及到平民百姓,其中还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千人邑活动的记载,为研究辽代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还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佛教主要为密教,信徒普遍诵持陀罗尼真言,《全辽文》中为数众多的经幢记、塔铭、墓志铭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关键词:《全辽文》;辽代佛教;文学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5-0028-04清末缪荃孙辑《辽文存》和王仁俊辑《辽文萃》,有辽一代文章搜罗已广,陈衍《全辽文》之编,内容更全。近年山西大学阎凤梧等先生重新汇辑辽代遗文,共得辽代作者228人、文810篇,比《全辽文》增收作者7人、文14篇[1](上),为学界深入研究辽代文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全面更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辽代的文章十之八九皆为帝王诏册、大臣奏议和文士们日常生活中创作的序跋碑铭题记之类。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大多质朴无华、实用性强,质实有余而文采不足,除了在应用文的骈俪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地位外,似无足多称。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这些文章作为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史料来看待,我们就会发现其特殊的价值。昔陈垣先生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云: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大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荃孙)、王(仁俊)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2]然陈氏当日所据辽文既有不全,其所论之目的又本不在辽代佛教。今乃袭陈氏之故技,依阎凤梧等重辑之《全辽金文》辽代部分,以对辽代佛教的显著特点有所论列。正如刘勰著《文心雕龙》时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①则早已对之有较专深的探讨,不仅镰田茂雄等人的中国佛教通史著作有专章讨论,而且还早就出现了野上俊静、胁谷神尾一春等人论辽代或辽金佛教文化谦、的专门著作。不过,从《全辽文》等现存文献来看,他们的观点有些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辽代佛教的兴盛,前人一般举辽朝帝王如太祖、圣宗、兴宗、道宗等实行崇佛政策为例以说明之。因为帝王的提倡与奖掖,无疑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兴盛标志。但从《全辽文》来看,辽代佛教的兴盛,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首先,现存辽代文章中出自佛教僧侣之手或内容关于佛教者占了绝大多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很能看出当时佛教兴盛之一斑。新编《全辽文》中共收录辽代作者228人(无名氏视为1人),而在这些作者和作品中,佛教僧侣作者达35人,篇题有佛或释等字样以及内容明显是关于佛教的作品,即有259篇,分别占到《全辽文》作者总数的16%和作品总数的32%。这个数字,比唐代僧诗在全唐诗中占约28%的比例还要高,可见当时佛教已深入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人们动笔用墨时不得不与佛教相联。其次,从《全辽文》中的碑铭或哀册文章来看,当时社会信佛或出家者非常普遍。辽代的各朝帝王崇佛已见于《辽史》,帝后王妃之信佛,则唯知辽景宗耶律贤的睿知皇后萧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3],其它则不得而知。而辽代文章却可在一②1对于辽代佛教的研究,国内的学者涉及者不少,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得见。而日本的学者收稿日期:2005-04-25作者简介:高华平(1962-),男,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①本文所谓的《全辽文》是指阎凤梧所辑《全辽金文》的上部《全辽文》。②关于唐代僧诗在全唐诗中的比例,参见拙作《唐代的诗僧与僧诗》一文,待刊。28
定程度上补充这方面记载的不足。如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钦哀皇后萧氏,史无明文考知其与佛教的关系,但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之墓的《圣宗钦哀皇后哀册》称萧氏: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可知萧氏必同辽圣宗耶律隆绪一样笃信佛教。又如兴宗耶律宗真的仁懿皇后萧氏,耶律孝杰的《仁懿皇后哀册》曰: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即中宫而居永乐宫迨五十霜。可见其亦应是信崇释氏的。再如辽代最著名的女诗人、道宗的宣懿皇后萧观音,《辽史宗室传》说她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她的名字萧观音似乎已显示出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因为根据《辽史礼志》记载:辽太祖曾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而《全辽文》所录无名氏撰《萧孝忠墓志》即载当时民间也有生女取名观音、天王的;而当时的寺庙又常修观音菩萨像、大德亦常诵《观音》《弥陀》等经①,足见辽代佛教观音信仰的普遍。但萧观音本人是否信佛,则并无确证。而《全辽文》可提供这方面的线索。辽天祚帝乾统元年(公元1107年)张琳撰《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曰:(萧观音)文章非学至之然,佛法本生知之性。静修蘋藻,动节珩璜。仪形祖祢,轨范嫔嫱。这说明萧观音不仅进入皇宫后与其公公、夫婿一样崇佛,而且其佛教信仰是自幼以来早就建立了的。而这种佛教信仰与其诗歌创作之间,应该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再次,从《全辽文》来看,辽代佛教的兴盛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当时民众信奉佛教的众多、虔诚和普遍上,当时的情形真可谓室室有出家之人,处处闻念佛之声。《全辽文》因多应用性文体,故其中所录碑铭类作品有相当分量。而由于这些碑铭类作品必记传主生平、爵里、先祖子嗣,故常常能从此类文章中透露出其宗族的佛教信仰状况:郝云《韩瑜墓志铭》:长女喜佛,早亡。杨佶《秦晋国大长公主墓铭并序》:诸孙在旁,恻恻恳褥。焚香祝天边佛,设供饭无边僧。王泽《王泽妻李氏墓志铭并序》:夫人慈爱宜纯植性习之愿,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惟切于诵口。有三女:长法微,出家,受具戒,讲传经律;次适三班判官郑涛;次崇辩,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王纲《王泽墓志铭并序》略同)王言敷《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仍复自备净食,时为斋设,诱之趣善,饶益颇多。至于居常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韩诜《董痒妻张氏墓志铭并序》:孙女五:省哥,落发为尼。龚谊《大辽保安军节度使邓君墓志铭并序》:女子四人:长适进士安曼期,次为比丘尼释了洙《悟空大德塔铭并序》:载三十六岁,嫠居。誓不再嫁,训毓诸孤为沙弥。士大夫妻有嫠居者,感而慕道者数人。李忠盖《惠州李祜墓幢记》:偶妻李氏,所育三男:长男业经,沙门僧元才无名氏《董承德妻郭氏墓记》:孙女三:尼圆朗、弓哥、寿哥。无名氏《郑士安遗行铭记》:女三人:长任郎妇,次马郎妇,次故尼圆融。无名氏《李内贞墓志》:次二女:尼归敬、归运,并于敬善寺出家。无名氏《史洵直墓志铭》:孙男三:次曰禄孙,出家,法名行敷,礼西京石佛院诠正大师。这里所引的尚只是《全辽文》墓志铭中的部分材料,其他见于塔铭、经幢记的材料亦复不少,此不一一征引。然仅此已可见当时民众信奉佛教的概况。当然,能说明辽代民间奉佛的普遍和佛教兴盛面貌的,还有关于当时民间普遍组建的名为千人邑的信众社团。日人镰田茂雄在其《简明中国佛教史》中曾说:辽的佛教还渗透到民众之中,产生了千人邑会。千人邑会分隶于各个寺院,由寺主担任领导,一般以在家信徒为会员,会员有一定的施财义务。[4]从《全辽文》中的文献来看,有14篇内容涉及千人邑的情况②,除王正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详细记叙了结千人邑的目的之外,更多的都只是部分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李仲宣《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云:其邑人姓名,俱列碑阴。释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曰结千人邑等。但即使是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对镰田茂雄的旧说也有补充和完善的必要:参见《全辽文》中的《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刘成,P114)、《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李检,P630)。②《全辽文》涉及千人邑的14篇篇目是:释志愿的《葬舍利佛牙石厘记》、王正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李仲宣《祜唐寺创建讲堂碑》、释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王实《石龟山遵化寺碑并序》、释行阐《义丰县卧如院碑记》、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释行鲜《涿州云居寺供灯塔邑记》、宋璋《广济寺供殿记》、无名氏《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无名氏《双城县时家寨净居院舍利塔记》、无名氏《释伽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无名氏《建塔题记》、无名氏《獾州西会龙山碑名》等。①29
30
参考文献[1]阎凤梧.金辽全文:上(全辽文)[Z].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2]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A].明季缜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下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宋会要辑稿蕃夷[Z].北京:中华书局,1957.[4]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汉语大字典:一[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上[Z].北京:中华书局,2000.(责任编辑陈朝云)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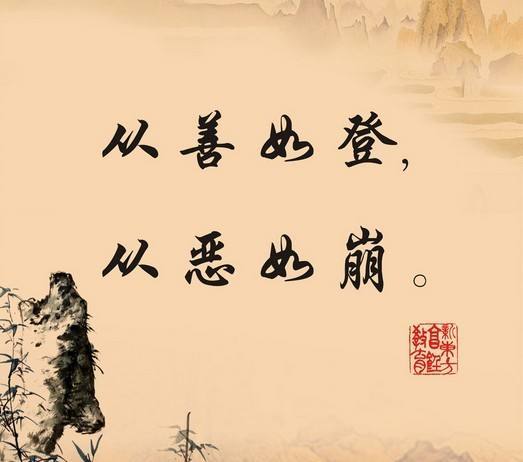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4-02-21 12:06:40,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848840027108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全辽文与辽代佛教.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全辽文与辽代佛教.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