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郴字怎么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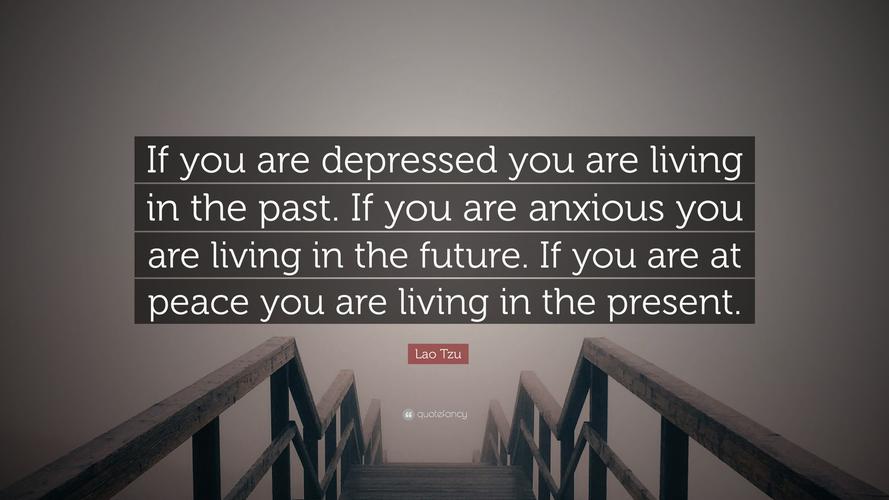
简述《汉书.艺文志》的六种分类
《汉志·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节其要而成,而《七略》又是在《别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别录》是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开始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整理群书的产物。这次整理群书,集中了当时有代表性的一大批学者。《别录》《七略》是这次校书的理论总结,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所以《汉志·艺文志》的文学思想,实际是西汉后期代表性的文学思想。
《汉志·艺文志》体现的文学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诗赋不同于经学,也与学术文章有别。从内容上讲,它是贤人失志、离谗忧国的情志抒发;从体制上说,则以有韵为其特点。
《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略又分若干小类。“六艺”本来是先秦贵族教育的六门课,孔子讲的“六艺”既是六门课,也是六种书。《六艺略》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础理论。《诸子略》从学术源渊和思想体系上来分,是对《庄子·天下篇》以来前人研究诸子百家的总结。《诗赋略》以文体来分类。《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是以内容和作用来分类的。
阮孝绪《七录序》云:“《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章学诚亦本是说,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说:“诗赋本《诗经》支系。”
现代学者多从其说。如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就说:“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则诗赋本当附入六艺诗家,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其所以自为一略者,以其篇卷过多,嫌于末大于本,故不得已而析出。”但“六艺略”中的诗类,都是有关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四家说《诗》,主要立足点是“王者之教化”,“把《三百篇》作了政治课本”(闻一多《匡斋尺牍》之六)。如果把“诗赋略”并入“诗类”,不仅篇数多寡悬殊,有喧宾夺主之感,更严重的是内容扞格难入。所以,“诗赋略”独立一项,这是基于对“诗赋”独立特点认识,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汉人的文学观念:文学既独立于经学,也与其它学术性应用性的文章有别。
“六艺”典籍的来源是官书旧典和贵族教育,这些书作者无定,一般只能有整理者。“诸子”则是私家著作。“六艺”谈一般原理,“诸子”谈一家之言,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战国后期,荀子、屈原等离谗忧国,吐为哀怨之词。“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汉书·艺文志》总序),与六艺诸子的区别更为明显,文学类创作与学术类著作遂判然二别。这种分别的是从性质上着眼的,不是从形式上入手的。清人刘天惠《海学堂初集》卷七《文笔考》说:
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数术,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数术、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
刘师培《论文杂记》也对此有说明:“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列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郭绍虞指出:“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了。”[1]郭先生还举了《汉书》中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的例证。
还要说明的是,西汉时“赋”所包含的作品种类,要比后世的赋包含的种类多。像《汉书·韦贤传》所录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等,在《汉志》中应当归于哪一类?这些诗在体制上同《诗经》完全一样,但却不是说《诗》的,自然不能归入“六艺略”的“诗”类;而一般人可能首先想到“歌诗”类,但这些诗显然是不入乐的,归入“歌诗”类,不合体例。我认为,刘班是把它们归入赋类的,因为它们虽然不能歌,但可以诵。《汉志》是将“诵诗”隶于赋类的。再比如,汉代有数量相当多的“颂”,著名者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有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马融的《广成颂》、《东巡颂》、《南巡颂》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的赋体。而东方朔的《旱颂》、王褒的《碧鸡颂》则是调侃性质的俗赋。其他像赞(如司马相如的《荆轲赞》、刘向的《列女传赞》)、铭(如东方朔的《宝瓮铭》、刘向的《熏炉铭》、崔骃的《扇铭》、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及众多的镜铭)、箴(如扬雄的《十二州箴》《上林苑令箴》《酒箴》、崔瑗《东观箴》《灌堤谒者箴》、崔琦《外戚箴》)等,都是归入赋类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曰:“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
第二,诗赋分类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
《诗赋略》分五家,第一家为屈原赋,下隶赋家20人,赋361篇;第二家为陆贾赋,下隶赋家21人,赋274篇;第三类荀卿赋,下隶赋家25人,赋136篇;第四类杂赋12家,赋233篇。第五家为歌诗类,下隶28家,诗34篇。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体制为序,无作者姓名。歌诗类作品也以无作者姓名者居多。
这个分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前四家为“赋类”,后一家是“歌诗类”,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才是将赋分为四家。但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又有交叉现象:前三家是文人创作,是口诵文学的书面化,“杂赋”和“歌诗”更具有口诵文学的性质,“杂赋”最后的“成相杂辞”“隐书”更为接近“歌诗”;文人赋——杂赋——歌诗,这是一个 “诵唱”因素渐次强化的过程。
《诗赋略叙》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对赋的特点的说明,也是《汉志》判断赋的标准。“传曰”云云,只不过表示有所本且本于儒学而已。“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是对诗的特点的说明。很清楚,刘、班所谓诗赋,主要就其传播方式来把握:赋“诵”而诗“歌”。正如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是有别于日常语言的音乐化的“乐语”。文学是在同音乐相分离的过程中独立出来的,诗赋便是这种独立的标志。“乐语”最基本的方式是歌唱和讲诵。歌唱对于语言简明性的要求,讲诵对于语言华丽性的要求,使传播方式的区别转化为表达方式和文体的区别,于是就有了诗和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
第三,抒发感情与描绘客观事物是诗赋的主要职责。
按照《汉志》的体例,六略前有总叙,所别每类之后又有小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叙例来了解刘、班分类的标准及其思想。但《诗赋略》仅有总叙而无小叙。这给我们探求刘、班的文学思想造成了很大困难。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云:“《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又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则认为《诗赋略》本无叙例,他说:“诗赋各分以体,无大义例,故《录》《略》不为小序,而班氏因之,不尽由于疏漏也。”不管由于佚失还是本来就没有写成,而《诗赋略》的分类依据却成了许多学人讨论的课题。
章学诚认为《汉志》所列诸赋,各有宗旨,前三类为一个标准,可比拟诸子。杂赋为一标准,为总集之类(此本胡应麟说)。姚振宗基本同意章学诚之说,他说:“《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刘师培从文学表达方式上分析三类赋的特点,认为前三类分别是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章炳麟的说法与刘氏相近,认为屈原赋言情,孙卿赋效物,陆贾赋是纵横之变[2]。章学诚认为所列赋家,各有宗旨,却未能进一步深究其宗旨所在,而且下文以“不可考”概括之,则说明其宗旨也难以深究。刘师培和章太炎从表述方式上分,抓住了文学不同于诸子的特点。过去探讨古代文学思想,从古代的文学理论方面探讨的多,而
从古代的文学作品挖掘的较少。刘师培和章太炎能从汉赋本身的特点分析刘、班诗赋分类的理论,因而很有启发意义。
诗赋的抒情性,从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以来,文人多有论及。司马迁在刘安《离骚传》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屈原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有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就是抒发忧愁。汉代诸多楚辞体赋作,都是以屈原口吻抒发忧愁幽思。王褒《洞箫赋》写道:“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刘向《九叹》也写道:“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外彷徨而游览兮,内恻隐而含哀。聊须臾以时忘兮,心渐渐其烦错。原假簧以舒忧兮,志纡郁其难释。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於《九章》。”论者或以为是模仿屈原的口气的无病呻吟。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赋家的身世遭遇,就会觉得大多数作品未必如此。刘歆在《七略》里明确总结:“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至于赋的描写特征,从司马相如“赋迹”、“赋心”的理论,直到班固的《两都赋序》都有很好的说明,这是当时学人的共识。
第四,关心国是、干预政治是对赋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
从表现手法上分析《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思想,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用此标准具体分析各类赋作,就会发现很多扞格难通处。因为即使同一作家的作品,也可以有不同的体裁和表达方式。如扬雄之《反离骚》、《广骚》、《畔牢骚》三篇,今皆在本传,乃抒
情者,而《汉志》归入“骋辞赋”类;屈原有《橘颂》、王褒有《洞箫赋》,皆效物者也,而《汉志》归入“言情类”。 冯商有《镫赋》,亦“效物者”,而归入“骋辞类”;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本抒情者也,而《汉志》归入“骋辞类”。枚皋实滑稽之雄,其赋嫚戏不可读,而归入骋辞之陆贾赋,也不恰当。《诗赋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分类,而是以人为纲的分类。由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使用多种文体和多种表现手法,所以以人为纲的分类本身就存在文体上和表现手法上的相互交错现象。那么,《诗赋略》赋分四家,应当还体现刘、班另外的文学思想。
汉人对赋的价值的评说,集中在“讽谏”这一点上。司马迁以“风谏”评判司马相如赋的价值,扬雄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词人之赋”,他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3]。所谓“则”,就是有“讽谏”的作用。刘向把屈原赋、荀况赋与《诗经》相比较,充分肯定其讽谕之义的价值,并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没其讽谕之义”。班固的《两都赋序》明确提出赋的使命和价值就是对政治得失进行颂扬或讽谕,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进忠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总之,汉代赋论家或者就赋有无讽谏用意而判断它的价值,或者就读者没有接受讽谏而指责汉赋没有讽谏效果,从而怀疑汉赋的价值。
汉代人不仅以“讽谏”作为评赋的标准,而且当作写赋的准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赋家在诸子中的类属得到证明。《汉书·艺文志》中,汉代人在“诗赋略”列名,又在“诸子略”列名的,共有十家;这十家中,列名儒家的有九家,列名杂家的一家。范晔《后汉书》没有《艺文志》,清人钱大昭、侯康、顾櫰三、姚振宗、曾朴五家有《补后汉书艺文志》,但他们的补志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没有赋家专略。我们按照严可均《全
后汉文》,将留有赋作的人,对照《补志》(以姚振宗所著为主)子部,其中有19人留有赋且在子部有名,这19人中,属于儒家者有16人之多。汉代赋家几乎皆入儒家,说明当时赋家作赋确实是以儒家的讽谕思想为主导的,这一点与汉代人对赋的评论标准是一致的。
所以,汉代学术界创作赋、评价赋的主要标准是“讽谕”,那么作为集当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七略》和《汉志》把赋分为四类,其标准也当与之相通。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正因为屈原的辞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故《七略》列屈原赋为第一。屈原赋以下二十家,大概是《楚辞》的雏形。考《楚辞章句》所录凡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九家,今《汉志》屈原赋二十家中不见景差、东方朔,其馀七家皆有之。当然《汉志》以人为纲,凡此人的赋作,全部著录,而《楚辞》则为别裁精选,故只能说“屈原赋”类是《楚辞》的雏形。姚振宗《汉志拾补》认为屈原赋类“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分为第一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汉志》列“陆贾赋”以下二十一家赋为第二类。这二十一家中,只有扬雄的赋保存了下来,其馀都散佚不传。扬雄的赋,尤其是《七略》所录的四篇[4],模仿同乡司马相如的赋作,靡丽之赋,劝百讽一,驰郑卫之声,曲终奏雅,《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所以他晚年很后诲,辍不复为。
这类赋以陆贾为首,陆贾的赋虽然没有传下来,但据《史记·陆贾传》,陆氏本为纵横策士。建国后,他曾两使南越,俱为太中大夫。《文心雕龙·才略》:“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是陆贾赋以“辩富”著称。刘师培《论文杂记》云:“陆贾为说客,为纵横家之流,则其赋必为骋词之赋。”从今存《新语》十二篇看,陆贾文章,概具赋体,如第七篇《资质》的首段,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如不通观全篇,极易疑其为写物之赋。所以王利器说:“陆贾赋今不可得见矣,读《新语》之文,不翅尝鼎一脔矣。”[5]
这类赋家中的朱建、枚皋、严助、朱买臣等,皆工于言语,这些纵横口便之人,在汉代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弃其所长,投合君王的趣味,将以前游说君王的政论,改为耸动君王的文辞;将侈陈形势的口论,变为铺采摛文的赋篇。“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于是风谏之旨日益稀矣。
《诗赋略叙》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则刘、班以为荀、屈赋在有恻隐之义这点上是相同的,那么何以分而为二呢?荀卿赋以下25家,除荀子赋外,其馀皆亡。而荀子的这些赋篇[6],《佹诗》与屈赋相近外,其馀诸篇,格调迥异。究其内容,基本上是儒家言,训戒的意味很浓,风格颇类古代的箴铭,其中所缺乏的正是屈赋中那种澎湃激情。屈子言情,荀赋效物阐理。
杂赋一类,共录12家233篇赋作,但不幸的是,没有一篇保存下来。综合前人的研究,这类赋,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7]。
《诗赋略》分赋为四家,内容上以《诗经》为对照物,看其“讽谏”教化之旨的多少。“屈原赋”是刘向编辑的《楚辞》的雏形,这类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陆贾赋”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类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为一类。《杂赋》一类,《诗》人之讽谏之义微乎其微。
最后要说明的是,近若干年来,一些学者强调:所谓文学思想,主要是在文学理论或文学创作中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一种感悟。而自我生命意识,主要是脱离政教的个人情感。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学精神的否定。因为中国文学中的风谏传统,说到底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学术界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魏晋说,二是西汉说,三为先秦说[8]。我认为,不管是哪个时期自觉的,但以为自觉了的“文学”就是“为艺术而艺术”[9],就是抛弃政教内容,都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一旦获得独立主体的地位后,政教仍是其主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注: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2]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按指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之不能尽归一例耳。”“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以前三类为一标准,后一类为另一标
准。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他重申说:“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论屈原赋类说:“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为第一篇。”论陆贾赋类说:“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故区为第二篇。”论孙卿赋类说:“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故区为第三篇。”论客主赋类说:“此十二家大抵皆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馀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
章炳麟《国故论衡·辩诗》:“《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3] 见《法言·吾子》。时下的文学批评论著多认为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是指屈原等的作品,“词人之赋”是指司马相如等的赋作,恐怕有问题。扬雄在同篇中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明确表示司马相如的赋作是“丽以则”的。我以为,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大致相当于《诗赋略》中前三类赋,“词人之赋”大致相当于《诗赋略》中的“杂赋”。扬雄说:“或问:景差、唐勒、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或据此认为景差等人的赋是“词人之赋”,但“必也淫”一句是有问题的,汪荣宝《法言义疏》已有详细辨证;于省吾先生《双剑誃诸子新证·法言新证》曰:“此文本作‘必也淫二则二奈何’。应读作:‘必也淫、则,淫、则奈何?’下‘淫则’下承上‘淫则’而言。上‘则’字即涉重文而脱。”据此,则扬雄认为景差等人的赋是虽有淫词但尚有法则,即存讽谏之义。
[4] 《诗赋略》著录“扬雄赋十二篇”,最后“左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班氏注云:“入扬雄八篇”。顾实说:“盖《七略》据雄传,言作四赋,止收《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四篇,班氏更益八篇,故云十二篇也。其八篇,则本传《反离骚》、《广骚》、《畔牢骚》三篇,《古文苑》《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三篇,又有《覈灵赋》、《都酒赋》二篇,凡八篇。”
[5]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新编诸子集成”版第107页。
[6] 《诗赋略》著录“孙卿赋十篇”,顾实说:“十篇盖十一篇之误。《荀子》有《赋篇》、《成相篇》,成相亦赋之流也。《赋篇》有《礼》、《知》、《云》、《蚕》、《箴》五赋,又有《佹诗》一篇,凡六篇。《成相篇》分五篇,合《赋篇》之六篇,实十一篇。”按,《成相篇》的分章,古来就有不同意见,或分三章,或分四章,顾氏本王先谦《荀子集解》之说,分为五篇,以足《汉志》十篇之数,并以为《汉志》“十”为“十一”之误,此亦臆说者,难以令人信服。但荀赋的主要内容如顾氏所述,则是可信的。
[7] 参见拙作《<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文学遗产》2002年6期)、《<汉书·艺文志>“杂赋”考》(《文献》2003年2期)
[8]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于1920年在日本杂志《艺文》上发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论》中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
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说:“汉赋是文学自觉的第一声春雷。”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2期)说:“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赵逵夫先生《拭目重观,气象壮阔》(《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中指出:“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是在先秦时代。从创作方面来说,这种自觉从西周末年召伯虎、尹吉甫等人的创作已经开始。综合地来看,到屈原时代,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还是文本意识上,都已经达到自觉。”
[9]鲁迅文章多次提到“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全都是持批评的态度或讽刺的语气。

本文发布于:2024-02-20 14:46:5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841161914548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简述《汉书.艺文志》的六种分类.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简述《汉书.艺文志》的六种分类.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