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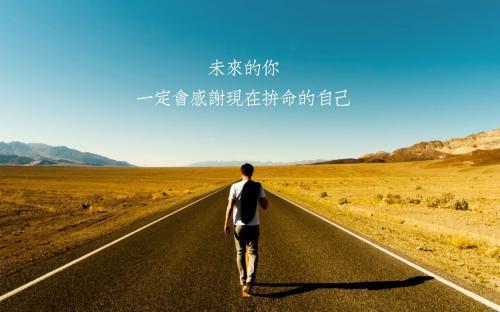
窑洞,学府
一堵崖面,三只窑洞,就是学校所有建筑;一个老师,二十几个学生,就是全体师生员工;一片废铁悬挂于老师办公室(边窑一)前的木桩上,一根铁勺柄被一根细麻绳吊在木桩的另一侧,“当当当”上课,“当当”下课,“当当当当当……”集合,老师就用这个最简陋的设备发号施令,它也就成了学校的象征;教室(主窑)有上下相叠而开的小窗、中窗、大窗,一则为了采光,二则是为了显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普通农户乃瓮牖绳枢之家,是没有能力在一孔窑洞开这么大的三口窗且用木头做窗框,用玻璃挡西北风的。土坯上支几页木板,就是桌子,麦草袋子压在屁股下就不能叫草包,该改口叫凳子,至于那一面被人字木架支起的用墨锭染得黑一道白一道,或者说黑里泛白木板,当然就是黑板了。另一孔窑洞是师生灶,它和农户的灶房几乎一样,只不过陈设更为简陋,一担木桶,一口水缸,一个小案板,直径不到一尺的黑锅,一只碗,一双筷子,如果你是被别人蒙了眼送到这间灶房,你肯定会根据这些家当判定是到了一家光棍的厨房里,子孙满堂是和这间屋子联系不起来的,更不敢想象它就是师生灶。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村学,是我学习点横竖撇捺,认识加减乘除的小学,它简陋得如同掩映在杂草丛中的乡村戏台,锣鼓不响,演员不登场,是没有人会想到它的存在的。可我把它不叫学校,更不叫窑洞,而把它叫做“学府”。冠以如此美誉,不是因为它有多少尖端科研项目,而是因为它传承的气息,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我的呼吸不止,它的味道不减。
太阳比较古板,按时东升西落,不会因为孩子们需要看书,多在天空停留一两个时辰,点灯又没有油,明亮的电灯泡还亮在收音机的新闻里,我们只能从大人们“亮得地上掉一根针,晚上都能看得见”的言谈中揣摩电的神圣。这就省去了早晚自习,在家里我们也不用趴在灯下抄写,正好帮家里做些零活。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劳动最幸福,劳动最光荣……如果说黄土高原是流水反复冲出了沟壑,那老师在我们的小脑袋里反反复复地刻出了“劳动”二字。早晨我们迎着朝阳高唱“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下午我们用“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要学喜鹊盖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送走天边的云彩。每学期通家书上,总有一句“督促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醒家长,操行评语栏里少不了在校劳动中的表现,我们都交换着看对方的通家书上是否填了“热爱劳动”四个字,少了那四个字,如果不哭个眼圈发红,也得耷拉着个脑袋好几天,像偷了人家的东西。不要以为那时候的学校劳动不过是打扫卫生而已,爱劳动与否都是老师凭印象打分,其实那时我们到三四里远的沟里抬水是每天必上的劳动课,学校有勤工俭学基地,十几亩平地,抬水浇树、种菜,拔草,耘土,割荞麦,扳苞谷,挖洋芋,打柴……这些劳作都很容易称量出你对劳动的态度。在家里偷懒,大人们总用“小心我告诉你老师”或者“再指使不动我就在通家书上写„假期劳动不积极‟”来吓唬我们,这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管用的一招。我们的童年,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要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成绩,首先就要大书特书“劳动竞赛”,“劳动竞赛”的种子在父辈的心田里开花,结果后,又不失时机的播撒在了我们心窝里,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吃苦耐劳,那时的劳动教育,功不可没。
光线不足造成的最大障碍在冬季。鸡叫头遍,就得摸着起床,最迟到鸡叫三遍就得摸着赶十多里山路,坑坑洼洼,一颠一颠地往前揣摩,加之黑乎乎鬼影一般的山峦、树木和猫头鹰、狐狸的凄惨的叫声,早使我们小小的心脏咚咚的跳,一个村里的孩子要一块走,大孩子要领着小孩子,这是生活的逼迫,也是老师的教导,更是班里的纪律,哪一路的小孩子因为害怕不能按时到校,这一路的大哥大姐首先要挨批。关爱他人,扶弱济困成了老师考察学生品行的第一项内容。到教室里还是黑乎乎的,看书写字是不行的,我们就放开喉咙唱歌,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我爱北京天安门》《学习雷锋好榜样》《绣金匾》《乌苏里船歌》《南泥湾》……虽然跑调,但把积极向上爱国爱民的激情唱了出来,现在时过境迁,给我们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我们很容易接受,因为那时就已经设置好了频道,现在一有同步信号,就会马上产生共振。唱困了,就轮流讲故事,讲《小白菜》《豆皮豆瓤》《狐狸精精》《白蛇传》《天仙配》《三结义》《下河东》……爷爷奶奶讲给的故事都可以拿出来露一手,小人书看到的情节都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老师和同学除了仔细听讲外,笑声和掌声是少不了的,叙述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潜生暗长在这朦胧的黎明中。故事讲完了,就得背课文,背不下去,有人领着背诵,背熟了就抢着到黑板前单独背诵,老师打分,同学评议,由于反复强化,背诵过的篇目至今记忆犹新,前天儿子翻出我的旧课本,看见课文的题目旁边老师用蘸笔写了六七个“背”字,愕然,追问何故,我说一篇课文老师最少要分期盯背六遍,儿子不信,我当场就把三十多年前背过的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背了一遍,两千六百多字的文字像听到了口令似的,依次登场,儿子惊得目瞪口呆,我又把那十几处精彩的比喻分析了一番,说是那个时候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听老师讲,后来又把它们反复抄在作业本上才记牢的,小家伙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温故知新,及时巩固,分期回顾,学以致用……我的老师没有系统的学过教育学,但他的教育思路却科学合理,就像“老子”时代没有懂黑格尔,但辩证法早已渗透在《道德经》中一样,我的老师已经在学术和师德上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这是目前到处抄袭论文,每周上一两节课就叫喊加工资的所谓教授们难以企及的。
光线不足带来的顽疾是黑板没有合适的摆放位置,如果将它立在窑掌,学生背对着窗子,看不清书本上的字,黑板也因为离窗口过远,上面的字还是看不清楚;如果把黑板放在窗口,学生书本上的字看清了,可黑板背光,老师的书写,只能靠学生根据讲解和粉笔运动的轨迹揣测,错别字就难免了;摆到侧面,两边的同学只能看到黑板有一寸宽的厚度,感觉不到黑板有多大。黑板就像一个没有型号的螺帽,在哪一辆机器上都找不到相应的螺纹。办法总是有的,我的老师根据光线的明暗移动黑板:早晨和傍晚,光线较暗,他就将学生分为两组,黑板放在教室的中间,面向门口,听讲的学生面向黑板的正面,做练习、默写课文的学生,坐在里面,面向黑板的背面;中午光线强,黑板可以放在窗子附近,虽然背光,学生还是看得清楚,三个年级可同时学的图画和简谱都能在黑板上展示。老师也相应的把练习课、复习课,安排到两头,新授课安排到中午。有些课确实需要在早晨上,我的老师就将要讲的例题或者生字、生词写在两面小黑板上,挂在教室的侧壁,照顾两头的同学,中间支一面大黑板,学生都面向侧壁听讲。老师给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这些题我是这样认真地做了三遍,才不出错;那些生字、生词我也是这样一笔一画地写了至少三遍才这么俊美,你们要像老师这么认真才能学到真本领。”我们都以老师为榜样,生字生词反复地写,力争比老师写得好;一道数学题做三遍,三遍都不出错才算通过。现在想来,那大小不同的三面黑板,挪前挪后的一面黑板,老师像教本一样提出提进的小黑板早已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涂上了踏实认真,一丝不苟的身影,那身影就像天安门上的国旗,早已成了一种崇高和伟大。现在我指导学生例题做三遍不出错,可以看下一种类型题;钢琴弹三遍不出错,可以再加一个拍子;英语的典型例句要听懂、背熟、写对,作为学习其他同类型句子的模板进行比对;回答主观题先听老师讲一遍,自己口述一遍,再动笔写到卷子上,才能保证卷面整洁,条理清楚……这都是窑洞小学教给我的思路,是四年大学里没有学到却十分见效的教法。
虽然说窑洞冬暖夏凉,夏凉倒不假,冬天不生火,还是受不了西伯利亚寒流的折磨,特别是我们这些一条棉裤穿几个冬天,裤腿时常露肉的孩子,更是没有实力和寒流对抗,脚上、手上的冻疮和苍蝇换班,夏天苍蝇上班,冻疮休息,冬天苍蝇刚下线,冻疮就找我们来了,一来就是一个冬天不回家,有时还磨蹭半个春天。教室里用土坯垒起一个土堡,土堡里唯一的铁制构造就是炉条,炉筒子是买不起的。燃料就是细煤和土倒成的煤块,可这煤块也不够用,多是山里捡来的干柴,一旦生火,教室里浓烟滚滚,呛人的气味使全体师生集体咳嗽,
只能将窗子打开。寒风将窑里的浓烟赶净,也将炉火带来的温暖一并驱逐出门。“生火”不能“取暖”,要上课,就得挨冻。搓手、哈气、跺脚,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影响老师的讲课。对付寒流,没有上策,但也有下策:老师在门外抹了一个土堡,生了一团伙,我们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火炉旁烤一烤,烤热了进来上课,但这样秩序太乱,出出进进,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老师把困难汇报到生产队长那里,生产队派劳力,给三孔窑洞的后面排了三个土炕,每个土炕可以坐十多个学生,一个年级正好一个土炕。师娘将炕烧得滚烫,整个窑里都热气腾腾,混合着微微的烟草味,给人一种家的温馨。我们借着微弱的亮光,在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爱老师,老师爱我们……”,老师给一年级讲解完,布置任务后又到另一孔窑洞上二年级的课,二年级的课还没讲完,三年级的学习委员又在门口报告,说它们已经做完了习题,等老师好半天了。我们都趴在热乎乎的炕上,老师却在三孔窑洞里穿梭,像发动起了的拖拉机,不关油门,就一直往下跑。师娘的饭煮熟了,诱人的香味使我们老咽唾沫,再也听不进去“段落大意了”,师娘让我们吃一口,“不吃”;师娘让我们吃一个,“不吃”;师娘让我们吃两个,“……”我们经受不住师娘的反复强化,小黑手终于接过了冒着热气的粗面馒头、玉米棒子、洋芋疙瘩、荞面搅团……爸爸妈妈知道后,先是骂我们“丢人”,后来又督促我们带些吃食,给老师填补馍篮,那年月,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尽管师娘多次推让,可最后还是收下了。老师觉得长期这样不好,就让我们把冻成铅球的馒头收集起来,让师娘托热,那个不到一尺大的黑锅,师娘得耗一早上的功夫为我们尽义务,我们一副馋狼般的吃相,老师和师娘颠一脸笑佛模样瞅我们狼吞虎咽。门外寒风呼呼,门内却春风拂面。前天来了个测字算命的,让我在他手心写两个字,我先写了“老师”,他说你是老师就不要写这两个字了;我又换成“师娘”,他说和老师有联系,再换两个字;我换成了“窑洞”“土炕”“大学”。他说这一下没联系了,我说还是有联系,这是我人生的“关键词”《大学》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意思是说,大学的宗旨,是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迎新,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按这个标准衡量我的母校,叫它“大学”,你看恰当否?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那时蒙受了老师“涌泉之恩”,但我们没有“江海之蓄”只能用“滴水”相报。老师备课,批改作业,我们给他翻本子;老师改卷子,我们加分,登记成绩;老师的衣服脏了,有高年级女生捶洗;老师柴垛矮了,我们使它长高长胖;老师的面缸见底了,我们哭着闹着向爸妈讨,讨不来了,就到麦地里捡麦穗,豆角地里拾黄豆,洋芋地里刨寻遗漏的“白蛋”“红蛋”;上树掏鸟窝,下夹子逮野兔,用小铁铲挖山芋,下雨后采蘑菇,拾地软软……把老师的的灶房变成杂粮店。现在有报道说日本的孩子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我说他们是夜郎自大,如果敢和我们一比高下,就像他们自以为是的围棋手遇上了聂卫平,非败不可。这得益于老师训练我们自救的秘方——凡是学生从山里淘回来的,老师一并“笑纳”,还要表扬,享用的时候还要分给大家,还要加几句“将来能干大事”的鼓励。如果是偷来的,或者是讨来的,坚决不要,还要点名批评,更要双手捧送给主人且道歉。我们这些窑洞学校里毕业的学生坚信“有一双手是不会被饿死的”。我们从这所“大学”一毕业,马上就有了“工作”。
如今,和我一同读村学的二十多个同学中,有上了“西北师大”的,有“人民大学”读了研究生的,还有“北京大学”读了博士的,可我们一说起母校,首先想到的是窑洞里的书声,和那些足以称作教育家的老师,至于那些别人羡慕的高校反倒居其次了。
本文由《文章马伊琍网》/ 负责整理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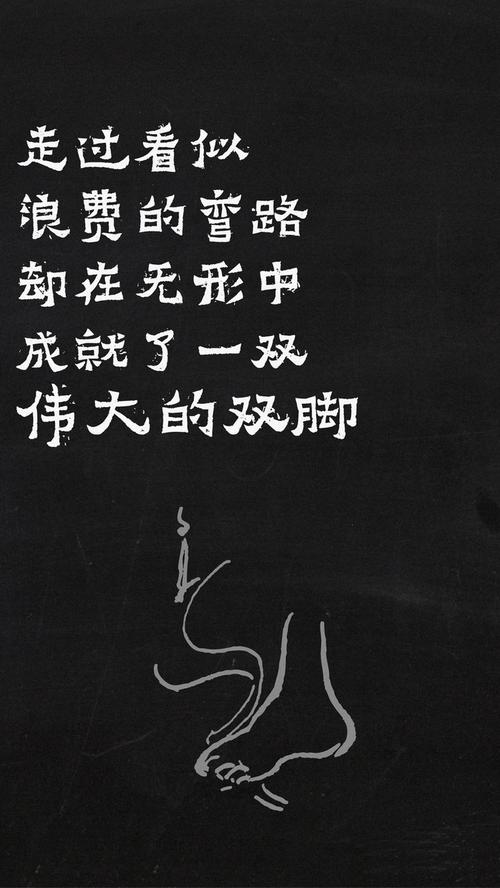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4-02-20 05:52:54,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8379575145095.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窑洞,学府.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窑洞,学府.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