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0日发(作者:学做小笼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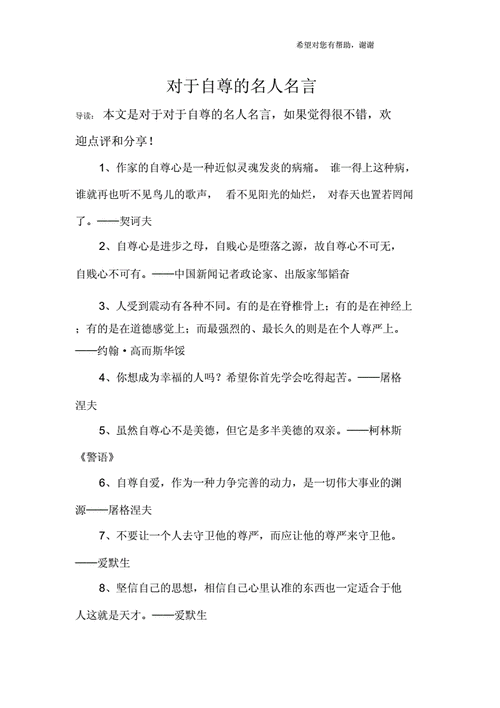
说说《老王》里的愧怍
《老王》一文中,最关键的是结尾一句话:“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许多朋友写文章认真分析这句话,大家都指出,杨绛本人其实也不是一个“幸运”的人:被剃了阴阳头,罚扫女厕所,“上台就有高帽子戴”,受尽了精神的屈辱。从这一点上说,可能是生活困苦的底层车夫老王比她还要幸运一些。
可是,在文章里头,杨绛还是以她一贯的冷静风格来叙事,不动声色地表现自己的强烈的思想倾向。这是一种来自真正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融汇了传统士大夫宽阔胸襟与普世价值的博爱精神。而这一份“愧怍”来自于一个文革的受害者而非施虐者,更加令人感慨。
上课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杨绛与老王之间的距离及产生的原因。尽管是被打倒的阶层,由于收入和知识地位等的原因,两位被批判的教授和一位底层的车夫之间,还是有着在精神与物质上都无法抹平的鸿沟。其实,老王的生计也是来自于钱钟书的车资,而他真诚的感谢,——香油和鸡蛋,——杨绛也是自然要付给他报酬。这近乎是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的体现;而这一点也是“几年过去了”之后,再被善于自省的作者所感悟到的。
文章中,杨绛给老王钱的时候,有这样的对话。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这里我让学生补出杨绛回答中的省略部分,那个破折号其实是思维的跳跃。“我知道”你是来感谢的,是表示友情的,但是,我们怎么会不要你的钱呢?意思是,我们怎么会白吃你的东西呢,我们本来还是要照顾你的呀,就算是到了这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白拿你的鸡蛋和香油。这些话都是符合人情物理的,唯独不符合的是友情,不属于真正的朋友,也许。而老王“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说明这种层次感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存在。之所以有这些,都是作者和老王的交往过程中造成的,也许,这也是作者深深“愧疚”的原因吧。
我说以上这些,其实是有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当年被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家庭,还有知青,尽管不少人还是“监督劳动”,来“接受再教育”的,但在淳朴善良的老百姓眼里,他们还是“城里人”,是“国家的人”,是“有水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太会与农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我自己的家中,父母也是文革受害者,我们在农村生活期间,我发现,我干部出身的母亲自反右后务农近20年,却没有真正融入农村妇女那个群体。我现在回想起,她与周围人的交往,在骨子里是有距离的。同时,母亲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是那种对品德修养及学习习惯近乎苛刻的要求。而1978年母亲复职后,我惊异地发现,她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如鱼得水地回到20年前的岗位上而毫无陌生感。
我说这些,是觉得《老王》这一课也许还揭示了很多更深层次的国民性的心理因素,这些特别的积淀,也许是作者“愧疚” 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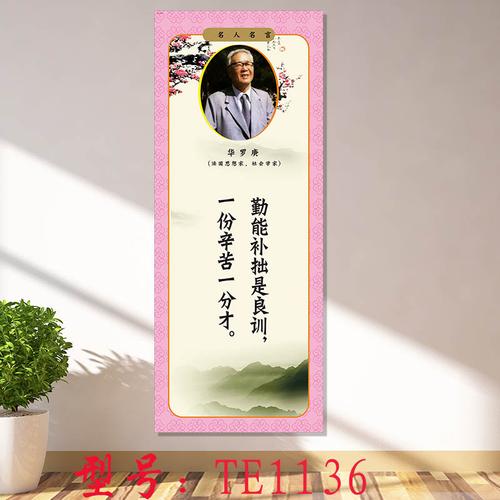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4-02-10 21:23:34,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7571414139715.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说说《老王》里的愧怍.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说说《老王》里的愧怍.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