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2日发(作者:迎江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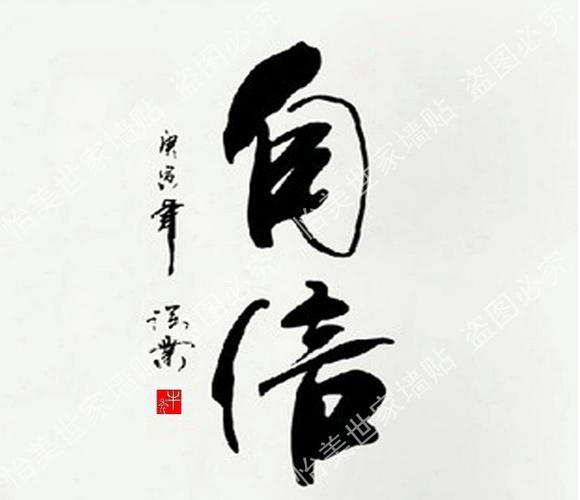
季羡林的人生经历简短
1. 季羡林的一生经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学校读书。 10岁,开头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高校附设高中。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考人清华高校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忙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犹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其次、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1978年复出,连续担当北京高校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高校副校长、北京高校南亚讨论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扩展材料: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闻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训练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高校名誉校长、北京高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讨论所所长,是北京高校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参考材料来源:百度百科——季羡林。
2. 急求季羡林人生经受~~~~~~~~~~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高校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高校主修印度学,先后把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本人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掌管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辟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讨论所所长等职。
给你精简出来的 盼望对你有关心
3. 季羡林的生平引见,短一点
季羡林,(1911.8.6—2009.7.11 早8:20),字希逋,又字齐奘。闻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通晓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高校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讨论所所长。1911年8月6日诞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高校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讨论建树颇多。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讨论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高校出版社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和善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伴侣,都应当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故弄玄虚;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依据我的观看,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晓得本
人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觉,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盼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行能的。
时间流失,一转瞬,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本人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一直保持平衡,心情一直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本人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本人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肯定把全部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肯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由于虽然国家有这样那样不行避开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终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矗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盼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行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实行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制服自然”,而东方则主见采纳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伴侣,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要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狡猾,学外语也要狡猾。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也许的状况。
4. 季羡林的一生事迹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讨论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高校出版社 次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觉并证明白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
的存在、阐明白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胜利的语义讨论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次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次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参考材料:
5. 【季羡林的人生感悟】
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 学习吐火罗文 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我学习吐火罗文,就与偶然性有关. 说句狡猾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缘由其实是很简洁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随时警告本人:本人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老人家肯定要把本人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莫非他不晓得教书的辛苦吗?莫非他不晓得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适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本人的绝学教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莫非这里面
还有一些极“左”的先生们所说的什么侵略的险恶专心吗?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传法、教授衣钵的佳话,什么半夜里隐秘教授,什么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当时都没有遇到,也许是由于时移事迁今非昔比了吧. 总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咨询看法的意味,他也不留给我任何考虑的余地.他提出了看法,立即支配时间,立刻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谢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本人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权威学习吐火罗文,是世界上很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由于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自怨自艾.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很多人所艳羡的.这一点我是特别清晰的.我要是不学,实在是难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给我开课的时候,比利时的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WalterCouvreur)来到哥廷根,想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殊班就开办起来了.高校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要两个同学,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殊班.可是西克并不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周有几次从城东的家中穿过全城,走到高斯-韦伯楼来上课,精神矍铄,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镜,他本身几乎就是一个奇观.走这样远的路,却从来没有人陪他.他无儿无女,家里没有人陪,学校里当然更不管这些事. 吐火罗文残卷只要中国新疆才有.原来世界上没有人懂这种语言,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策(s)关心下,读通了的.他们三人合著的《吐火罗语语法》,蜚声全球士林,是这门新学问的经典著作.但是,这一部长达518页的皇皇巨著,却绝非一
般的入门之书,而是特别难读的.读通这一种语言的大师,当然就是最抱负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头.我们一起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常常称之为“精制品”(Prachtstück)的《福力太子因缘经》.我们本人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番译成德文,西克加以订正.这工作是特别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肯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爱好日益浓郁,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落到人间,由于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四周静得令人发憷,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烁着积雪的银光.似乎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始终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暖和,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 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添加点养分,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
这一点,只要从本人的少得可怜的食品安排中硬挤.我也许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遗忘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出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这无疑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明显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感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开心的,成为我一生最开心的回忆之一.
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状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定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定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学问带回到中国.虽然我一直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两头还由于种种缘由我几乎有三十年没有搞。
6. 季羡林的生平事迹
季羡林是中国闻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高校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讨论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高校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高校与德国的交换讨论生,赴德国入哥廷根高校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
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机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讨论道路。1945年,其次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举,季羡林被聘为北京高校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讨论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晚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订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卑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而,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状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许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讨论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讨论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后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
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示国内运用音译梵字讨论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肯定要留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讨论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讨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沟通的历史实际。因而,季羡林在讨论中,一方面注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讨论》(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后能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月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虽然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旧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讨论,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沟通是人类进步的次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需相互学习,扬长避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定是某
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乐观参加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争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复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剧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乐观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高校,创建东方语文系,开辟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7. 简洁引见一下季羡林
季羡林说本人:镜头人生。
在品德的好坏方面,……我虽然有不少的私心邪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慌,这当然也是衡量品德的一个标准。
我说过不少谎话,由于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
因而我是一个好人。 我的学术讨论,特点只要一个字,这就是:
杂。
……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所可以聊以自慰者只是,我在杂中还有几点重点。
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地讨论的课题。我在讨论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
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光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
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胜利,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
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特别人所可得者。 ——季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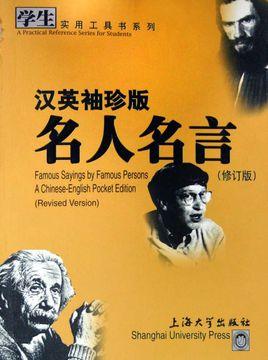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4-01-12 16:10:32,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504703246714.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季羡林的人生经历简短.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季羡林的人生经历简短.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