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0日发(作者:秋天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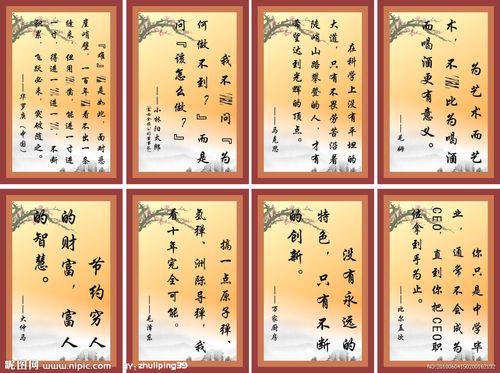
面对金钱势力侵袭的恐惧呼喊——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
安国梁
【摘 要】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和非凡的历史价值。"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泰门对颠倒乾坤的金钱的诅咒和恐惧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情。这种感情莎士比亚时代有,早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有,晚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坛金子》就是古代社会对金钱力量的破坏性所作的一次虽然片面然而不失深刻的形象展示。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
【年(卷),期】2012(000)010
【总页数】5页(P87-91)
【关键词】金子;金钱;图斯;恐惧;莎士比亚;历史价值;承前启后;戏剧舞台
【作 者】安国梁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49
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有着承前启后的
作用和非凡的历史价值。“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泰门对颠倒乾坤的金钱的诅咒和恐惧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情。这种感情莎士比亚时代有,早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有,晚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坛金子》就是古代社会对金钱力量的破坏性所作的一次虽然片面然而不失深刻的形象展示。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1]泰门对颠倒乾坤的金钱的诅咒和恐惧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情。这种感情莎士比亚时代有,早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有,晚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坛金子》就是古代社会对金钱力量的破坏性所作的一次虽然片面然而不失深刻的形象展示。
现实人物的古老基因
奥维德《变形记》的弥达斯王的故事以幻想的形式思考了在社会上日益发展、日益得势的金钱势力。酒神巴克科斯因为义父西勒诺斯受到佛律癸亚王弥达斯的款待和保护,决定送一份礼物表示答谢。弥达斯王说:“请你答应我,凡是我的身体接触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黄金。”[2]酒神虽加劝阻,但未奏效,只得难过地答应了他。他果然把石头、泥土、殿柱等都变成了黄金。到吃饭时间,他面前摆上了丰美的筵席,但是任何食物,经他一沾便变成了无法充饥的黄金。食物虽多,不能吞咽;口渴难熬,喉咙干裂,却无水可喝。他被可诅咒的黄金折磨得苦不堪言。“这种新奇的灾难使他惶恐。他固然富有了,但是很不快活,他想逃避财富,他痛恨他不久前还在祈求的东西。”[3]他请求酒神宽恕并收回传授给他的点金本领。酒神一方面批评他“欲望”给他带来灾难,一方面指示他到帕克托罗斯河的源头,跳进水里,连头带身全没在水里,这样,他点金的能力就能从他的身上转到河里,而这条河也
就成了著名的金川。
远古时代,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只能甚至不足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有了剩余产品。进一步分工,进一步的财富积累、交换和货币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统治者一方面凭借财富、权力支配着另一个阶级,另一方面也被财富所支配,甚至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不管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他们都感觉到了自己创造的处于自身之外却支配着自身的财富的强大力量。这样,神话中就不能不出现弥达斯王由财富而带来的生存焦虑和困惑。
神话作为原始人的灵魂,作为人类精神现象最初的、整体的表现,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历史大地上播下的第一粒种子。在不同的文化气候和土壤中,这一范型就能萌发出无数大同小异的奇葩异卉。《一坛金子》及其据以改写的希拉菲勒蒙原著只不过是弥达斯王这一神话原型的最初的现实呈现。在随后的岁月里,欧克利奥拥有一群血浓于水的兄弟姊妹,如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阿巴公,巴尔扎克的小说《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头,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普柳什金等。
《一坛金子》、《威尼斯商人》、《悭吝人》等在欧洲戏剧舞台上先后辉映,大放异彩。《一坛金子》和《悭吝人》在创作上的借鉴和创新及一脉相承和华丽变奏的关系尤其引人瞩目,发人深思。
普劳图斯的晚辈莫里哀对《一坛金子》颇感兴趣,他用创造性的继承方法表示了对前辈的敬意,把《一坛金子》改写成了《悭吝人》。在这写作的变奏中,莫里哀对剧本的主人公作了重大的改造,老人不仅有一待字闺中的女儿,而且有一个已届婚娶年龄的儿子。剧作家异想天开,不仅让这对父子成了情敌,而且也成为债权人和
债务人。同时,为了与老人的这对儿女相对应并发生纠葛,剧本又增加了从意大利流落到巴黎的昂赛末及其一对儿女的故事。与《一坛金子》相比,《悭吝人》的情节复杂得多、丰腴得多。
假设有这么一个时间隧道可以让这两位剧作家不期而遇,那么我们可以猜想,普劳图斯一定会对自己的后辈宽容地说:“也许这一切对你都需要,但是,对我来说,我却会因这些藻饰而苦恼。我只需神话原型的最基本、最简单的架构。用这最简约的因素,我同样能写出典范的喜剧,喜剧的典范。要知道,用最简约的要素写出最美妙的剧作,这才是剧作家的光荣和骄傲!”
《一坛金子》果然没有莫里哀《悭吝人》中的装饰成分,它只是一个实在而简约的故事,一个以婚嫁为背景,家中窖藏的老人欧克利奥的一坛金子被盗、失而复得、最后被作为嫁妆送给女儿的故事。没有附体的萝蔓,没有侧出的斜枝,金子的得—失—得—失(赠女)构成了整个剧作的核心和骨架。这种艺术安排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绝,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同样地抛弃一切多余的粉饰,同样地删除一切不必的附丽,留下的只是让观众怦然心动、相看不厌的观赏对象。这确是艺术中的大手笔才能达到的境界。
这种只就本事生发的本领使《一坛金子》充分展示了古罗马时代的艺术欣赏口味和艺术欣赏期待。
普劳图斯并不把喜剧的成功建立在巧合等追求戏剧效果的技巧的基础上,而是要凭借当时公认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去摘取喜剧的桂冠。《悭吝人》中那不勒斯达尔西·托玛爵爷一家逃避迫害、遭遇海难、全家离散、流落巴黎悲惨曲折的经历很能动人心弦。他们父亲兄妹因为相知相亲、重建家庭的要求而在阿巴公家中不期而遇,偶然会面也能使人喜极而泣。当然,这类巧合在现实生活并非绝无仅有,其作为广泛采用的艺术手段在喜剧中确也屡见不鲜。但是,这种巧合不免给人一种过于矫揉
造作、过于粉饰雕琢之感而使作品缺乏自然的神韵与洒脱。这不是古罗马艺术家心仪的目标。普劳图斯追求的是一种符合情理、恰到好处的统一和谐。《一坛金子》正是这一美学思想的有趣图解。
剧本的发端是一个贫穷潦倒的老人欧克利奥在家中灶下找到了其祖父埋下的一坛金子。贪财、多疑的性格使他对藏匿的黄金无法放心,把老女仆赶到门外检查黄金是否安妥,自然构成了戏剧的第一幕。邻居梅格多洛斯应姐姐的要求而决定结婚,但他不愿娶“会把男人变为奴隶”[4]、花费无度、身份高贵的女人,而想向穷困的欧克利奥的女儿求婚。欧克利奥以为老女仆泄漏了他藏金的秘密,梅格多洛斯看中了他的财富才采取了富人向穷人求婚这种不合常情的做法。欧克利奥经过反复试探、猜度和窥测,然后以“我不能给她任何嫁妆”[5]、“她没有嫁妆”[6]为条件答应了这门亲事。未来女婿体谅他贫穷,为他家准备婚宴、派来了厨师等人,欧克利奥家顿时热闹起来。这些情节的发展确实自然。欧克利奥怕家中的金子被发现,一顿棍棒把厨师们赶了出去,并趁机把藏有金子的坛子转移到屋外,然后才允许厨师等人进屋置办酒席。他又和梅格多洛斯一阵搭讪以后,决定把坛子藏到守信女神神庙。这是喜剧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听说欧克利奥嫁女,爱上他女儿的卢克尼德斯派自己的奴隶前来,“打听打听,事情究竟怎样”[7]。藏好金子的欧克利奥因预示不吉的乌鸦叫,再次到神庙检查时发现了这个奴隶,并起了争执,发生了冲突。他疑虑重重,把金子再次转移,但这个奴隶跟踪了他,金子失窃。接着就是著名的第四幕第九场:老人发现金子失窃,找寻路上,发出了“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8]的浩叹,喜剧情节发展达到高潮。此后,由于卢克尼德斯的介入、干预,欧克利奥的奴隶不得不把偷得的一坛金子归还老人,老人高兴之余,在卢克尼德斯舅舅梅格多洛斯的同意下,决定把女儿嫁给卢克尼德斯,并把一坛金子作为嫁妆赠给了女儿。老人没有金子的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宣布说:“以前我白天黑夜守着它,心里始终平静不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睡觉了。”[9]
这仿佛是然而并不是《一坛金子》故事的复述,而是我们对剧作家那复杂而玄妙的运思所作的简单而合理的猜度。作家如何在想象的翱翔中生发故事,并给予这种故事的生发以充足完全的理由呢?显然,在《一坛金子》中,剧作家已直觉地参透了性格与情节的关系,紧扣老人“贪财、多疑”[10]的性格特点,经过推导、想象,组织起一个合情合理、符合情节发展逻辑的精彩故事。情节一环紧扣一环,后一情节是前一情节的必然结果,上一情节又是下一情节的原因。因果相承,环环衔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故事组织得那么紧密,以致“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11]。这正是一个结构完美的布局,正是它赋予了剧作朴实、单纯、统一、和谐等古典戏剧所固有的优异特质。《一坛金子》中欧克利奥身上具有的古老基因,即潜在的神话原型也使作品具有历史的厚重感,成为全体人类说话的载体,超越个人而成为永恒不朽的存在,展示人类内心最深邃的魂灵的颤动。深刻的现实体验、明净和谐的艺术风格使《一坛金子》成为古罗马戏剧颇具代表性的剧目。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也决不会贬低莫里哀的价值。《悭吝人》自有它的价值和成功的秘密,只是不在论者论述范围之中而不能详加考察而已。
“失斧者”心理的典型例证
现实生活中,失物者常常会疑神疑鬼地看待周围的人。有一个寓言把这种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樵夫不慎丢失了砍柴的斧头,在焦急寻找时他发现邻居有偷窃的嫌疑,邻居的一言一行都能证明他的这种猜测和怀疑,他愈看邻居愈像贼。当他找到自己的斧头以后再看邻居,感觉邻居并无这种恶习,自己也奇怪当初怎么会认为邻居有作案的可能。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一文中曾对判断错位的这一心理现象作过精彩的剖析。他说:“感情引导我们陷入错误。”[12]“常常在这些对象并不存在的地方向我们指出这些对象。”[13]“我们经常总是在事物中只看到自己要想发现的东西”,“幻觉是感情的一个必然结果”[14]。一个失去东西而急于找回东西的主人,他急切而强烈的感情往往会使理性退避三舍,一点可疑的蛛丝马迹就足以
使他视为铁证,甚至把子虚乌有看作手中抓到了对方的把柄,把幻想当作真实,错误、笑话自然在所难免。
普劳图斯通过欧克利奥这个人物,活灵活现地刻画了穷人暴富后由保持财富带来的精神紧张和巨大压力,也把现实中的这种“失斧者”心理现象移植进剧作之中,使剧作成为一个深刻揭示人类灵魂的杰作。
欧克利奥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跟他有过联系的只有老女仆斯塔菲拉,厨师康格利奥及助手,奉主人卢克尼德斯之命前来探听消息的奴隶斯特罗比卢斯,邻居梅格多洛斯、卢克尼德斯。欧克利奥对财富失去的恐惧使他无限夸大财富的抢掠者,他以为一坛金子将成为众人追逐的目标,他忧心忡忡地说:“啊!坛子啊!你和你里面藏着的金子面临着多少敌人呢!”[15]他把与他多少有过交往的人都划进了“敌人”的范围。他把他的老女仆看作是黄金的窥探者、藏金的泄密者,把厨师和斯特罗比卢斯看作是小偷、是贼,把梅格多洛斯看作是一坛黄金的觊觎者,把前来补过赎罪、向其女儿求婚的卢克尼德斯错认为是宝贝的占有者。
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泛化中,他与他们的语言碰击,常常出现一些足以使人把握他灵魂的有趣意象。
《一坛金子》中,门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欧克利奥进出家门次数颇多,每次出门从忘不了交待女仆“把门关上”、“在屋里守着”、“不要让任何外人进屋里去”[16],嘱咐女仆“用两根门闩把门插上”、“即使好心的财神降临,也不许放他进去”[17]。他自己进门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门关上”[18]。当他从市场返回,看到家门洞开,他立即惊呼:“不好,是不是有人来抢我的东西?”[19]
在欧克利奥看来,门是把他和世界分割开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不仅保证了黄金的秘密,而且保证了它不受外界侵害的安全。因而,对他来说,门是黄金的神圣守卫者。对门的关注也就是对财产、身家性命的关注,是丝毫懈怠不得的工作。在舞台上,我们确实看到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割舌与挖眼是两个十分恐怖的意象。欧克利奥与老女仆斯塔菲拉朝夕相处,家中的一切对她难以隐瞒。但是,欧克利奥发现祖父埋下的窖藏并得到一坛四磅重的金子的秘密是绝对不能让她知道的。绝对不能让她知道的秘密又对她难以隐瞒,他不能不为此惶恐,不能不为此焦虑不安。欧克利奥觉得她是他财富的窥测者,“这个坏婆子连后脑勺上都长着眼睛”[20]。为了使到手的财富不致另换主人,唯一的也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让她看到、发现。不让她看到、发现的最好手段当然是让她失明。剧中欧克利奥多次恫吓、威胁她说:“鬼东西,我真想把你的眼珠挖出来,让你再也没法偷看我在干什么。”[21]当梅格多洛斯求他把女儿嫁给自己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立刻回去……挖出她的眼睛!”[22]
在欧克利奥看来,斯塔菲拉是当然的、糟糕的、可恨的藏金泄密者。当梅格多洛斯求他女儿为妻时,他觉得事情十分蹊跷,富翁怎么会向穷人求婚呢?他的第一个判断是“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了金子”[23],他的第二个推断是“事情很清楚,老婆子一定向他泄漏了关于金子的秘密”[24]。露富诲盗,这还了得,怪不得梅格多洛斯要通过婚姻来抢掠他的金子。他不由怒火中烧,宣称:“我要立刻回去割掉她的舌头。”[25]在另一场合,他再次威胁要把老婆子的“舌头齐根割掉”[26]。为了保护财富,他在意念中竟起了动刀的杀心,真令人不寒而栗。
三只手和六只手是两个荒诞的意象。“六只手”是神话的残留物。欧克利奥说厨师“个个都是革律翁的后代,每人六只手”[27]。革律翁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三个身子连在一起的三头怪物。这里的着眼点不仅在于手的多少,而且还在于手取物的功能。实际上这是由神话引申出来的意象。“三只手”则与“六只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欧克利奥却在感情的巅峰状态中把“三只手”这种心理映像当作了真实对象,他怀疑斯特罗比卢斯盗窃,并进行搜查,让后者“把手伸出来”。后者伸出双手,欧克利奥接着说“我看见了。把第三只手也伸出来!”[28]后者的反应是:这个老头中了邪,完全疯了。确实,倘若不是疯子,谁会要一个正常人伸出“第三只
手”呢?
棍棒和揍是与恐怖意象相辅相成的暴力意象,欧克利奥的行动不仅有语言的威胁,也有凶狠的行动。欧克利奥先后狠揍过斯塔菲拉、康格利奥及其同伙、斯特罗比卢斯。他还不断地在口头上威胁他们:“我要把你狠狠地揍一顿。”[29]在他看来,对付那些觊觎他的一坛金子的窃贼,棍棒是必不可少的,身上的疼痛至少可让他们下手之前先想一想。
小偷与贼是《一坛金子》中使用最广泛、频率最高的、侮辱人格的、法官给人定罪的意象。尤其可笑的事,他把鸡这样的家禽也归进了“贼”的行列。他说:“还有屋里那只公鸡,它是老婆子用私房钱买的,也差一点没把我彻底毁了。那只公鸡用爪子在我埋金子的地方到处抓。我一见就火冒三丈,操起棍子,把那只鸡——那只当场拿获的贼打死了。毫无疑问,厨子准是答应给公鸡报酬,只要它能把东西刨出来。我终于斩断了他的魔爪。”[30]在他的主观测度中,梅格多洛斯和厨子,甚至和公鸡都是一伙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抢我的东西。”[31]因此,把当场拿获的贼乱棍打死也自在情理之中。公理在自己一边。殊不知,他心目中的贼不过是一只在土中刨食的公鸡!
人的心理是一种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倏忽而来,飘然而去,没有才能的作家往往会眼花缭乱、无法捕捉。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不得不面对这一文学难题而作出自己的创造。《一坛金子》中上述有关欧克利奥的言论构成的意象,实际上也是剧作家对此人心理所作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西方谚言说,知道你拥有什么样的朋友,就能知道你是什么人。如果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知道一个人对自己周围人的态度和评价,就能知道这个人此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拥有什么样的灵魂世界。人的心理状态外射到这人所评价的人物身上,被评价的人物必然染上此人这一心理状态的色彩。从欧克利奥对待周围人的态度和不断出现的意象可以断定:欧克利奥整个人已被一坛金子所控制和支配,保持
现有财富的超限压力使他具有强烈的偏执倾向,这种偏执倾向达到了精神混乱的程度,精神和现实、概念和实质消失了一切界限,从而使他作出一些令常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这确是一种人的“异化”。这种对财富的贪婪和保持财富的冲动也磨灭了他的人性,使他成为了一个冷酷、残忍而无情的冷血动物,棍子揍、割舌、挖眼等血腥言词自然成了他的口头禅。这使我们真切感受到金钱来到人间,确实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这种通过对他人的感情评价来解释主人公心理的迂回方法较之直接刻画、勾勒主人公灵魂的方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这可以说是普劳图斯的一个创造。
残缺未必不真不美
一个完美的对象,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到伤害,所以残缺、破损。这个受损的完美对象给人的审美感受并不是单一的,有时它可以因残缺而丧失往昔迷人的风采,变得丑陋不堪;有时它并不因为破损而损伤过去那优美典雅的气质,因而它仍是美的化身。这在现实和艺术中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
破损而失去美的价值,这类事情比比皆是。试想,一个美女头像被挖掉了如水秋波,双眼变成了两个黑洞,我们还能找出她那“巧目盼兮”的昔日风情吗?我们还能感受她的美而承认她是美的精灵吗?
残缺而无损于美,这类现象也不罕见。在世界文化史上,最突出的、最有代表的个案当数1820年发现的古希腊雕像“米罗岛上的维纳斯”。这是一尊古希腊美神阿弗洛狄忒的塑像,双臂已经残缺。但是,残缺双臂的维纳斯仍然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的美人坯子,端庄典雅,亭亭玉立,刚健流丽,妩媚婀娜,也曾引得几多凡人心醉神迷,使得他们五体投地!
残缺而仍不失为美的审美对象并不是因残缺而美,而是残缺无损美的总体效果因此使美得以保存延续。残缺美是一种有条件的美。照我们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促成了这种美。
首先,残缺部分不是整体的主要部分和重要部分。美虽然是在整体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来,但是,一个完整体的主要部分和重要部分在美的呈现上还是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责任。因而,如果完整体的主要部位,如拥有完美曲线的维纳斯的身躯也遭毁损,那么米罗岛的维纳斯像的美也就不复存在。残缺的量和部位对原有美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其次,残缺部分有无可能构成想象的空间,使人产生种种神奇的联想,从而丰富而不是削弱审美对象的内蕴,这也很重要。据说,许多艺术家曾为米罗岛的维纳斯残缺的双臂设计过种种修复方案,结果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艺术家们只得无功而返。正是这无法修复的残缺,使人生出无限的遐想,产生出无限的可能性,在探索中感受着美,作品由此更耐人寻味。
第三,残缺部分有时能显现、扩大和增强原来完整体所固有的美的因素,使残缺的审美对象有可能更突出作为完整体时不易被察觉的那些优美特征。完整的米罗岛的维纳斯雕像自出土时起谁也没有见过。但从残留部分看,双臂应该是分置在身躯两边的。从比例的角度看,这尊雕像的身高会因为双臂的宽度而变得不那么高挺。双臂的残缺恰恰改变了这种比例,也改变了人的视觉印象,它是那样颀长、苗条而显示出非语言所能形容的美。没有残缺,也就没有这理想的美。
《一坛金子》实际上是戏剧中的“米罗岛的维纳斯”。它的残缺无损于它的美,却使人在无穷的联想中享有着智性活动的乐趣。
留存的《一坛金子》是个残缺的本子,好在残损不多,只缺了第五幕“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即使残缺部分,仍有若干破句、残句存留。根据戏剧创作的规律,残缺部分应该是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对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一完美的交代。
《一坛金子》的残缺部分并不影响全剧的完整性。一般来说,欧洲古典戏剧具有鲜明的传统,按照必然律或可然律来组织安排整个戏剧情节,这样的情节必然因果相承,头、身、尾相承相续,有条不紊,完整紧密。《一坛金子》完整保存下来的前
四幕的人物关系,足以使我们合理推测出普劳图斯作品可能的结局。
欧克利奥和求他女儿菲德里雅为妻的卢克尼德斯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语言错位:卢克尼德斯要他的女儿,而欧克利奥以为卢克尼德斯要的是他的一坛金子。在老人心目中,女儿绝不是宝贝,金子才是他的命。语言的错位足见金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位视财如命的老人丢失了金子后声称:“我完了……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32]他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生命对他只是悲伤、痛苦和灾难。因而,当卢克尼德斯责令自己的奴隶——偷得老人一坛金子的斯特罗比卢斯把金子归还老人时,老人绝对不会拒绝把菲德里亚嫁给这个求婚的年轻人。
卢克尼德斯求老人把菲德里雅嫁他为妻有没有必然性呢?卢克尼德斯在地母节的狂欢之夜喝醉了酒,对菲德里雅心存爱意的他竟胆大妄为,一时冲动而强暴了她,使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在古时罗马人看来,这并非不赦之罪,完全可以补赎。他对欧克利奥说:“如果有人犯了过错,他既不感到惭愧,也不想为自己赎罪,这样的人是最可鄙的。”[33]他不愿成为这种“最可鄙的”人。因此,他说:“欧克利奥,我现在请求你,请你宽恕我曾经无意中对你和你的女儿犯下的过失,请你把她嫁给我,法律要求这样做。”[34]对姑娘的爱、对过失的愧悔、法律的要求(强暴少女致使怀孕,必须娶少女为妻)使卢克尼德斯必然跨出求婚的一步,并最终与姑娘喜结良缘。
由于欧克利奥并不知道女儿被人玷污,怀孕的菲德里雅在老女仆的掩护下没有透漏出一丝受辱的消息,因此,他把女儿许给了首先求婚的梅格多洛斯。这似乎成了卢克尼德斯娶菲德里雅为妻的障碍。但是,卢克尼德斯与梅格多洛斯的甥舅关系成了消除障碍的有利条件。首先,梅格多洛斯并不是热衷婚姻的人,当他的姐姐、卢克尼德斯的母亲劝他成家时,他说:“啊呀,要我的命了。”[35]其次,菲德里雅怀孕使他难以接受这一婚姻。第三,最主要的是他与卢克尼德斯有着血缘联系的甥舅关系。在古罗马,甥舅关系在世俗生活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这实际是上古母系
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遗存。梅格多洛斯必须为外甥的幸福操持。既然外甥爱上了菲德里雅,他就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幸福结合。
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卢克尼德斯和菲德里雅必然踏上婚姻的红地毯。全剧就这样在欢乐、祥和、幸福的结婚宴会中告终。
《一坛金子》的残缺不足以影响对全局整体情景构成的理解,全剧在受众的心目中仍有其完整性。这种残损的完整性使剧本拥有一种残缺美。
《一坛金子》的残损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了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上面我们说到剧作的情节基本上可推导出它的原始状态,至少是近似原貌。这仅仅是一个“说什么”的问题,而关键却在于“怎么说”。比如,卢克尼德斯的奴隶斯特罗比卢斯对主人宣称:“即使你杀死我,也永远不可能从我这里拿……”[36]剧本由此中断。中断处奴隶斩钉截铁的立场和态度,主人也拿他无可奈何。主人究竟怎样才使他把盗窃来的金子归还老人呢?是主人向奴隶妥协,让他赎身为自由民,还是用暴力迫使后者屈服呢?当然,计谋、诡计都能从他手中取得黄金……这无数的可能性给受众以有趣的智性游戏。再如,老人是一个爱财如命的吝啬鬼,邻居梅格多洛斯求婚时,他坚持以“女儿没有嫁妆”为条件才答应了婚事。但是,在女儿出嫁时,他却把一坛金子作为嫁妆送给了女儿女婿。根据普劳图斯的创作意图,剧作必须作这样的处理。剧本“开场白”家神的长篇交代,肯定了这一点,因为女儿菲德里雅对家神的敬意而赢得了家神的欢心。留存的残句中,欧克利奥所说的“以前我白天黑夜守着它,心里始终平静不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睡觉了”这句话也证实了剧作的这一处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位视钱如命的、简直到了冥顽不化的老头怎么会有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一转弯如何才能表演得合乎情理而又符合他的性格?什么巅峰时刻促使他作出这一仿佛不合本性的决定?这中间同样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给受众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受众那无羁的想象力可以在其中尽情驰骋。可以这样说,没有残缺,受众就不可能享受这无拘无束的神游艺术世界的机会。残
缺大大提高了优秀剧作的欣赏性。
注释:
[1]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76页
[2][3] 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45页,146页
[4] —[10][15]—[36]古罗马喜剧三种.王焕生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82页,86页,87页,107页,114页,122页,71页,105页,78页,79页,99页,96页,77页,76—77页,83页,83页,83页,83页,87页,104页,109页,108页,100—101页,100页,114页,119页,119页,81页,122页
[11] 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8页
[12][13][1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北大哲学系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74页,174页,174页

本文发布于:2023-12-30 19:58:47,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3937527131744.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面对金钱势力侵袭的恐惧呼喊——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面对金钱势力侵袭的恐惧呼喊——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