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发(作者:蚂蚁篇)

琦君的散文《髻》
读琦君的忆旧散文,给人一种凄迷而幽怨的美感。美的令人忧伤,美的令人无法释怀。正如她自己所说:“淡淡的哀愁,像轻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虚无缥缈,更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
琦君.原名潘希珍.台湾散文学.生于1917年.浙江永嘉人.1949年去台湾.
1969年在美国定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已出版散文集《烟愁》、《溪边琐语》、《琦君小品》等十余部。她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写的最为动人的是怀乡思亲之作。《髻》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巧妙地选择了发髻这个女子青春美丽的象征物为视角.回忆了母亲与姨娘两个女人以韶华俏丽到年老色衰.终而殁世的人生历程.令人感同身受.读来凄怆悲凉.潸然泪下。
文章开篇点题.由回忆母亲年轻时的发髻写起.打开记忆的闸门.一幅幅承载女性人生情感的多彩画卷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分明感受到人生历程中的两种境遇冲撞心扉:爱情与美丽带来的欢悦明朗.衰老与孤独带来的凄凉伤感。两段人生的写照.两种境遇的感观.使人如历其境。
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我.便痴迷于对母亲如云的长发的玩赏之中。天真无邪的童心一定明了.母亲之所以快乐幸福.引以为自矜的定是那如瀑的“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的秀发。
每年的七月初七,是乡下妇女的洗头日。“女为悦己者容”,洗过头发的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心中流泻着掩饰不住的欣喜与欢乐,媚人的笑容挂在眉眼之间,因为这一天是父亲久客而归的好日子,母亲寂寞的心中一定在急切地盼父亲的归来。父亲张终于来了,不是独自,而是双双,带给我一位姨娘,一个比母亲更美丽更年轻的女人。女儿的眼眸,最能捕捉到母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从此,母亲的世界渐渐黯淡下去,“一把小小的黄杨木梳子,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了。”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母亲与姨娘坐在廊沿下,背对背彼此不交一语的梳头情景,深深地触动着我做为女性所特有的、与生俱来的对母亲的同情与怜悯的情怀。母亲最大的哀痛莫过于在父亲眼里心中的失宠。一个女人一旦失去爱人的关注与眷顾,如花的容颜就会渐渐枯萎。每每听到廊尽头传来父亲与姨娘的阵阵笑语声,就更加刺痛了母亲敏感而柔弱的心。“母亲的脸容反而不如以前在乡下忙来忙去那么丰润艳丽了”,母亲就是在这样郁郁寡欢的落寞中垂垂老去。
我长大后,离家在外求学,父母先后去世。定居台湾后,我惟一的亲人便是姨娘。多少年过去了,我望着衣着简朴、脸容哀戚、红颜已逝的姨娘:这就是使母亲悒郁一生的女人。然而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的内心深处也产生了一种与她相依为命的情愫。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姨娘也已作古.我流眄照镜.早也不年轻了。人生啊.什么是可以留住的?什么又是永恒的?爱恨痴贪.一切都如烟云过眼.渺不可追。
琦君1949年从大陆移居台湾. 1969年又侨居美国.面对流寓无定.世路茫茫.那种失落感、沧桑感和漂泊感.化为她文学作品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忆旧与怀乡。文中每一幅饱含爱恨情仇的图景.都以作者回忆的笔端渐次绘出.这正与天涯漂泊的游子的内心渴念相谐相契。台湾当代散文从1945年光复到60年代前后.乡土文学、海处游子文学相继涌现.背离生于斯长于斯歌哭哀乐于斯的熟稔的山水、人事、习俗.以温馨的回忆为题材.谈自然、谈情感、谈人生.不离亲情人伦之美.强烈地抒发了对故土、亲人、往事的追忆。台湾都市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对物欲的追求使得自然质朴、真挚坦城的人性美在人际的紧张和
冷漠中悄然消失.关注心灵的作家便求助于回忆的安慰.枝枝蔓蔓延展很多的情感触角里.总有一根最主要的情感线.那就是离乡越久缠绵越紧的思亲之情弦。
在《玉炉香,红烛泪——温庭绮》一文中,琦君说:“词中多用名物,重重叠叠地烘托出一种气氛”。在《髻》一文中,作者依赖象征青春与美丽的女子的发髻这一“名物”,或着意凸现,或随意点染出人生易逝,红颜易老的凄婉无奈的艺术境界。正如台湾学者夏志清所说:“琦君的小品散文晶莹清澈、典雅隽永.其风格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那种婉约清丽、诗意翩跹、凄美幽怨的轨迹清晰可寻。艺术境界上追求自然天成.平淡朴素中见出膏腴醇厚。
每位创作主体都有自己看重的美学品格.琦君就对真与自然情有独钟。她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的冰心相似.多半写童年记忆.母女之情等.堪称以真善美的视角写童年故家的圣手。在她笔下.童年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类个体生存史上的童蒙期.而是“蓦然回首.不复存在的心灵伊甸园”。她是将儿童圣洁的心灵.对童年的一次回忆.当成是涤滤心灵的一次巡礼。琦君绝少采用直抒胸臆的粗糙手法.而注重突出浓郁的个性色彩.结构上采取闲话家常的方式.笔致细腻柔婉.善于精心筛选出典型的生活细节.擅长捕捉人物心理活动的微妙之处.尤能抓住见出人性深度的心理活动。
《髻》一文的结构,就是作者从年幼时的记忆写起,将几十年的沧沧桑桑凝聚在两个女人的发髻的变迁中,看似随意道来,其实独具匠心,字里行间蕴藉着含蓄之美和深湛的感思。这份感思绵密纤细,没有大悲大痛,却又无孔不入,只是它并不粘执小气,而是环环递进,步步深入,又层层超越,娓娓道来,如絮家常,显现出女性特有的宽厚和同情,不失为一篇清丽永(按:原文如此)的散文佳作
沈謙教授說:「琦君,是生活在愛的世界裡的。……當她六十歲時,仍然常存著六歲的童真和十六歲的純真。」
透過文字,彷彿看到了一位小女孩默默地瞅著父親、母親、姨娘,參與之間的深愛與憂愁,看盡人世間的輕仇輕恨,但仍不忘對世間的愛,及對人的無比寬容。
本文則透過髮髻,抒寫母親黯淡的愛情和人世間的寬容。
文中作者善用對比手法寫母親與姨娘。除了不同的髮髻樣式之外,尚有性格、心境與處境上的對比。母親是七月初七才能洗頭的土氣,是閉目養神的沉默,是常望著鏡中影出神的落寞;而姨娘則是一月洗好多次頭的摩登,是與梳頭婦有說有笑的健談,是不時有琅琅笑語聲的受寵。
不同的髻式塑造了母親與姨娘兩個不同的女性形象。姨娘是比較注重外在美的漂亮新潮的女性,而母親則是有傳統內在美的樸素女性。從兩人梳不同的髻中,產生了對比。
髻也有其象徵的意義。在前面,髻象徵了母親和姨娘在與父親的關係上的優劣。母親的髻在款式上敗給姨娘,同樣,也象徵了在父親的寵愛上,母親也是敗陣了。
「髻」象徵母親和姨娘在與父親的關係上的優劣。母親的髻在款式上敗給姨娘,同樣也象徵在父親的寵愛上,母親也是敗陣了。姨娘新式髻就象徵了年輕、美麗和勝利。而母親只梳些老式樣,就象徵了老土和失敗。之後隨著兩人髮髻的變化,也象徵著人際關係與人生觀的改變。
答:(1)起初只有母親和五叔婆時,母親的俏麗,絕勝於「亮著半個光禿禿的頭頂,只剩後腦勺一小撮頭髮」的五叔婆。
(2)以「髻」的樣式,塑造母親和姨娘迥然對比的形象:母親的傳統樸素,對比於姨娘的漂亮新潮;髻的好壞,也反映出父親對母親與姨娘的寵愛與否。
(3)髮的多寡與容顏,形構母親、姨娘在歲月中自身的對比:母親年輕時頭髮是「又粗又長的辮子」,到老年「剪去了稀疏的短髮」,乃至「白髮如銀」,對比中,彷彿所有的憂思愁緒,都隨著髮絲與容顏而有所起落。而姨娘自父親去世以後,「當年如雲的青絲,如今也漸漸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夾有絲絲白髮。」藉對比表現出人事滄桑,衰榮無常。
论琦君散文《髻》中的某些消极哲学
【摘要】琦君的散文《髻》将一个家庭婚姻悲剧写得哀婉优美,但文中流露出的某些消极哲学值得探究,比如母亲的自我封闭、散文对矛盾根源的掩盖与消解等。这些固然来源于琦君的本性基础,以及她所浸淫的文学与哲学基础,但仍使作品的思想价值打了一定折扣。
【关键词】琦君 髻 消极哲学 自我封闭 掩盖矛盾 妥协美化
琦君作为“20世纪最富有中国风味的散文家”①,其至情至性、温柔典雅的文笔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她著名的散文《髻》,用含蓄隽永的优雅语言,将一个家庭婚姻悲剧写得哀而不伤、婉约优美,抒发了韶华易逝、人生无常这一人类的永恒叹息。然而,在沉醉于散文呈现的古典美学、感动于作者的宽容胸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中流露出的某些消极哲学。
首先是母亲的自我封闭以及琦君对此的弱化。琦君的母亲是个普通的乡下妇
① 曹惠民,台港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第10页
女,与受过良好教育、身居高位的父亲存在着天壤之别。母亲如果能尽力改变自己以弥补这种差距,那么她也不至于落入之后的悲伤结局。然而,母亲却固守着从乡下带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散文一开头就提到母亲的头发是又黑又长的,这本可以成为吸引父亲的资本。可是她却坚持着乡下的愚昧习俗——每年七月初七才洗一次头,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恐怕是天方夜谭。所以平时她的头发总有难闻的“油垢味儿”,还梳成一个“不像样子”的“尖尖的螺丝髻”,这实在不能跟“美”沾边。而从大城市来的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女人面前,不要说是处于多妻制时代的父亲,就算是今天的男性,也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后者吧。因此,母亲身上顽固的传统烙印,注定了她的失宠。
当父亲将新的女人带回家来后,母亲的悲伤落寞是显而易见的。“形势逼人强”,如果这个时候母亲能够通过改变自我来与姨娘抗衡,也不会输得一败涂地。但是相反地,母亲采取了消极的自我封闭策略。姨娘以受宠者的高姿态送给母亲翡翠耳环和三花牌头油,刺痛了母亲敏感的心,但母亲只是把它们弃置角落,说自己“不配”、“反胃”;当“我”问母亲为何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时,母亲“沉着脸”,以“乡下人不配梳摩登的头”为理由拒绝了。可母亲现在已经不是在乡下,而且谁又规定乡下人不能梳摩登的发髻、使用讲究的饰品呢?实际上,母亲是退居在“乡下人”的坚硬外壳里,以拒绝与姨娘攀比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受伤的自尊,也就使得自己与美丽、潮流绝缘。这样只会更加失去父亲的心,反而无声地证明了姨娘的胜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母亲的悲惨命运主要是由于父亲的移情别恋,但母亲的自我封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我们无法过分苛责父亲,任何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都希望另一半有气质、有见识,一方面与自己可以有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在社交场合中也能为自己争光。母亲难看的发髻只是她整体形象的一个侧面,想必衣着、谈吐等其他方面也不符合官太太的标准。母亲为了自己的自尊而坚守着“乡下人”的规矩,这只是一种徒然的逃避,只会让父亲离她越来越远。
然而,母亲的这种消极处世哲学,在琦君的笔下以儿童的叙述口吻被小心翼翼地淡化了:在“我”的眼里,母亲一年洗一次的头发虽然“有些难闻”,却给
我一份“安全感”;母亲不肯戴翡翠耳环,“我”猜想是因为舍不得,于是母亲的朴素节俭得到了印证;对于母亲拒绝潮流的行为,则通过表现包梳头“陈嫂”的恶劣态度而转移了读者的视线„„出于对母亲的深爱,琦君并不愿意指出母亲的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对母亲独居生活的描绘上,以母亲境遇的哀婉凄凉与姨娘的备受恩宠进行对比,让读者为之心酸不已,以致对母亲的消极思想也会报以谅解的态度。毕竟,小农社会的狭隘性和封闭性给母亲造成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散文对矛盾的掩盖和消解。在琦君的笔下,似乎造成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罪魁祸首是姨娘,但姨娘也是女人,她所做的也不过是尽力在非正常的社会里谋求生存而已。造成悲剧的真正根源是当时旧式的婚姻制度,包括将母亲和父亲这两个格格不入的人绑在一起的“定亲”习俗,以及为父亲喜新厌旧提供便利的“一夫多妻”制度,千百年来它扼杀了无数女子的幸福。就算是享尽荣华富贵的姨娘,随着父亲去世、容颜枯萎,也一样陷入孤独空虚的境地。
然而,在“我”天真的眼中,只有母亲的水晶发夹、姨娘的横爱司髻,只有父亲对母亲的皱眉和对姨娘满眼的笑,而将生活隐秘灰暗的一面过滤掉了,也就隐去了对父亲以及整个婚姻制度的批判。即使是母亲和姨娘的斗争,也在人世沧桑之后得到了化解。所有的矛盾,在产生时就被琦君不着痕迹地掩饰下去,之后又随着时间的洪流自我消解了,仿佛从一开始它们就没有存在过。琦君并没有控诉抨击,在她看来,岁月自会冲淡一切的恩怨,人世的“爱、憎、贪、痴”,终将归于“木然无动于衷”。所以,她以一颗超越阶级的博爱、慈悲之心,在无形中宽容了所有的矛盾和压迫。她自己也说:“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不透过文学多多渲染祥和美好的一面以作弥补?”②
但不得不说的是,旧式婚姻制度是时代的糟粕,它带给女性的伤害不是通过原谅、宽容就能治愈的。琦君用饱含温情的文字建立了一个几乎没有矛盾的博爱世界,这固然“出自她真挚敦厚的禀赋气质,也得力于她深受儒家忠恕之道影响的老师的教诲,还有饱沾慈悲为怀佛家色彩母亲的感染”③,却也是她对无情现实的妥协和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散文的思想价值打了折扣。这是我们在总体肯
②琦君:《钱塘江畔·细说从头(代序)》,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第4页
③徐学,《当代台湾散文中的生命体验》[J],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1期
定琦君的文学风貌时不能不注意到的。
参考文献:
A.著作类
1、 琦君,《钱塘江畔·细说从头(代序)》[M],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
2、 曹惠民,《台港文学教程》[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
B.期刊类
1、徐学,《当代台湾散文中的生命体验》,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5.1.
2、邓倩,《梳不透,青丝云髻几多愁——品读琦君散文<髻>》,《名作欣赏》,2010.1.
3、危卫红,《对比中一声长叹——琦君散文<髻>的再解读》,《山花》,20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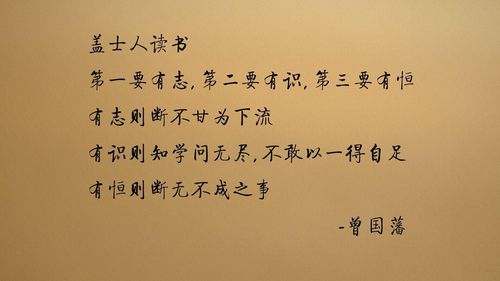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2-28 02:53:33,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370321325389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论琦君《髻》中的消极人生哲学.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论琦君《髻》中的消极人生哲学.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