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发(作者:尺素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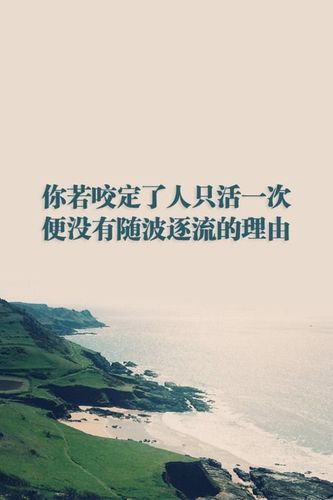
第15卷 第1期
2021年1月古代文明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anuary, 2021 Vol.15 No.1
【帝制中国】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解析秦汉徭役制度的几个概念——事、算与事算王彦辉事、算与事算的含义,在出土的计类文书中基本相同。事的本义是役使,从役使的提 要:客体论即事于国,服事于某种义务。算作为计征赋税的一个计算单位,可以算人,也可以算物,依算征收的人头税称赋钱、算钱,民间或称“算赋”。事算即服事于“算”的义务,在县、乡统计赋钱的年度计簿中指的是算钱。《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应是为上计准备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底本或草案,其中的“定事口”指的是符合缴纳口钱和算钱的口数,也表示在事口中实际缴纳口钱的口数;“凡筭”指符合缴纳算钱的口数,包括复算和事算人口;“定事筭”即实际缴纳算钱的口数。走马楼吴简“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的户计简是为征收“更口筭钱”而编制的最基础账簿,其中,“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的书写格式在口径上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是统一的,但在时态上属于未完成时,“口〇事〇”的“事”指的是应当缴纳口钱(大口钱和小口钱)和算钱的口数,“筭〇事〇”的“事”即“事筭”,指的是应当缴纳算钱的口数。事;算;事算关键词:DOI: 10.16758/.1004-9371.2021.01.007事、算、算事与事算是秦汉及三国吴赋役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涉及到国家的课役对象和被课役者的赋役负担。其中,事、算与算事屡见于文献,“事筭”唯见于简牍。这组概念在文献记载中由于史家对概念本身没有界定,后代注说也往往模棱两可,所以,学界基本是在不加追问的前提下释“算”为按人头征收的赋钱,如口赋、算赋、更赋等;释“事”为徭役,如“勿事”即不服徭役;释“算事”为算赋与徭役,“勿算事”即“不出1算赋及给徭役。”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算赋”,是随着简牍资料的陆续发现而展开的。一、简牍所见事、算与事算的相关研究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披露后,裘锡圭先生在对记录算钱的4号牍进行分析时就已指出,汉初并无一算120钱的规定,“其即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每年出赋钱,人120钱为一算;“口赋”,即民年七岁以上至十四岁每年出口钱,人23钱。对“算”“事”的进一步探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号:17ZDA1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 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250页。81
实,所谓‘算’的本来意思只不过是征收赋税时的计算单位。”《汉旧仪》所谓“人百二十为一算”的制度大概到武帝时期才规定。1其后,马怡先生也指出:“‘算赋’也可以是‘依算出赋’的意思,并不一定是人头税的专称。”2杨振红进而论证曰:“算”是一种计征徭、赋的方式和单位,将“算赋”看成是一种征税方式而非单一的税目更为妥当。3何为“事”?如淳曰:“事谓役使也。”4由“役使”的义项引申为“徭役”原本是通常的理解,但走马楼吴简“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以下简称《年纪簿》)5户计简的书写格式一般为“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6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个“事”数少于口数,“筭”数少于“事”数,后一个“事”数又少于数,如果用通识的“役使”或“徭役”去理解这类结计简的前后两个“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贯通的解释。2004年安徽天长纪庄村19号西汉墓出土的又出现了“事算”“复算”的概念,“事算”之“事”指徭役还是服事,同样需要重新思考。为此,学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长期讨论,或专注于吴简进行研究,或将吴简与凤凰山十号木牍、天长纪庄《算簿》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试图疏通汉魏时期的赋役体系及相关概念的固有含义。7学界迄今的探索主要聚焦于“事”与“事算”的含义,附带出文献记载的“算赋”是否单一税目的问题。从研究思路上说,可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一、徭役说,即“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的仍指“算赋”或“口算”,前后两个“事”都指徭役或与徭役有关。王子今认为前一个“事”指的是按照制度规定应当服役的人数,后一个指的是实际服役的人数;8于振波以为前一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后一“事”指应当服役的人口。9二、赋役说,即“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的指成丁缴纳的“算赋”,前后两个“事”分别指口算赋和徭役。张荣强主张前一“事”指课役口数,即应缴纳口钱、算赋的人数,后一“事”指应征发徭役的人数;10孟彦弘理解前一“事”指82服力役的人数,后一“事”指实际纳筭的人数;11杨振红认为“口〇事〇”的“口”指家内人口总数,“事”指承担国家赋役的口数,“算〇事〇”的“算”指达到服“算”义务年龄的口数(包括成年人交纳的算赋和服行的徭役),“事”指实际服“算”义务的口数。12三、口筭钱说,即“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的“筭”为算赋,前后两个“事”指的都是“口筭钱”。凌文超指出:“口”指口食,即家庭的总人数,前一“事”指缴纳“小口”“大口”钱和“算赋”的总人数,“筭”指制度上规定的纳算人数,1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2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39页。3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4
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第55页。5
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有标题简作“小武陵鄉□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紀簿”,凌文超释“□”为“谨列”,将同盆简命名为“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6
走马楼凡字头户计简的书写格式可举例如下:凡口四事三 筭二事一 中訾 五 十 壹·2907凡口六事四 筭三事二 訾五十 叁·3390凡口七事六 筭二事一 陆·216凡口六事五 筭二事一 訾 五 十 玖·55537
相关研究现状参见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张荣强:《再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以结计简为中心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8
王子今:《走马楼“凡口若干事若干”简例试解读——以对“事”的理解为中心》,2002年北京吴简研讨班讨论稿,收入氏著:《长沙简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7—347页。9
于振波:《“筭”与“事”——走马楼户籍简所反映的算赋和徭役》,《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台北:中华书局,2004年,第189—209页。10
张荣强:《说孙吴户籍中的“事”》,载《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后以“孙吴户籍结句简中的‘事’”为题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4—162页。11
孟彦弘:《吴简所见“事”义臆说——从“事”到“课”》,载《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12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筭”《算簿》“筭”“事”“事”“筭”
后一“事”指实际缴纳算钱的人数;1张荣强近年修正了以往的意见,认为前一“事”释“口”,指应缴纳口钱的人数,后一“事”释“筭”,指应缴纳算赋的人数。2以上诸说大多是把孙吴的赋役制度置于秦汉赋役体系之中提出的,早期研究又缺少乡里户计简的复原与整理基础,因此意见纷呈。对“算”的重新定义,是由凤凰山十号木牍引发的,经过讨论,学界大体认为:“算”作动词用,指计算,如“算人”“算车船”;3亦是统计15岁以上承担徭役和算赋的成年男女人数的单位。4作名词用,是指计征赋税的计量单位,如“二算”“五算”。5每算的数额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西汉武帝时期定制为120钱一算。这些认识是在认可“算赋”为赋税征收的一个固定税目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至于“算赋”是一种计征单位还是一种征税方式,目前还没有统一意见。其实,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话题主要是围绕走马楼吴简《年纪簿》户计简中前后两个“事”展开的,早期研究由于缺少天长纪庄《算簿》所见“复算”的参照,对“事”的含义只能从古注的“役使”义项去解读,因此提出了“徭役说”。近来的研究建立在凌文超对“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的复原工作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赋役说”和“口筭钱说”,尽管各自也存在差异,但基本都认为“凡口〇事〇”的“口”指的是家庭的总人数。“赋役说”由于没有跳出“事”即“徭役”的传统认知,因此对“筭〇事〇”的“事”,或释为“应征发徭役的人数”,或释为“实际服‘算’(包括算赋和徭役)义务的口数”。“口筭钱说”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前一“事”或解释为缴纳口筭钱的总人数,或解释为应缴纳口钱的人数;后一“事”或释为“实际缴纳算钱的人数”,或释为“应缴纳算赋的人数”,区别反映在“事”这一行为是否已经发生。总体而言,以上讨论从不同方向增进了对“算”的理解。但分歧仍然较大,产出歧义的原因有三:一是对“事”的本义和引申义没有做出透彻的解说,二是在时态上没有对《年纪簿》的文本性质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在理解上存在偏差,三是走马楼户计简仅是乡里编制的簿书,对其中的几个概念——口、事、算、事的内涵和限定的对象还难以从整体上予以辨别。而新出《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作为一份上计性质的文书,详尽记录了堂邑县一年内的口数事口数算口数事算口数,以及卒数甲卒数和更卒数,为我们确切理解涉及赋役征派的特定用语提供了可能。二、《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的事、算与事算《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出土于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东北的M147号汉墓,墓主人名“刘赐”,生前曾任萧县令和堂邑令。6该墓出土的11枚木牍,应是刘赐归葬家乡时的随葬品,内容属于不同类别的计类簿书。对《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以下简称《要具簿》)的文书类型,整理者称之为“‘上计’文书性质的文书牍”。7“计簿”亦称“集簿”,胡广《汉官解诂》记汉代上计制度就说,秋冬岁尽,县要“上其集簿”于郡。秦汉实行两级上计制,胡广所云应是县邑侯国上计郡国的制度。郡国上计中央的法令见载于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令文曰:“县1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载《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观点亦见氏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第143页。2
张荣强:《再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以结计简为中心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3 高敏:《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原载《文史》第20辑,1983年,收录氏著:《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4
山田胜芳:《西汉武帝时期的地域社会与女性徭役》,载《简帛研究200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8页。5 高敏:《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载氏著:《秦汉史探讨》,第310页。6 彭峪:《汉代县令家族的身后事——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2018年第2期。按:堂邑,原属九江郡,高祖六年封陈婴为堂邑侯,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废堂邑侯国为县,先属广陵,后属临淮。7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83“算”“一算”“事算”“事”《大众考古》(前201年)
官上计执灋,执灋上计㝡(最)皇帝所。”1“㝡”即总汇、总计。郡国上计中央的文书书写格式和内容,从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M6汉墓出土木牍《集簿》可以窥其原貌。依制度规定,县邑道侯国上计郡国的簿书亦当冠名“集簿”,然土山屯汉墓的文书牍何以名之为“要具簿”?2《周礼·天官冢宰》记“宰夫”之职曰:“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贾疏谓“岁会”为一年会计文书;“月要”为月计文书。3合而言之,“月要”“岁会”又合称之为“要会”,郑司农曰:“要会,谓计最之簿书,月计曰要,岁计曰会。”4据此,“要会”即秦令的“执灋上计㝡(最)皇帝所”的“计㝡(最)”,汉代称之为“计簿”“集簿”。可堂邑县的这份计类文书既不称“要会”也不称“集簿”,或许是因为这个《要具簿》还不是上计簿的定本,而是为上计准备的底本,类似现在常说的“草案”。所以称“要具”,取义应当是这类簿书属于“月要”的年终合计。要、会,其义相同,郑玄注《礼记·乐记》“要其节奏”一语曰:犹会也。”“要具”之“具”,《广韵》曰:“備也、辦也。”可知备、具可互训。由此而言,“要具”即“要备”,亦“月要”之总计、完备。进一步说,按秦汉制度规定,县廷诸曹每月要在日计(《周礼》称“日成”)的基础上总结出“月要”,年终完成年计(诸曹的“岁会”),如里耶秦简的“某某曹计录”。这类年计的簿书称“计簿”,亦即诸曹的“集簿”,如土山屯文书牍的《诸曹要具集簿》5即是。秋冬岁尽,县廷要在《诸曹要具集簿》的基础上分类统计出全县应当上计的各项数据,然后按固定的书写格式写出“集簿”,上报郡国二千石官。《要具簿》记录的内容比之尹湾木牍《集簿》更为全面和具体,除窜入的《堂邑元寿二年库兵要完坚簿》,举凡县城的周长和县域面积、户口数奴婢数及其增减、复口事口算口和事算数、卒数罢癃睆老卒及甲卒更卒月更卒数、提封田与垦田的面积、当收田租的顷亩数、种植宿麦的顷亩数、收事它郡国的户口数、市租钱和湖池税鱼钱、鳏寡孤独和高年口数、一岁诸当食者的用谷数及月食者的身份和口数、流亡户口数、贷84予贫民的户口数等,应有尽有。为讨论起见,现将与本论题有关的口数事口数算口数事算口数以及卒数甲卒数更卒数抄录于次:户二万五千七,多前二百丗七口十三万二千一百四,其三百卅奴婢,少前千六百八复口三万三千九十四定事口九万九千一十,少前五百丗四凡筭(算)六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其千七百七十九奴婢复除罢(癃)筭(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定事筭(算)四万四千三,多前六百廿二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多前五十一罢癃睆老卒二千九十五见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卒复除䌛使千四百卅一定更卒万七千三百八十三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这几组数据未必准确,却可以透过这些数据分析其指向的与徭役有关的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中户数25700,口数132104(含奴婢330),户均5.14口,与晁错所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大体吻合,这个“口”当为堂邑县的总人口。口、复口、事口、算口、事算的记录顺序与走马楼《年纪簿》户计简的书写格式“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大体一致,口、事、算、事指向的人口身份及其含义亦应基本相同。如能切实解决这组概念的具体内涵,或许可以推进走马楼吴简的事、算问题的研究。复口、定事口、算、定事算分别表达了什么1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2
按:“要具”作为一个合成词不见于文献记载,居延汉简有“移计余诸员见要具簿●谨移应书一编敢”(编号:26.10)的断简,当为依“应书”要求上呈某部门的文书,因缺少相关信息,属性不详。走马楼吴简屡见《要簿》的记载,记录的是各粮仓的年度支出或付授的岁计簿书(参见陈明光:《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总第九十三期),与县级上计类文书有别。3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9页。4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67页。5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要,
含义?或许可以从这些概念后缀的数字中找到答案。根据总人口数到定事算口数的记录顺序,事口、算口、事算口数后缀的人数阶梯式递减,在总人口中分别占比75%、52%、33%,说明这些概念除了固有含义还应是一个年龄段的划分界限。“复口”之“复”即“复除”,堂邑县“复口”多达33094人,在总人口中占比25%,恐怕不能简单地用特权人口来解释,且下文另有“复算”口数,包括“复除”和“罢(癃)”,所以,这里的“复口”的指向应为不“事”的人口。关于的含义,学界最初是从“役使”的义项理解的,因此将之解释为“徭役”或与徭役有关。杨振红受天长木牍《算簿》所见“事算”“复算”的启发,以为“事算”当如“复算”一样为动宾结构的词组,据《说文解字》“事”的本义是“职也”,由“职”衍生出“役使”“服事”等含义,新出简牍中的“事”或“事算”都应释之为“服事”。1这一解释推进了吴简《年纪簿》户计简“事”字含义的研究,嗣后的讨论多从此说。其实,“事”在甲骨文中与“史”“吏”形同义通,用作“事”,指“王事”,卜辞多见“古王事”的用例,“意为治王之事或勤劳于王事”。2而王事的发生是和国家起源时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相伴而生的,所谓“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3被征服者既已臣服,就要承担义务,这些义务种类不一,都可归入“服”的范畴,此即“指定服役制”。的概念最早由徐中舒先生提出,赵世超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商周时期的内外服制的“服”,本意“即为服事、服役”,并将之定性为早期国家的产物。4他还认为,这种“‘有事弟子服其劳’式的家内奴役,又以建构仿族组织的方式推及被征服者的身上。”进而,世代相袭。“服”的内容虽然包罗万象,但大体可分为“贡”和“役”。5将之略作推演,后世的“赋”“税”“徭”就是由指定服役制中的“役”和“贡”衍生而来。由此论之,“事”由而定,故《诗经》《楚辞》等旧注,以及《尔雅·释诂》皆谓:“服,事也。”《广韵》谓:“事,使也。”6使即役使,从役使的客体论,就是“服事”。“事”的另一个义项是“服其职业”,《说文》云:“事,职也。”职即职事、职任,如《周礼·夏官·掌固》的“民皆有职焉”、7《孟子·公孙丑上》的“能者在职”8等即是,可见“事”的这层含义更侧重于社会分工和百官的职任。“事”即服事,服事于王事,亦即事于国。战国以后,“事”的内容从类上划分无非“赋”“税”与“徭”。这等“事”并非所有在籍人口都有能力承担,出于各种考虑,不具有劳动能力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口应被排除在“事”之外,按汉代定制,1-6岁的儿童和60岁以上免征赋役的老年人口就属于不事的范围,9称儿童为“未使男”“未使女”,称老年为“免老”。所以,《要具簿》的“复口”指的就当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事”即事于国,自可事之年开始,就要承担应尽的义务。但事口不等于算口,“定事口”99010口,“凡筭”68568口,算口比事口少30442口。这个“筭”无论是“依算出赋”,还是指算赋,表示的也是一个起算的年龄界限和出算的年龄范围。至于何时可事,何时起算,文献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可靠的证据。《汉书·贡禹传》记载:(元帝朝)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101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2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4页。3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越语上》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4页。4
赵世超:《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5
赵世超:《服与等级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6
周祖谟:《广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60页。7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2406页。8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页。9
关于60岁以上者免征赋役的问题,可参见张荣强:《“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10
班固:《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5、3079页。85“事”“指定服役制”“人皆有服”“服”
《汉旧仪》载汉家制度云: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给车马。1《论衡·谢短篇》诘问: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2综合以上记载,民年7-14岁出口钱,15岁以上出赋钱的制度自此成为汉家定制。由此,事口多于算口的30442口就应当指7-14岁的小男小女,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又称“使男”“使女”,具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所出口钱体现的是事于国应尽的义务。另外,从这组数据来看,算口容纳于又不等于事口,说明这个“定事口”是包括出口钱的口数和出赋钱的口数在内的。算口也不等于“事算”人口,在算口中减去复除罢癃算才是“事算”口数。“事算”在《年纪簿》户计简中单称“算”,写作“筭〇事〇”,这很容易误导人们把“算”理解为“算赋”,把“事”理解为徭役,因此才有“徭役说”的提出。天长木牍《算簿》记录了西汉临淮郡东阳县某年度八月、九月的“事算”数和“复算”数,牍文如次:筭 簿集八月事筭二万九,复筭二千卌五。都乡八月事筭五千卌五。南乡八月事筭三千六百八十九。垣雍北乡八月事筭三千二百八十五。垣雍南乡八月事筭二千九百卅一。鞠乡八月事筭千八百九十。杨池乡八月事筭三千一百六十九。·右八月。集九月事筭万九千九百八十八,复筭二千六十五。3中“事筭”与“复筭”对举,这个“事筭”的“事”从事于国的主体来说,就是“服事”,服事的内容是“筭”。算的本义是筹算、计算,在计征赋税的领域使用时确定为一个计算单位。算的对象可以是人,如“算人”的“一算”“倍算”“复算”等;也可以是物,如“算缗钱”“算车船”等,每算的税额在西汉初年还不是很清楚,最迟从汉武帝以后定制为120钱。在一般情况下,86民年十五至免老人一算,此即“人百二十为一算”,晁错所谓“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吴简中称“筭一”。民年十五以上以“算”为单位交纳的人头税,当时称“赋钱”,如果把七岁至十四岁所出“口钱”与“赋钱”合称,文献中称为“口赋钱”,4亦可简称“口赋”,即“口钱”和“赋钱”。东汉以后,“赋钱”也称“算钱”,晁错建议“入粟拜爵”,具体措施之一是“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如淳注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师古解释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5不论所“复”内容是卒是钱,此处已把“赋钱”称为“算钱”了。这种用法也屡见于走马楼吴简,如“右東鄉入民筭錢一萬”(贰·6663),“口赋钱”在吴简中则径称“口筭钱”了。由于“赋钱”称作“算赋”在文献中仅见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八月诏的“初为算赋”,因此才有学者提出“算赋”实际上是“以算为单位计征赋”的意思,“算赋”并非单一的税目名称,而是一种征收方式。6现在看来,把“赋钱”称为“算赋”应当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当“人百二十为一算”成为定制,且称“赋钱”为“算钱”以后,习惯上或者就有“算赋”之称了。郑玄注《周礼正义·天官·太宰》之职曰:“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7郑玄以汉制比况《周礼》,依其文意,筭泉,即算钱。其中,民或谓之赋”一句很重要,“算泉”1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页。2
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谢短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3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牍文公布后,学界对释文屡有新释,所录释文引自杨振红的修订。杨振红:《从出土“算”、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按:垣雍南乡八月事筭应为“二千九百卅一”,杨文误作。4
昭帝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第232页。5 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33—1134页。6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7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90页。“定事口”“以九赋敛财贿”“今之算泉,《筭簿》“事”“二千九百卌一”
按民间的俗称就是“算赋”,称“赋钱”为“算赋”是否由此衍生而来,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天长《算簿》的“事算”即服事算,“事”的内容是“算”,对这个“算”学界或解释为“赋钱”或解释为“算赋”,其实一也。如此,“事算”即交纳“算赋”,学界对此并无异议,只是在时态上存在已然和未然的分歧。“复算”即复除“算”,复除的对象不明。结合《要具簿》分析,“定事筭”口数是算口减去复除疲癃算的余数,即“凡筭”68568)-“复除罢(癃)筭”(24565)=44003口,据此,“复除罢(癃)筭”指的即为“算簿”的“复算”。问题在于,这个“复除罢(癃)筭”的意思是复除疲癃人口的“算”,还是复除与疲癃并列,包括“复除算”和“疲癃算”?笔者以为应属后者。湖南阮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的墓主人死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出土的《黄簿》也有“复算”的记录,简文曰:复算:百七十,多前四,以产子故。1即本年度复算的口数比前一年度多出4人,是由于民产子的缘故。2民产子属于“复算”人口,显然不能列入疲癃。另据走马楼吴简的记载,复除算还当包括:吏卒、穷老、女户等,诸如:東陽里户人公乘□黑年廿六筭一真吏復 玖·6234……互年□□ 筭一給軍卒復 玖·6213其卌户各穷老及刑踵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役 叁·6375以“真吏复”也写作“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给军卒”还包括“给县卒”等。“不任调”据学者研究,即免除赋税和徭役。3“罢(癃)筭”在吴简中分别写作腹心病、刑踵、尪羸等。至此,《要具簿》应是为上计准备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底本或草案,称之为上计类的簿书亦可。“复口”指1—6岁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免征赋役;“事口”指7岁—60岁的服事人口,包括7—14岁的使男女交纳口钱的口数和交纳赋钱的口数;“算口”指15岁至60岁的人口,15岁是起征赋钱的年龄界限,“凡筭”虽然涵盖服徭役的口数,但这里统计的事项主要是征收赋钱的数据,不代表“筭”本身指向服行的徭役;“定事算”即本年度实际服事“算”或赋钱的口数。三、事、算与事算在不同文书的时态差异与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及天长西汉墓木牍专项记录算钱的文书不同,作为县级应上计需要分项统计的数据,《要具簿》的记录格式是:“户〇口〇复口〇定事口〇凡筭〇复除疲癃筭〇定事算〇”。对照《年纪簿》户计简的“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如果把“户计”结计时不需统计的户数、复口数以及通过注记反映的复除疲癃算数排除,其格式就成为“口〇定事口〇凡筭〇定事算〇”,进一步简化的话,即“口〇事〇筭〇事〇”,两者完全相同。根据前文对《要具簿》的分析,“口〇”是堂邑县的总人口数,“定事口〇”的“事口”指的是出口钱和出赋钱的总口数,“凡筭〇”包括“事算”和“复算”口数,“定事算〇”是指实际交纳赋钱的口数。那么,《要具簿》的事、算与事算的各自含义能否对应走马楼吴简的“凡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呢?这就需要对已有诸说中存在的歧见略作归纳。其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徭役说”已经淡出大家的视野。“赋役说”以杨振红为代表,其与“口算钱说”的最大区别,是认为“口〇事〇”的“事”和“筭〇事〇”的“算”都包括承担或服事口赋和徭役的口数。在“口算钱说”中,凌文超与张荣强的分歧一是对前一“事”的解释不同,或认为这个“事”指缴纳口钱和“算赋”的总人数,或认为仅指口钱;二是在时态上或认为后一“事”指实际缴纳算钱的人数,或认为指应缴纳算赋的人数。笔者以为,产生以上分歧的症结可能是对不同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阮陵县博物馆:《阮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2 汉高祖七年春诏曰:“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师古注曰:“勿事,不役使也。”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第63—64页。学界一般将文中的“事”解释为徭役,如今看来应解释为“事算”,“复勿事二岁”即免除二年的赋钱或曰“算赋”。3 参见[日]阿部幸信:《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的“调”——以出纳记录的检讨为中心》,载《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张荣强:《再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以结计简为中心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87(
文书的认知差异造成的。秦汉实行两级上计制,就县级上计的工作流程来说,由于各种基础账簿是以乡为主体进行编造的,1县廷诸曹要以乡所上报的簿籍副本为根据统计年度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分项统计出诸曹的“集簿”,如土山屯文书牍的《诸曹要具集簿》,县廷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并写出上计年报。目前公布的记录算钱的文书较为完整的分别是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天长西汉墓《算簿》、青岛土山屯西汉墓《要具簿》和走马楼吴简的各种文书账簿,吴简中集中讨论的是其中的《年纪簿》。这些簿书的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凤凰山汉墓“记算钱的木牍”应当是江陵县所辖西乡年度月入“算钱”和分项支出的记录。其中,4号牍反映的是市阳里、郑里2-6月征收算钱和交付西乡的详细清单,分别记录了这两个里每月征收的次数、每次多少算、每算多少钱、每次合计多少钱、由里正付西乡。如“市阳三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5号牍反映的是当利里正月、二月的数和算钱支出记录,支出的项目包括转费、吏奉、传送和缮兵等,如:当利正月定筭百一十五正月筭卌二转费正月筭十四吏奉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十号汉墓的绝对年代当为汉景帝四年。2当时以“算”为名的赋钱是以里为单位征收,以乡为单位进行结算的,5号木牍就是在4号木牍各里交付记录的基础上统计的月份总算数和各项支出,因此称“定算”若干。“定算”入钱数扣除各项支出的结余部分,按制要交付到县,如吴简中就有很多县库入〇〇乡口算钱的记录。3整理者认为十号墓出土的刻有“张堰”字样的木印,“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用私印的明器”,4据此,“付西乡偃”的“偃”即西乡有秩或西乡啬夫张堰,4号木牍属于乡级月入“算”钱的记录,5号木牍是在月入“算”钱的基础上统计出来的每月“定算”总数和分项支出的“算”数,这或许就是乡上报县的“年计”底本或抄本。安徽天长西汉墓的年代当西汉中期偏早,整88理者认为墓主人“是东阳县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吏”。5如此,木牍《算簿》就应为县廷某曹编制的“年计”,这份簿书虽然只保留了八月、九月的“事筭”和“复筭”数,但“集”的用法证明这个《算簿》应是对各乡呈报“年计”的汇总,性质或与土山屯汉墓的《诸曹要具集簿》类似。由此而言,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5号木牍和天长西汉墓《算簿》的性质同土山屯汉墓《要具簿》大体相同,分别属于乡和县曹编制的年度“计簿”,在时态上属于完成时,在这个意义上,“事算”指的是已经征收“算”的意思。但吴简《年纪簿》的性质与此不同,因此,对户计简出现的“事”与“筭”就不能按完成时来理解。凌文超在复原“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的基础上,指出这份簿籍是为征收“更口筭钱和訾税”制作的,认为采集简第11盆所出的乡计简——“右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户,口九百五十一人,收更口筭钱合□□一千三百卅四钱”(壹·4985)——应是对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缴纳更口筭钱的统计。6连先用认为这枚乡总计简未见有关“訾税”1
参见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2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3 诸如:“入廣成鄉嘉禾二年口筭錢四百”(壹·5197);“入模鄉元年口筭錢九百八錢”(玖·1682);“入西鄉嘉禾元年口筭錢一千”(玖·2451)等,据《竹简·壹》1677号简的记录,这些“口筭钱”交付的部门是县库,简文曰:“入鄉口筭錢一千九百,嘉禾元年十二月九日□丘□□付庫吏殷”。这笔钱是由某某丘某某人付给库吏殷某的,口筭钱1900显然不是一个家庭全年应缴纳的口筭钱,以所见家口最多的“凡口十六事十 筭九事二 訾五”(叁·6987)计,其中1口交“小口”钱为5钱,9口交“大口”钱为252钱,2口交“筭钱”为240钱,合计497钱;以缴纳算钱较多的“凡口十事九 筭四事 訾五”(叁·5773)计,5口交“小口”钱为25钱,4口交“大口”钱为112钱,4口交“筭钱”为480钱,合计617钱。因此,某丘某人“付库吏”或为代交。4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5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6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8、103—104页。按:简文原释错漏较多,所引简文为凌文超校订。“定算”
的任何记录,因此确信这样的簿书系为征收“更口筭钱”而编制,故可称之为“更口筭钱簿”,并在同属采集简第11盆中找到了“更”“口”(“大口”和“小口”)“算”的分项统计简,初步复原如下:右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户口九百五十一人收更口筭钱合□□一千三百卅四钱 壹·4985其八人更人收钱三百合二千四百 壹·4755其六百八人大口々收钱廿八合一萬七千廿四钱 壹·4464
其三百卅四人小口々收钱五合一千六百七十 壹·4436其二百五十二人筭人收钱一百廿合三萬二千二百卌 壹·49801我们暂且不论这几枚简原来是否与乡计简为一组,也不去追究分项统计的更、口、算钱的总数能否与乡计简的“合□□一千三百卅四钱”吻合,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在于孙吴时期的人头税是分为小口钱、大口钱、算钱和更钱的。2将之与户计简的“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联系起来考察,说《年纪簿》是为征收“更口筭钱”而编制的意见是可取的。据此,它就应当是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征收“更口筭钱”的最基础账簿,具有预征性质。进一步说,凌文超还发现这类嘉禾四年编制的簿籍到嘉禾六年还在使用,根据是小武陵乡下辖的平阳里家庭简中有一简写有:“平阳里户人公乘黄监年五十,六年三月廿三日物故死,訾五十”(叁·4298·31)。不过,户人黄监年五十,却没有“筭一”的注记,与《年纪簿》的整体风格不符,或者还不足以支持上述结论,现可根据已公布的发掘简补充如下:妻惕年卅一筭一 以过年十二月廿日被病物故 柒·5529牙妻姑年卅八筭一 以过年十一月卅日被病物故 柒·5781男姪石年廿八筭一 以五月十八日被病物故
柒·5836□妻取年廿三筭一 以过年十一月廿九日被病物故 捌·2293注记“被病物故”的意义何在?中乡所辖变中里有一简记为:“变中里户人公乘黄條年五十七,條以今年五月十日被病物故,应除”(柒·5176),“应除”的事项不明。前列“被病物故”者虽然缺少后缀语“应除”,但注记的意义应是相同的,不过一种省略写法而已。即这些“被病物故”者按嘉禾四年编制的各类簿书本当“算一”,但在嘉禾五年或六年征收算钱之前死亡,因此要在本年度统计已征收的算钱中减除,所以才做出这样的注记。由此而论,《年纪簿》结计简的“事”“算”的含义虽然与其他计类文书并无二致,但在时态上还属于未完成时。至此,我们就可以对吴简的“口〇事〇筭〇事〇”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口〇事〇”的“事”,指制度规定的需要事于国的口数。《要具簿》的“定事口”涵盖了缴纳口钱、赋钱和服行徭役、兵役的人口,因为其后列出的算、事算、卒、甲卒、更卒口数都是在事口中逐级递减的。尽管如此,这些专项统计的算、事算、更卒等数据又分别指向了实际缴纳赋钱和服行徭役的口数,并不代表这些概念在簿书具有多重含义。《年纪簿》的主要功能是征收“更口算钱”,不涉及派役问题,因此这个“事”指的是在家庭总人口中应该缴纳“更口算钱”的口数,是分项统计缴纳口算钱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凌文超认为指的是缴纳“小口”“大口”钱和“算赋”的总人数,张荣强以为仅指口钱。如果不计缴纳口算钱的时态差异,从后缀的“筭〇事〇”的数字去分析,就会发现凌文超的意见更为可取。为讨论起见,列几枚结计简如下:1 连先用:《走马楼吴简所见吏民簿的复原、整理与研究——以发掘简为中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84、288页。2 按:孙吴时期还没有形成西晋以后那样完备的丁中老小的“丁中制”,大口、小口的年龄划分延续了汉代以来的标准,即7—14岁为“小”,15岁以上为“大”。学界对缴纳“大口钱”的年龄还存在争议,张荣强认为民年15—60岁都要交“大口”钱(张荣强:《再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以结计简为中心的讨论》);连先用认为民年15岁以上都要缴纳“大口”钱(连先用:《走马楼吴简所见吏民簿的复原、整理与研究——以发掘简为中心》,第296页)。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论题,暂不讨论。89
凡口四事 筭二事一 中訾 五 十 壹·2944凡口六事四 筭三事二 訾五十 叁·3390
凡口十六事十 筭九事二 訾五 叁·6987凡口七事六 筭二事一 陆·216凡口六事五 筭三事一 訾 五 十 玖·5523从这类结计简来看,事口与家庭总人口除少数对应外,其余都相差1-6口,说明缴纳口算钱的口数并非家庭所有人口,只是年龄达到或符合缴纳小口、大口钱和算钱的人口。其中,缴纳大口钱的人口同时要缴纳算钱,“筭〇”等同于“大口”若干,在事口中减去“筭〇”就是“小口”。因此,“事〇”指的是家口中符合缴纳口算钱的口数,也是按户征收“小口钱”和“大口钱”的依据。“筭〇事〇”的“筭”是指符合缴纳“筭钱”的口数,“事〇”即“事筭〇”,指的是应当缴纳“筭钱”的口数。“筭〇事〇”的“筭”,杨振红以为指达到服义务年龄的口数,“包括成年人交纳的算赋和服行的徭役”。这一认识从“算人”的宽泛意义来说是正确的,正如日本学者山田胜芳指出的那样,“‘算’与徭役税收相关而言,不仅是以一定的财产评估额为算,还是统计15岁以上承担徭役和算赋的成年男女人数的单位。”1但在计类文书使用时,“筭”一般是有特定指向的。天长虽然没有出现单字“筭”,但“事筭”“复筭”的用法已明白无误地指明了这个“筭”表达的是“算赋”,将之与湖北荆州松柏木牍《南郡卒更簿》一并考虑,当时郡县诸曹年终编制的《集簿》是分别统计的,如此,《筭簿》的“筭”仅指算赋,不包括徭役。同理,《要具簿》的“凡筭”照应的是下面的“定事筭”,“凡筭”减掉“复除罢(癃)筭”得出“事筭”口算,而“罢(癃)”本来就无需服行徭役,这就反证这里的“筭”并不90指向徭役。在“定事筭”(44003人)中只有“卒”(21629人)才是应当服行和实际服行“甲卒”和“更卒”的人数,卒数比事算数减少二分之一以上,这恐怕只能用男女比例来解释,说明妇女按制度规定是不服徭役和兵役的。据此,“筭〇事〇”的“筭”在家庭户计简的语境中针对的事项被限定于“口筭钱”,算口中虽然包涵着应当服行徭役的口数,但“筭”本身并不指向徭役。总之,正因为“口〇事〇 筭〇事〇”标识的意义属于预征备案,是为县廷核实年度收缴税款和考课乡里业绩服务的,所以才列出户内的总口数、事口数、算口数和事算口数,在书写格式上要与县曹集簿和县廷上计类簿书保持口径上的一致。比如《年纪簿》和《要具簿》的书写格式其实就是一一对应的,“口〇”-“事〇”=“复口”,“筭〇-事〇”=复除罢(癃)筭。事、算和事算的含义在这两种性质的簿书中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时态上前者表示的是未然,后者表示的是已然。也就是说,天长《筭簿》和《要具簿》的“事算”表示的是实际缴纳算赋的口数,《年纪簿》表示的是应该缴纳算赋的口数。[作者王彦辉(196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收稿日期:2020年3月2日]
(责任编辑:李媛)1 山田胜芳:《西汉武帝时期的地域社会与女性徭役》,载《简帛研究2007》,第318页。“算”《筭簿》
doctrine of the Changes bad upon ideas of the Five Elements, instead of Yin and Yang. This led
to a result of that the early Sancai bad world model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Five Element system.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al expression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was
finally prented in the Taiji Tushuo( of the Song Dynasty.
《太极图说》)by Zhou Dunyi(周敦颐)Through such an analysis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Sancai model to the Five Elements system,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ilk book from Mawangdui was not later tha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Qin to words: Yellow Emperor and Laozi; Sancai; Book of Changes; Yin and Yang; Five Elements[Imperial China]Title: Shi, Suan, and Shisuan: Explanation of Some Terminologies Concerning 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Bad on Tang-Yi Yuanshou Er-Nian Yaoju Bu………………………/81Author: Wang Yanhui,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t: Shi(事), Suan(算), and Shisuan(事算) are connected terms in the unearthed corvee related
documents dated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Shi means rvice,
usually referring to rving the state as a duty. Suan is a unit of measurement for calculation of human
and material objects. Accordingly, fuqian(赋钱) , suanqian(算钱), suanfu(算赋) were ud as
diversified expressions referring to head tax. Shisuan means the obligation of fulfilling the suan
related duty, which might be mentioned in the county or district level annual statistics as suanqian.
Tang-Yi Yuanshou Er-Nian Yaoju Bu(《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 should be a draft of report for
official statistical purpo. Further comparis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draft with the taxation related
document of Kingdom Wu of the Three Kingdoms unearthed in Zoumalou(走马楼)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period in words: Shi; Suan; ShisuanTitl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eployment of the Prisoners in Qin Dynasty………………………/91Author: Qi Jiwei, Post-Doctoral Rearcher,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t: The prisoners ntenced to conduct forced rvice in the Qin Dynasty include Li-chen-qie(隶臣妾) , Cheng-dan-chong(城旦舂), Guixin(鬼薪) and Baican(白粲),
while the so called Guan
Nubi(官奴婢) was not considered in this category. The dispatch and transfer of the prisoners,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refectures, were actually carried out by the Censors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ey would assign different tasks to the prisoners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 age, ability,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When all the were the same,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of
the job would be considered. The departments that were assigned labor prisoners had no jurisdiction
to change anything.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all the states, the Qin Dynasty faced a situation of labor
prisoner’ shortage becau of its extraordinary words: Censors;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prisoners; deployment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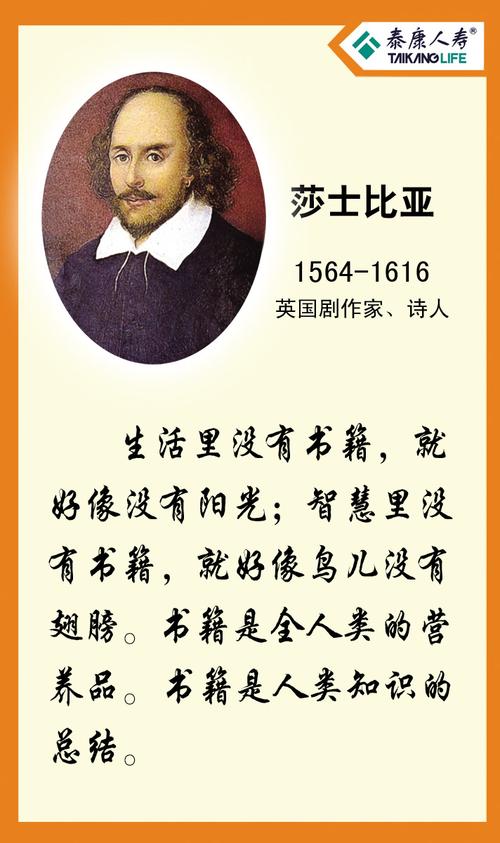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2-28 00:24:26,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3694267244601.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解析秦汉徭役制度的几个概念——事、算与.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解析秦汉徭役制度的几个概念——事、算与.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