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4日发(作者:儒林外史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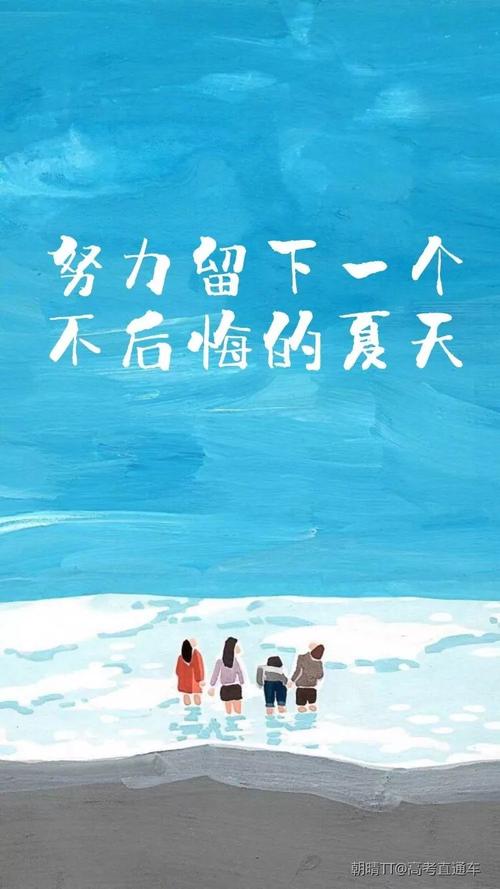
论《中外新报》
内容提要 《中外新报》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二份传教士中文报刊,也是浙江的第一份近代报刊。由于该刊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在国外也只有残本,因而对它的研究远逊于同时期的《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报史学界在《中外新报》的创刊日期、停刊日期、主办者、刊期等方面长期说法不一,对该刊的内容也基本没有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阐析,还原《中外新报》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改变研究滞后的状况。
《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的宁波,是浙江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也是我国最早以“新报”命名的中文报刊,“比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46)仅晚九个月,比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还早了两年又七个月。论其出版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月刊为长。”“换句话说,当时宁波的《中外新报》不仅与香港的《遐迩贯珍》和上海的《六合丛谈》齐名,曾在同一时期发行,而且《中外新报》的编者玛高温还目睹了《遐迩贯珍》的盛衰及《六合丛谈》的诞生和消亡”。但是,自《中外新报》创刊至今150多年间,报史学界对《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的重视与研究远超过《中外新报》,对于后者,许多新闻史著作只有简单介绍,有一些甚至只字不提。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外新报》这一报刊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在国外也只有残本。而且,该刊曾有“两名美国传教士,即玛高温和应思理先后主持,后者所编的《中外新报》未继承前者所编的序号,致使一部分只接触其中一名编者主持的《中外新报》的后来研究者对该刊的创始年月和内容等有所误解和混乱。”
本文试图对报史学界长期混淆不清的有关《中外新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辨析,并就《中外新报》的内容与报刊特色进行分析。
一、报史学界关于《中外新报》的各种说法
在传教士创办的所有中文报刊中,报史学界对《中外新报》的介绍恐怕是最为混乱的一个报刊,围绕它的创刊日期、停刊日期、主办者、刊期等,从晚清到当代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说法,现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中文报刊目录》:《中外新报》,1854年5月创刊于宁波,半月刊,玛高温主编,1861年停刊。
《中国报学史》:“《中外新报》(原名Chine and For-eign
Gazette),为半月刊,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发刊于宁波;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改为月刊,始由玛高温(Daniel JeromeMaegowan)主持。后彼赴日本,乃归应思理()主持。至一八六?年停刊。”
《晚清报业史》:“1854年5月发刊于宁波,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egowan)、应思理(Elias -slee)先后主持。初为半月刊,1857年暂停;1858年复刊,改为月刊。出至1861年停刊。”
《宁波报刊录》:“1858年12月19日(清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创刊,为外国传教士所办。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性质略同于《国闻周报》。开始时由玛高温主持,后来玛高温去日本,由应思理接任。1860年(一说1861年)停刊。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认为此报于1854年创刊,《鄞县通志》认为同治末年刊行,并以为全国有新闻纸之始,都不确。”
《东瀛访报记》:“《中外新报》是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的,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初由玛高温负责,后由应思理主编。……可以订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有关《中外新报》记载中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刊期,戈书作‘半月刊,……(后)改月刊’,实际上名为月刊,实为不定期刊;每期的篇幅,戈书作‘四页’,实为8页;停刊的日期,戈书作1860年,宁树藩曾订正为1861年,这批藏报证明后一说法是对的。”。
《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858年12月19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创刊于宁波。半月一期,每期四页。有边框界栏,正楷木刻。不久即改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止。开始由玛高温主持,后来玛高温去日本,由应思理接任,1860年(又一说1861年)停刊。”。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1858年12月19日(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创刊于宁波。初为半月刊,每期4页。有边框界栏,木刻。不久改为月刊。由玛高温主编,后玛高温去日本,由应思理接任。……有学者称该报‘1854年创刊’,《鄞县通志政教志》称‘甬之有报章盖在同治末年,其名日《中外新报》,为全国有新闻纸之始’,皆不确。《中外新报》于1860年出至第11期停刊。”
《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一)宁波的《中外新报》前后共有两种,第一种是1854年、1856年刊行的,性质略同《国闻周报》;第二种1858年刊行,如《中国报学史》图版所显示的一种,为应思理或者是白保罗、戈柏、绿赐所办。(二)后者在大英博物院收藏中,将其与1854年的《中外新报》相衔接,编为第三或第四卷。除这两种可能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1858年的第一号,是《中外新报》改刊日报的第一号。……至于《中外新报》的停刊时间,……应是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
《宁波最早的一份近代报刊――》:“创刊时间,多作1858年,实为1854年5月;刊期,戈书‘半月刊……(后)改月刊’,名为月刊,实为不定期刊;篇幅,戈书‘四页’,实为八页;停刊时间,多作1860年,实为1861年。”。
二、关于《中外新报》的一系列问题
从上面的十多种论述中,笔者梳理出以下几个问题,依据报史学界近年来的考证意见及笔者的研究心得予以辨析。
1.关于创刊时间
关于创刊时间说法很多,但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第二种,《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这两种说法均源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中国报学史》称《中外新报》“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发刊于宁波”,但该书(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同时附有《中外新报》影印照片,上面清楚标明“中外新报第一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刊”。据此,《中外新报》产生了两个创刊日期:一部分研究者采用1854年的说法,另一部分则采用影印照片上1858年的说法。
问题的症结来自影印照片。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经过考证后给出的说法是:戈公振书中1858年的“这‘中外新报第一号’第一页版面的电版并非复制自《中外新报》的原件,而是取自日本版的《官板中外新报》。”。
日本的近代化报刊诞生于1868年,而中国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六合丛谈》都是在日本近代化报刊诞生以前出现的。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由于长期实行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直接来往不多,一些有识之士想了解西方,只能以中国为主要渠道。中国的一些传教士报刊受到明治维新前日本有识之士的欢迎。最先被带进日本的是《遐迩贯珍》,但它没有被翻印成日文。而《中外新报》与《六合丛谈》带进日本后被翻印成了日文。负责删定、训点、翻印中文报刊的是幕府下属的著书调所,后改称洋书调所。因为是官方机构,经它删定、翻印的书报被冠以“官版”或“官板”字样,如《官板中外新报》、《官板六合丛谈删定本》等。为了方便阅读,经翻印的书都注上日文句号和训读符号。根据卓南生的研究,日本并没有翻印玛高温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只翻印了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即日本的《官板中外新报》都是应思理接管后的《中外新报》的删定版。而应思理接管《中外新报》后并未延续玛高温所编的《中外新报》的序号,又从第一号重新开始排序。所以,《中国报学史》所附《中外新报》影印照片,实为日本的《官板中外新报》,也即应思理续编的第一号。由于报史学界只有极少数人(如戈公振、卓南生、日本的小野秀雄等)曾在大英图书馆阅读过玛高温编的《中外新报》的原件,一般研究者只接触了《中国报学史》所附《中外新报》影印照片,即应思理所编第一号的照片,从而导致了1858年创刊的说法。
因此,《中外新报》的创刊时间应是1854年。
2.关于主办者
《中外新报》的主办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由玛高温主办;第二,由应思理主办;第三,玛高温、应思理先后主办。
出现歧义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一般研究者只接触到其中一位主办者所编的《中外新报》。戈公振、卓南生都曾阅读过玛高温主持时期《中外新报》的原件,而且卓南生说:“《中外新报》的创刊编者玛高温在其报刊名左侧最后一行堂堂正正地写着:‘耶稣门徒医士玛高温撰浙宁北门外爱华堂刊印’”。如此,玛高温作为主办者的身份似无可怀疑。 因此,《中外新报》是由玛高温创办、应思理继办的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
3.关于刊期
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半月刊;第二,半月刊改月刊;第三,不定期刊;第四,玛高温时期为半月刊改月刊,应思理时期为不定期刊。
玛高温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开始为半月刊,封面上写着“每月朔望编售”,即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出刊,但从第三卷即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开始,改为月刊,封面上写的是“每月之望编售”,即农历每月十五日出刊。半月刊改月刊的原因是“买报者少”,“每月终耗费洋银数元”,“现苦亏本”。
而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封面上写的是“或每月或间月编售”,即“月刊”或“双月刊”,实际上却成了不定期刊。据卓南生研究,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前后共出版12号,除第九号内容不详之外,余者皆收录于日本官方删定的《官板中外新报》。从收入《官板中外新报》的11期来看,有间隔一二个月的,也有间隔三四个月甚至五个月的,因此,“不难发现编者虽尝试按其目标,在农历‘每月或间月’之朔(初一)或望(十五)刊印,但在实际上往往脱期,其中有者之间隔甚至长达半年之久。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应思理主持的《中外新报》与其说是定期的宗教期刊,不如说是不定期的宗教刊物。”所以,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虽在封面上标明“或每月或间月编售”,实际上是不定期刊。
因此,玛高温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始为半月刊,后改月刊;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为不定期刊。
4.关于停刊时间
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停刊于1860年;第二,停刊于1861年。
方汉奇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看到了《中外新报》五册翻印本,即五册《官板中外新报》,出版时间分别为1859年10月、11月,1860年9月、12月,1861年1月,这说明1861年1月《中外新报》还在出版。卓南生还看到了1861年2月出版的一期,即第十二号:“笔者看到的日本翻刻版《宫板中外新报》收录着‘中外新报第十二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刊’(即1861年2月)的内容,可见至少是在1861年2月,《中外新报》尚未停刊。”至于1861年2月出版的第十二号是否就是停刊号,“编者应思理及其家人是在1861年4月27日离开宁波返回美国的,从时间段来看,正好是在《中外新报》第十二号发行之后不久。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期间,临别宁波而又忙碌的传教士应思理,似乎不太可能再为这不定期的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付出心血。因此,在未有任何新资料佐证之前,我们可以推断1861年2月号的《中外新报》就是该刊的停刊号。”
因此,《中外新报》停刊于1861年而不是1860年。
三、《中外新报》主要内容及其报刊特色 1.退居次要地位的宗教宣传
由于《中外新报》仅在国外存有少量残本,因而国内报史学界对该刊的内容基本无介绍,或只有极简单的介绍,笔者尝试弥补这一缺憾。因条件所限,笔者未能阅读到玛高温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原件,就以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中外新报》来分析它的内容。
《中外新报》在封面宣称:“拜真神,尊帝王,畏官长,亲爱兄弟,圣经之要旨也。故是报以此数者为宗旨,不敢悖理妄录”。似乎这是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的报刊,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外新报》的宗教色彩比较淡,宗教宣传不占重要地位。
当然,作为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宗教仍然是必备内容。从应思理主持时期的三期《中外新报》看,共刊登了4篇传教文章,即第二号的《辨教说》,第四号刊登于封二的《劝读耶稣圣经说》,第十号继续刊登于封二的《劝 读耶稣圣经说》与另一篇传教文章《回心向道说》。
尽管宗教仍然是必备内容,但三期报刊只有4篇宗教宣传文章,所占篇幅非常有限。这一情况从《中外新报》的目录中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以第十号目录为例:
(封二)劝读耶稣圣经说;宁波;舟山;杭州;上
海;潮州;香港;黑龙江;日本;天竺;萨尔盖西亚;西班
牙;茄佛岛荷兰属;英吉利;佛兰西;花旗;造醋法;造
钢法;回心向道说;附苏州 目录清楚表明,宗教文章所占篇幅很有限,一期刊物不过一二篇而已。所以,《中外新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办以来传教士中文报刊不以传播西教为主要目的的办刊方针是一致的。
2.以报道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报刊
《中外新报》数量最多、篇幅最大的是新闻,这从第十号目录也可以看出来,《中外新报》实际上是一份以报道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报刊。从应思理主持时期《中外新报》第一号首页的一条内容,也可以反映出该刊对新闻的重视:“窃思,《中外新报》所以广见闻、寓劝戒,故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使阅者有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然一人之耳目有限,报内如有报道失实者,愿翻阅之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敝寓,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览者愿之。”
《中外新报》所登新闻,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杭州”、“上海”、“香港”、“日本”、“天竺”、“西班牙”、“花旗”、“英吉利”等。新闻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宁波新闻;第二,宁波周边地区新闻;第三,国内其他地区新闻;第四,世界新闻。
作为一份出版地在宁波的报刊,编撰者非常重视宁波新闻,将其排于头条,而且每期必设,报道的消息非常详细、具体,例如刊登于第二号的“科场作弊案”、“摘心致祭案”、“鄞县公案”、“东乡案始末”等,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宁波官场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中外新报》的新闻触角已经深入到市井间巷。
《中外新报》出版之时,正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外新报》对太平天国运动作了大量报道,而且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例如第四号以“南京”为标题的新闻,批判了洪秀全的宗教;第十号以“杭州”为标题的新闻,记载了太平军攻打杭城的经过。当时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外新报》对此也有报道,例如第十号在“英吉利”标题下,报道了英国议会开会议论对中国战争之事:“近日有耗来自英京伦敦云:两月前,英国大宪会议中华之事,或云去岁天津变故,乃我国钦差与提督等办理未善;或云大清背约是实,非关我国钦差之故;或云攻击中华宜与佛兰西同事;或云不宜与之同事;或云与中华决战,必宜攻人北京方为得要;或云不宜攻人北京,因恐大清国祚,不无有碍;或云先宜攻击各处炮台,后当夺取南京,居中华心腹,以为久计。又有一种桂格尔人,抱煦煦之仁,不忍与中华决战。因此议论纷纭,尚未定夺。”。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言都是珍贵的资料。
对于截稿以后的新闻,《中外新报》以“附宁波”、“附苏州”等方式附录于同号的页末,以区别于正文中的“宁波”、“苏州”等新闻。例如第四号末尾登载了“附宁波”,第十号末尾登载了“附苏州”。
《中外新报》是一份主要刊登新闻的报刊,但同时也刊登一些西学知识。例如第十号刊登的《造醋法》与《造钢法》,介绍了西方造醋与炼钢之术。第四号刊登的《亚美利加土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起,介绍了欧洲殖民者如何教化、驯服亚美利加土人。
3.《中外新报》的影响
作为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二份中文报刊,《中外新报》的发行量超过同时期的《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这从玛高温自己写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昔香港新报,名《遐迩贯珍》,上海新报,名《六合丛谈》,因买之者少,亏截浩繁,故皆截然中止。惟予所作新报,浙宁人稍有买之,故每月虽有亏截,而巍然独存。”
《中外新报》是宁波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也是浙江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它毕竟‘开风气之先’,为长期处在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的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救国自强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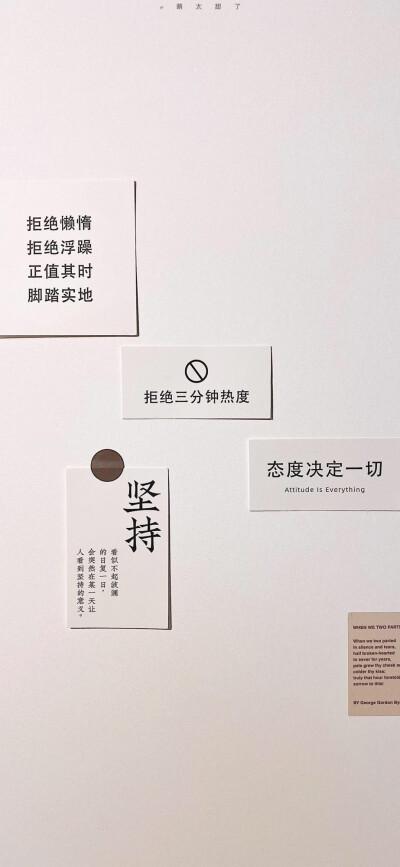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2-14 03:04:53,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249429312094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论《中外新报》-2019年文档.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论《中外新报》-2019年文档.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