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乙访谈: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
文 | 阿乙 胡少卿 受访人:阿乙,作家采访人:胡少
卿记录人:余欣采访手记:余欣采访时间: 2013年5月7
日下午14:00-15:30采访地点:北京某咖啡馆本采访稿内容已
经受访人授权 胡少卿:在你列出的影响你的作家名单中,
有两个不太常见的名字:皮兰德娄和阿利桑德罗·巴里科。
先谈谈你对这两个作家的感受。阿乙:皮兰德娄和巴里科的
书在中国不是特别流行。皮兰德娄,上次有个意大利学汉学
的,他问我,你喜欢哪个意大利作家,我就读过这么一两个。
像卡尔维诺,几次都读不下去,主要是读了《寒冬夜行人》
开头,那个废话,从第一行可以删到第二十行。我看了这个
就一直没读下去,然后可能就错过这个作家了。皮兰德娄在
中国没有几本书,我只买到一本,译者叫“厦大六同人”。
翻译质量是这样:可能有一两篇翻得还挺好,剩下的就翻得
不行。不过,皮兰德娄的每个故事都好,经得起翻译的糟蹋。
我觉得皮兰德娄是一个精品作家,他在很深的程度上,关心
人本身。王安忆在“短经典”总序里,转述了一个他的故事:
一个有家族遗传病的人,他用各种方式,锻炼、节欲、饮食
调理等等,最后突破了那个生命规律,也就是说,可能他的
祖父、父母只能活到多少岁,但他突破了这个岁数。然后他
自杀了。这就是皮兰德娄的故事。我还记得他另一篇写自杀
的。一个人打定主意去自杀,心意特别坚决,但是在路上,
被一个熟人拉去类似卡拉OK、大排档的地方转了大半夜。
这就很荒谬。一个人要去自杀,路上被一个朋友给带走了。
朋友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不能说“我去自杀”,所以跟
着朋友大半夜。最后他只好返回家里,快要到家的时候,在
车上吧,很仓促地把毒药吃了。你就感觉很悲凉:人连自己
的死亡都决定不了。就好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人喜
欢了很久,就要搞起来的时候、很神圣的时候,突然被什么
事延误了。我早期写的《自杀之旅》就是模仿皮兰德娄这篇。
皮兰德娄可以很多年后重读,而巴里科是你读第一遍挺喜
欢,读第二遍的时候就挺厌恶。巴里科可以定位为小资作家。
他就那么几招,其中一招是:先把东西弄得特别好,女人就
很美,男人就特别有才,像那个海上钢琴师,然后把他们又
弄得特别孤独,最后让他们无可挽回地碎掉,毁灭掉,然后
让你心里有个巨大的落差,你读着读着感动得就哭了。这个
模式基本上就是小资作品的全部秘密。村上春树也逃不开这
个。这样的小说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跟人的痛苦没关系,是
人的一杯咖啡。胡少卿:以前的访谈中你提到最喜欢三本书:
《局外人》,《慢》,《茶花女》。这个名单现在有变化吗?阿
乙:现在可以扩充一下,《罪与罚》。还有福克纳的什么我都
喜欢:《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的每一部都经得起推敲。胡少卿:你的《下面,我该
干些什么》里的那种紧张感有点像《罪与罚》。阿乙:最开
始是想模仿《罪与罚》,后来发现能力不够,推倒重来又按
《局外人》的路子去写。胡少卿: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有点
像《罪与罚》与《局外人》的混合体。结尾那个“我”的振
振有词有点不符合他的学生身份了。阿乙:有道理。可能90%
写作的人都会犯的一个毛病是,写小说的时候,结尾都是最
先浮现在心里的。那个谜底早就在心里了。等你耗尽半年时
光,终于写到结尾的时候,你就失态了。胡少卿:迫不及待
要把这个结尾安上去?阿乙:不是安上去,是你一开始写的
时候,这个结尾就存在。如果它是在戏剧里面,就很好。放
在小说里有点突兀,因为前面我太服从小说的规律了。前面
笔法压得挺好,一路在压,压抑自己,让自己不展示什么,
里:为什么他要这么撞一下?他可以不撞,不撞的话他就成
球王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偷懒编的理由。我改
东西已经改得太苦了。胡少卿:看得出来你的文字是很讲究
的,是呕心沥血出来的。和早期余华很像。你的许多语调、
语句都非常之余华。阿乙:早期特别是这样。2004年《新京
报》同事萧三郎约我写一篇余华的书评。我想,我要进军书
评行业了。因为是第一次写书评,很隆重,把上海文艺出的
那套余华都买齐了,集中读了十天还是九天。突然读到中文
有这么好的作家,中他的毒就很深,那个时候我刚刚要开始
写作。胡少卿:28岁才开始读余华……余华对你来说,有点
不用再期待了。胡少卿:《兄弟》是2005年出版的,余华沉
默了又将近十年了。阿乙:是噢,真快。人生有几个十年。
胡少卿:你的小说里我印象尤其深的是两个短篇:《小人》
和《杨村的一则咒语》。《小人》的技巧很完善。小说里那个
中学老师叫陈明义,你把“义”字写成了繁体,是不是有你
的讲究?阿乙:用繁体字说明他的那种自我期许,他有追求,
他是一个读书人,他对《孝经》有了解。胡少卿:繁体的“義”
字,上面是个“羊”,底下是个“我”。我读时产生了“我是
羔羊”这么一种联想——他是无辜的。阿乙:这个解释挺好
的,我还没想到呢,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胡少卿:这个小说
的包袱藏得特别深,许多搞评论的都没看出来。钥匙就在小
说最后一句:“李喜兰便哭,便喊便叫,你这个骗子,你骗
了陈明義又来骗我,你这个骗子。”阿乙:小说设计的时候
很危险,各种走钢丝。最后一句话要把前面搭起来的坚固的
大厦抽走一根线,整个的塌掉,然后就看到另外一栋建筑物
在里头。胡少卿: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脊背发冷,想这个人
怎么这么阴险。实际上凶手还是那个看似被冤枉的冯伯韬。
阿乙:我当时写的时候蛮兴奋的,前后写了一个月,各种谋
算,实际上是想讲一个完美的故事。玩故事是我的一个追求。
我一生想玩这么三四篇故事。不过《小人》里有一个漏洞,
就是这个人为了下棋输了去把另一个人杀掉,合法性不够。
胡少卿:另一篇,《杨村的一则咒语》获得过蒲松龄短篇小
说奖。故事是你从杨继斌那里听来的。小说和他讲的故事之
间有多大的距离呢?阿乙:壳子等于说是他讲的。这个事发
生在他的村庄,所以叫杨村。有两个人因为一只鸡赌咒,就
说你要是没偷我的鸡,我的儿子就今年死,要是你偷了我的
鸡,你的儿子今年死。农村吵架吵到一定份上,就是要赌咒,
才能结束。两人信誓旦旦的。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
有个全球化的东西和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农村联系起来。那些
打工的人带回来很多东西,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巫术一样的东
西,那首歌也是这样,Beyonce是一个全球化的符号。胡少
卿:哦,你有这方面的考虑。我读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阿
乙:其实农村是这样的,大家像聋子一样活在现代社会。不
过,Beyonce,Ladygaga,包括凤凰传奇,都曾经飘过。胡少
卿:现在真实的农村就是这样光怪陆离,一些外面来的很怪
异的东西,在农村里的确存在。阿乙:这个故事我结了四次
牛B。你读第一遍的时候觉得是个天作,第二遍是天作,第
三遍是神作,到第四遍的时候你就看出漏洞来了。漏洞在哪
儿呢?前面90%,他都是按照完全冷漠、冰冷的视角去写的,
到结尾作者开始恋战,舍不得离开这么美好的故事,舍不得
结束它。他写那些人来分尸,有的来锯腿,有的来开肠破肚,
有的拿走了心,有的拿走了肺。那段写得特别油滑。读了三
四遍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作者不懂得控制结尾,不
懂得怎么离开,所以导致这个神作里有个很别扭的问题,就
是前面都很克制,后面就油滑了。而且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就是一个农妇怎么懂得遗体捐赠这一套东西,而且是代签。
这个合理性不够。恋恋不舍最容易带来油滑,语言的油滑,
和那种自恋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兄弟》那部小说,他保
留的就是10%的这个油滑,90%的冷静全部不见,这是很危
险的。我对自己很警惕。油滑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每个作
者都是这样,对自己稍有放纵,你的肮脏、自恋、丑态都会
关系,但你能感到背后这个作者的思想应该是不错的。但是
到《活着》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开始有意识地煽情,这说明
读者和一些市场的反应已经在侵袭他了,已经来找他了。最
开始来找他的都是世界名著,后来找他的可能都是读者的意
见。《活着》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煽情。好多人说读《活着》
的时候半夜起来哭。然后我就想,这个作品可能不行。因为
好多电视剧也是这样,人也是被感动得要哭。《妈妈再爱我
一次》,哭得肯定比《活着》还多。到《许三观卖血记》的
读以后,你所阅读的对象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价值观,这个不
用分谁是谁的。人开始是没有价值观的,人只有在阅读的过
程中、在接受外界的东西时才会形成价值观。人就像一头牛
一样,始终要拿起鞭子鞭策自己去读一些好东西,你读苏格
拉底,苏格拉底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你可以把他的一些你认
为不对的东西抛弃掉,但是你每天晚上看《我是歌手》、看
《中国最强音》的话,你的价值观就是章子怡的,很棒,很
棒,天天就是很棒;就是罗大佑的,罗大佑大家觉得有文化,
但是他真正有多大文化?胡少卿:你写小说一直保持着形式
探索的热情,在每篇小说里都尝试新的写法。你是怎么考虑
的?阿乙:我其实是设定了时间界线的。我从2006年开始
写,允许自己写到2011年,大概五年的时间,这五年里放
肆地去看,放肆地去阅读,放肆地去模仿,放肆地去掌握别
人的技巧。比如加缪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技术
它本身也就完成了。我写《春天》探索了一种形式:这个故
事是螺丝型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
话,永远可以这么读下去,第二节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三节
的最后一句话。到最后,你从最后一章开始读起,倒过来读,
它又是一篇,而且符合你的线性结构。我倒叙,还有不停地
顶针,读起来就比较好玩,这是一个探索,倒过来写,对寻
找一个很悲惨的女孩为什么死蛮有帮助。而如果你从开始写
到她怎么死,这样写的话,反而可能有点怪。胡少卿:现在
比写容易。差点写病了。胡少卿:写作很需要体力。记得残
雪说过,她经常每天要跑五千米锻炼身体。阿乙:吐口水式
的写作不需要体力,而我的这种写作充满了失败。吐口水式
他就能泡出都市文学的好茶。好比张爱玲,她不是名门之后,
她怎么能写出来呢?她写着写着可能就像夏衍一样写个包
身工。打多了麻将才知道打麻将有什么意思。胡少卿:在你
默默无闻的时候,你是如何保持写作的冲动和热情的?阿
乙:开始我对发表的环境是持有怀疑的,我觉得我这么写的
话有谁能知道呢?别人介绍我是一个写作的,我什么都没发
表过,我很羞惭:“我不是我不是,我就是写写博客的。”我
当时立下一个志愿,就是有可能终生就这么写下去,给自己
留一堆,无所谓,反正有博客在那里留着。开始打击我的人
就他一个是聪明的。他在写人与人的隔阂与疏离的时候,完
全是鸟儿在空中飞,充满嘲笑,嘲笑就是他的漏洞。像博尔
赫斯,每个作品何其精妙,但是他的漏洞就在于他的精妙,
就像魔术,你在看完一个魔术的时候,觉得特别精妙,但是
你同时会想,这个魔术是没有力量的。我读完了一定要在崇
了,但是它会一直在那儿。读你的那些生活小片段我感到,
在一般人眼中平面杂乱的现实,到了小说家笔下,会变得很
生动,通过一种洞察力重新组织起来,好像透过表象,抓住
话,或者哪一个作家给另外一个作家写信那种深入和透彻的
交流。你会发现世界上讲文学的人各有各的道理,这个道理
大地震,我会感到悲痛,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生活方式,
完全跟这些创作者没有关系。文艺绝对不能俯就于大众。文
艺就是提供一种有效活着的方式,哪怕最后只剩你自己在看
你自己的作品。胡少卿:你说的这些有效活着的人,既包括
你刚才说的为数不多的创造者,也包括能够欣赏这些创造的
人,是吗?
阿乙:我觉得包括那些向上的人。你在地铁里,你就
看,每个人都像默哀一样,拿着手机,这一排都是。这批人
就是无效活着的人,你可以蔑视他们。胡少卿:如果他恰好
在手机上看你的小说呢?阿乙:很罕见,怎么可能呢。有几
个人在地铁上读苏珊·桑塔格,读亚里士多德?当然,我们
不能去胡乱评说另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每个人活着都有他的
价值所在。但你走上创作的道路以后,你就自然而然地不想
跟那些人打交道。设想那些人,假如临去世之前留下什么遗
言,遗言可能是这样的:我没什么遗言可留,我就觉得相比
着燠热。道路天桥编织起来,日光里像只烁白笼子。蝉影子
鸟影子一个不见。偶尔车过,一街的浮尘日影便喘息起来。
咖啡馆里满地暗暗的阴凉。一盏洛可可式黄吊灯,照着中午
的玻璃镜。咯噔咯噔爬上木楼梯,满眼茶几软椅尽是空荡,
只左壁一个鸦青衣裳的女人,面目埋在电脑屏幕里,一味模
糊下去,倒像是她桌上那盏咖啡杯的背景。中间一个男子睡
着。紫粗布的沙发上,一团乱发像杨树上的鸟巢,栖止在扶
手上。又像秋野的飘蓬。茶几上三两个狼藉杯盘。再远些,
阳台窗子半开,日光斜进来。风吹得绉纱帘子如清波漾漾。
这大屋真是暗哑油画一张。我四下一望,看来阿乙还没来。
空中仿佛浮有依依呀呀的电扇声,瞌睡虫四处飞。“阿乙!”
老师叫道。我一惊。木楼梯上并无人影。飘蓬升起来。一张
惺忪面目铺展开来,满是呵欠。呵欠里说:“你们到啦?”
这人真瘦。火红T恤衫一穿,像个收拢来的灯笼骨,慵慵立
在面前。脚下趿一双人字拖,磨过地面哒哒响。两片双眼皮,
羊角也似,抵牾这城市阴阴的驯化。说话只是粗阔,一点不
像文字的细密劲,其中一股子万事无谓的坦荡,野得很。我
一口齿的嚼字嚼句,立马羞赧下去。又颓唐。存在主义的颓
唐,铺成眼底迷蒙的火,四散开来,看这世间尽是荒诞面皮。
荒诞面皮的海里,浮出一个岛,漫天的碧青碧翠,那便是纯
文学。他眼底那团微暗的火,咻地燃亮。简直滔滔,那火与
言语。皮兰德娄是个金子。巴里科,小资作家,一杯咖啡。
福克纳的什么我都喜欢。《罪与罚》,牛气。白烟飘得无稽无
涯。他斜坐在烟雾里,飘蓬熠熠,像枚万寿无疆老神仙,蓬
想,画名就叫“行走的现代派”。 刊载于《西湖》杂志2013
年第7期
阿乙:重拾“先锋派”的激情 (2013-06-22 00:27:20)文 | 胡
少卿 阿乙在当代文坛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2008年因微博
意见领袖王小山、罗永浩的推崇始渐为人知,并出版首部小
说集《灰故事》。此后保持平均每年一本的频率,陆续出版
小说集《鸟看见我了》(2010年)、随笔集《寡人》(2011年),
中篇《模范青年》(2012年),小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2012年),小说集《春天在哪里》(2013年)。许多人初读
阿乙会联想到余华。不仅因为他的小说像早期余华一样迷恋
暴力和冷漠,还因为他和余华有类似的生活轨迹:余华从海
盐牙医出发,阿乙从瑞昌警察出发,拨开艰难游向中心,才
华是唯一的通行证。2002年阿乙离开家乡江西瑞昌,外出闯
世界。此前他在省内读警察专科学校,做过五年的小镇警察
和公务员。对乡镇生活的反刍构成了迄今为止他几乎全部的
写作题材。他的小说是一个贾樟柯电影式的世界,活跃着妓
女、逃犯、偷情老汉、打牌民警、台球桌边的青年、苦苦思
索的民间哲学家。他的故事可以总括为“一个乡间警察的所
见所闻”,有论者称他是把公安局的档案柜搬到了小说里。
这决定了他的小说充满悬念,使读者获得一种侦破和窥秘的
快感。作者像一个手持利刃的法医,划开表皮,展示生活触
目惊心的内脏。阅读快感,哪怕是一种残酷的快感,是阿乙
小说追求的首要目标。阿乙的文学趣味给人一种“纯正”的
感觉。在浮出水面之前,他曾花费多年苦读卡夫卡、博尔赫
斯、加缪、福克纳、皮兰德娄、巴里科、余华等人的作品,
其飘忽残酷的文字让人联想到残雪《山上的小屋》、余华《河
边的错误》,给人“先锋派归来”的错觉。他自述喜欢把作
品当做一件工艺品来打磨,渴望作品达到“没有一句废话”
的境界。他的语言简洁,准确,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
台湾作家骆以军称阿乙是“动词占有者”。随便拈出一个句
子:“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
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
修改了杨村。”(《杨村的一则咒语》)“变化”和“修改”用
得多好。阿乙还特别在意故事的叙述技巧、结构方式,比如
《意外杀人事件》是一篇努力按照“非”字的几何形状结构
的小说,讲述六个人从六条小巷走出,在中间的大道上遭遇
同一种命运:死亡。在“先锋派”退潮20年后,阿乙重拾
形式探索的激情与冲动,仍然令人尊敬。1980年代的“先锋
派”小说往往模糊了时间和地点,对现实政治进行一种表面
上的疏离,以强化“纯文学”之“纯”。阿乙的不同之处是,
他把时间和地点明确化了,使小说与中国乡村、城镇在世纪
之交的真貌发生连接。形象点说(未必准确),这相当于把
早期余华和后期余华糅合在一起。在广受赞誉的短篇《杨村
的一则咒语》中,村妇钟永连怀疑邻居吴海英偷了她的鸡,
因此赌下残酷的咒语:“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
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第二天,鸡自己回来了。故
事的结局是两个儿子都从南方打工回来过年,吴海英的儿子
开着车带着女友,钟永连的儿子则疲惫地死在自家的床上,
打工地的工作环境摧毁了他的身体。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坚硬
的宿命,它强调的不是咒语应验的偶然性,而是一个大时代
中带有普遍性的悲剧。阿乙一直在追随加缪于《西西弗的神
话》中提出的命题:如何度过荒谬的一生?《下面,我该干
些什么》把对这个命题的思考推到极致。小说里的“我”为
了让空虚的时间变得充实,不惜杀掉一个美好的女孩成为逃
犯。这部作品既有加缪《局外人》的冷漠,又有陀思妥耶夫
斯基《罪与罚》的紧张,它尝试对作家的道德感进行节制,
而只忠于写作本身。当西西弗开始认清并正视自己的命运
时,这同时意味着一种得救。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理解阿乙小
说中的残酷,正如阿乙所言:“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内心坦诚,
去认清那些本就存在的结局、宿命,才会在绝望中清醒,才
能走上自我找寻的道路。”(《杀手阿乙》) 刊于《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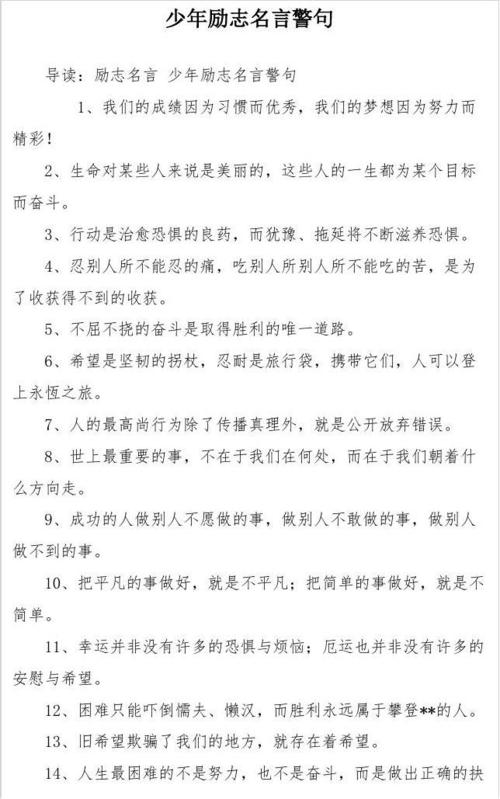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1-28 11:21:45,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1141705228984.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阿乙访谈: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阿乙访谈: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