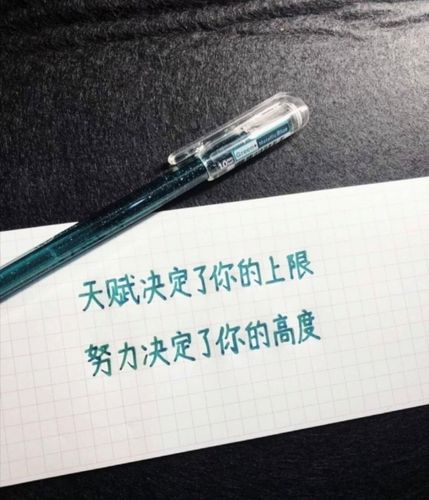
《挪威的森林》的物哀之美
[摘 要] 村上春树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体现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物哀之
美。本文从三方面论述小说物哀之美,首先,作品中直子是个虚无飘渺的人物,“我”与她
的爱情弥散着淡淡哀愁。其次,作品以哀怜伤感语气叙述人物死亡和阿美寮疗养院,也增添
了小说的物哀氛围。再者,小说中微弱细小的生命体上流溢特别的美感,反映作者青春年代
的精神苦闷,散发出一种孤独无助的青春感伤。
[关键词] 《挪威的森林》;物哀之美
Norwegian Wood, the Sentimental Beauty
Abstract:
Murakami Haruki’s most masterpiece, the NorwegianWood reflect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yamato spirit – the ntimental beauty. From three aspects this paper has discusd the
beauty of the novel thing works, first of all, such child is a characters, "I" and her love
playing some light happiness and sadness. Secondly, the work to pity sad narrative characters tone
death and may enterpri, also added a novel sanatorium things atmosphere. Moreover, in tiny
organism novel on weak swelled the aesthetic feeling, reflect the author particularly in the mental
anguish, youth exude a helpless youth ntimental.
Key word:
Norwigian Wood;incomplete;love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49年)的代表作,也是日本当代文坛极具影
响的扛鼎之作。小说自一九八九年七月面世后迅速风靡日本,不仅受到无数读者的欢迎和追
捧,还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学景观:“村上春树现象”。《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文学史上独树一
帜,它继承了西方文学的一些创作元素,却反映出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特质。有学者认为,
村上作品中弥散的淡淡的物哀之美,就体现日本人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经验。侯传文教授指出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完全西化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
现渗透在村上小说中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实质并不像它的外在形态那样西化、洋化。村上的作
品中流淌着日本的情感,洋溢着日本传统的物哀幽玄的美。”田崇雪也指出,日本文学“从
早期的《万叶集》到《源氏物语》,直到今天一直红火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都笼罩
着这种冰凉的‘物哀’气氛。”不可否认,学界注意到了村上作品的物哀之美,并认定这
种日本人特有的文化品质,是导致村上春树在日本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然而比较奇怪的是,
在文学评论具体层面,却鲜有学者从“物哀”的审美角度,对村上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
作出深入的论述。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中的审美情趣,是以“哀”来表现悲哀与同情爱怜浑成的感动
情绪,故传统日本文学中常有一种淡淡的感伤的情调,这是一种日本民族独特的悲剧精神。
叶渭渠认为,哀与物哀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其中以男女恋情的哀
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即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作者所说的“天下大事”
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
[4]
[3]
[2]
[1]
叶渭渠是在分析日本名著《源氏物语》时给“物哀”划分层次的,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物
哀”的本质内涵,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事实上,村上的《挪威的森林》与《源氏物语》
有共通之处,下面,我们从恋情、世相和自然三方面分析《挪威的森林》所体现的日本民族
的物哀之美。
一.直子与爱情
村上春树认为,《挪威的森林》“应该算是恋爱小说”,“腰封上的广告词是我写的:百
分之分的恋爱小说”。这部以“恋爱”为名的小说叙述的是一个三角故事,大学寄宿生“我”
在同学木月自杀后,偶然遇到木月的女友直子并与之发生恋情。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直子
因患精神疾病进入疗养院治疗。“我”在此期间却结识校友绿子,被活泼阳光的绿子所吸引,
由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我”回来寻找绿子,却意外收到直子自杀的消息。“我”不能排解
内心忧思,决定开始外出流浪。《挪威的森林》的魅力在于,作家在叙述男女青年爱情交往
时,无论告别还是欢聚、旅游还是交欢,总能揉进一些失落、虚无的情绪感受,使得小说弥
散着一种淡淡伤感、悲凉的氛围。按照日本文论家本居宣长的观点,这正是“物哀”审美情
趣的最好表达。本居宣长认为,爱情最能表现“真实”人情,物哀在恋爱方面最能得到深刻
揭示,所谓“知物哀”也即知道爱恋之情。他在评论《源氏物语》时认为:“在发挥人情这
点上,没有什么能胜过恋爱(好色)的东西了……如果不写恋爱故事,就难以表现出人情之
深邃、细腻,就按耐不住物哀的深深的心情和捕捉这种心情的细腻的意境。”那么,《挪威
的森林》是通过怎样的恋爱故事来描写人情的呢?确切地说,作者对恋爱主体直子进行细腻
描写,直子的气质及其爱情故事的氛围成为物哀之美的重要源头。
[6]
[5]
直子是一个阴柔虚渺的人物,她身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残缺美。从名字看, 直子无疑
是一个残缺的存在。谢志宇指出,“直”在日语中动词时含有“修正、治疗、复苏、重新”
之意,与名字相对应,“小说中直子所出现的场所大多被涂上疾病、死亡、阴间的色彩。”
[7]
直子的命运一直与忧郁、疾病和死亡相关, 在个性上,直子有一股阴郁的性格特征。直子
身边没有父母亲人,其内心是一个充满孤独的世界。她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中,由于较少
与外界沟通而养成落落寡欢的性格。作者描述直子也并非采用完全写实的手法,他呈现给读
者的是一个平凑、含混、模糊的影子。作者很少直接描写直子的外貌特征,甚至作者与直子
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小说第三章写道:“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
每每是她的侧影。”
不仅如此,直子的爱情故事也笼罩在阴郁与感伤中。直子最初的恋爱对象是病态懦弱的
木月,她与木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像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
蕉,寂寞了就相抱而眠。”尽管这是一段纯洁美好的感情,但他们的爱情虽开花却并未结
果。首先,直子与木月之间有爱无性。直子在阿美寮和渡边说过:“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
没有处女贞操什么的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
直子在恋爱中似乎有意压抑自己,然而木月自杀后,她又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小说中“我”追求直子并与她发生关系,这段爱情同样打上了伤感的烙印。直子在木月
死后陷入悲痛中,这时木月的朋友渡边“我”就成为直子精神上的依靠,换句话说,成为她
空虚寂寞时的救命稻草。然而直子对“我”的感情付出似乎有所保留,他们之间并无多少深
入的精神交流,“每次直子和渡边见面都是四处闲逛,很少谈话。”直子对渡边的态度也是
若即若离,一方面她的思想出现了危机、需要渡边疼她,这是人类同有的本性使然,另一方
面她在感情方面无法给予相应回报。她无法摆脱木月死后留下的阴影。因为她与木月长期缺
乏和谐性爱,她决定在渡边这里稍作改变,在二十岁生日时她将身体交付渡边。然而事后,
她又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内心深处她仍无法忘怀木月。直子对自己的背叛感到深深自
责。爱情是男女之间最纯洁美好的情感,性则是爱情升华的自然结果,然而在直子这里,我
们发现性与爱是割裂开来的。直子在与木月和渡边的两次恋爱过程中,她由于缺乏性能力而
对恋爱对象产生疑惑,甚至由此对人生和世界都产生了悲观思想。叶岗先生认为,“在渡边
到阿美寮后,直子两次在黑暗中展现自己完美的裸体,但这种凄美的浪漫所诉说的,只是生
命体的苍凉。”
[11]
[10]
[9]
[8]
作品以第一人称“我”叙述直子与“我”渡边的爱情,在追忆中充满伤感与孤寂的气息。
这种叙述手法与“我”与直子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爱情相一致,也为小说平添了哀伤之美。
“我”看到孤独、忧郁的直子后,内心浮起惋惜、担心等复杂情感。由于自己孤身在外求学,
所以看到同样孤独的直子时,有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觉。“我”明知直子心系已然
逝去的木月,却仍追随在直子身边,正如渡边所言,“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手臂,而是某
人的手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
愧疚。”在相爱却不能相守情况下,“我”仍然固执地渴望进入直子内心的世界。然而直子
的世界是封闭的,是一片虚无飘渺的真空世界,无论“我”怎样努力,它似乎都是一样遥不
可及。当直子独自进入阿美寮以后,她更是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虚幻世界,再后来直子自
杀身亡,进入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我”跟在直子后面不断追求,却只能看到她模糊的背
[12]
影,当“我”试着向她靠近时,她却宛如一缕青烟瞬间烟消云散,留给“我”的是怅然若失
的迷茫。正是这种对虚幻飘渺人物的追求,以及爱而不得的忧愁与失落,让作品超越了是非
善恶界限,而具有一种唯美、哀伤的色调。
二.彼岸与救赎
按照叶渭渠先生的理解,“物哀”还包括对“世相”的感动。我们认为,《挪威的森林》
所反映的重要世相就是死亡。村上春树在小说的扉页上题词“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声称
“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村上的宣言告诉我们,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
小说采用哀怜伤感的语气展开叙事,死亡特别气息浓厚。作品中许多人物先后踏上了死
亡之路。除绿子父亲因身患癌症病故而外,其他人物几乎都是自杀身亡,而且都是英年早逝,
死于人生最美好的花季年华。木月自杀是只有十七岁,直子年仅二十,初美死去时大约二十
五岁。尽管玲子最终生存下来,但她在年轻时也有过自杀行为。在上述众多的死者中间,直
子姐姐悄然而逝,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家境优越、成绩优秀、才华横溢、青春俊美,按
说是拥有了许多青年人望拥有的一切,却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悄然无息
的离世令人唏嘘不已。
直子的命运是小说关注的焦点。直子在姐姐死后又经历了木月自杀,从此像被一种神秘
力量牢牢控制,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一方面她最亲近的姐姐和男友离世,对她是一
种痛苦不堪的打击,她感到活在世上异常孤独;另一方面姐姐和男友死亡,对她也是一种暗
示、启发或诱惑,让她明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她对遥远的彼岸世界产生了好奇心理。
虽然小说并未详细披露她在这方面的心理活动,但可以推断,她对姐姐和男友去的那个世界
不仅不恐惧,甚至还有几分憧憬和向往,因为那里才有和谐、亲密的关系。相比之下,此岸
生活却让人感到窒息、沉重和孤独。
也许正是因此缘故,直子与“我”的恋爱常被评论者称作是相互拯救。在“我”看来,
直子已陷于令人窒息的境况,渴望把她从孤独中解救出来,用自己的热去温暖她的生命。而
事实上,这也是“我”的一种自救行为,因为“我”同样处于孤独之中,“我”对直子产生
了同病相怜的惺惜之情。在直子这方面,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并试图自救,她在二
十岁生日之际,毅然将身子交付给渡边,就是她对孤独和绝望的抗争。但事后她发现这种抗
争是徒劳的,她的性与爱是分裂的,她尽管与“我”发生了性关系,但她真正牵肠挂肚的还
是木月。换句话说,与“我”的性爱并未解除其精神危机,对她具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个彼岸
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阿美寮带有彼岸世界的色彩。阿美寮本是一个精神疗养院,但小说却竭
力渲染它的神秘性与虚幻性,致使它成为一个颇具乌托邦色彩的所在:“我们来到四面环山
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
路边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升起。随处可见的晾衣杆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
叫着。”阿美寮山清水碧、景色怡人,宛如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更重要的是,阿美
[13]
寮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病,他们乐于彼此间相互帮助。这里的医生与病人一起劳动,人与
人之间充满了真诚与关爱。直子在心信中告诉“我”,人一旦进入阿美寮就懒得出去,或者
说害怕出去。由于这里与外界少有联系,在阿美寮生活的人也似乎成了幽灵。“我”从阿美
寮返回东京后,绿子一见面就吃惊地认为“我”活像见过幽灵。
然而,阿美寮毕竟是一所精神病院,它并不是直子最终的归宿。直子在阿美寮并未治愈
自己的疾病,也未在精神上拯救,她仍有一种莫名的孤独。小说写道“直子孤单单地坐在窗
前,静静地凝视窗外。她怀抱双膝,如同饥饿的孤儿,下骸搭在膝头……我伸出手,想要摸
她。直子却倏地往后缩回身子,嘴唇略略抖动。”尽管村上在小说强调,死并不是生的对
[14]
立面,它只是为了永久地保存生,但直子很快就否定了这样的生活,她在“我”离开阿美寮
后就自杀身亡。阿美寮不是直子所要寻找的世界,她的精神归宿是另一个世界,是活着后面
的彼岸世界。
如果把现代社会看作是此岸世界的话,那么死亡则是一个彼岸世界。此岸世界中人的压
力越来越大,不仅生活节奏加快、活负担加重,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人对此岸生活普遍有
一种失落感,在精神上感到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孤独无依。村上通过众多的死亡事例批判现
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表达出一种对生存的忧患意识。值得称道的是,村上并不认为死亡是最
好的归宿,否定所谓彼岸世界的生活。小说结尾,“我”回到了阳光活泼的绿子身边,因为
绿子是此岸世界的象征,而直子则是彼岸世界的幽灵。“我”最终在此岸世界获得了精神救
赎。
小说中众多青年的自杀死亡,实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他们就像年年盛开的樱花
一样,经历短短几天花期之后,生命便悄无声息地掉落。他们的死亡固然令人扼腕叹息,但
却同样体现了“物哀”之美。日本人认为悲与美是相同的。他们感喟年轻生命的过早凋谢,
就如同他们偏爱残月和落花这类自然景物一样,认为残月、落花甚至生命的逝去,都集中体
现了生命的无常。在残月和落花上面寄托了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而人们欣赏残月和落
花其实就是在品味美感。这是日本人所谓“物哀美”的特质。
三.生命与物伤
“物哀”中的“物”自然也指自然界的物体。“物哀”就是通过外界客观存在的物象来
反映主体内心悲哀、苍凉的主观感情,是外在的物象成为内心情感的载体,这样在审美过程
中,人与自然和谐地统一起来,从而达到一种物我同悲的审美境界。日本人对身边物体的观
察可谓细致入微,他们尤其偏爱一些细小清丽的物体,认为这些微弱、细小的生命体上流溢
一种特别的美感。村上春树的作品大体上反映了日本人这一审美情趣。在村上笔下,静谧的
乐曲、芬芳的小草、清凉的山风、起伏的远山、甚至鸟鸣犬吠等,洋溢着日本传统的物哀幽
玄的美。
首先,村上将小说取名为《挪威的森林》显然是要表明这是一部青春感伤小说。作品叙
述“我”在三十七岁这年(即作者认为得青春即将过去),因在飞机上听到《挪威的森林》
的旋律,情不自禁陷入对青春往事的追忆之中。村上春树以歌曲名字展开叙述是别有一番深
意的,这不仅显示作家高超的叙述技巧,还因小说与歌曲实际上存在一定的互文性。《挪威
的森林》是甲壳虫乐队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静谧忧伤、令人心醉神迷的曲子。歌词大概是:
我有一个女友,或者说她曾拥有我,她领我看她的房间,“不赖吧,这挪威式的木屋?”她
说她明早还要上班,并爽声大笑……我醒来时独自一人,鸟儿已经飞去。我生了堆火,难道
不好吗,在这个挪威式的小木屋?小说中的“我”听到歌曲《挪威的森林》,尤其是“我有
一个女友”一句,不禁想起自己的昔日女友直子,因为直子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更重要的是,
“我”和直子的爱情很像歌中所言,“我醒来时独自一人,鸟儿已经飞去”,甚至可以说,歌
曲高度浓缩了小说的主题和内涵。“我”和直子曾经相爱,“我”也曾渴望进入她的世界,可
当“我”某天回头找她,她已悄然而逝、音容不在。相爱与永诀、生离与死别,仿佛都是一
夜之间的事情,一觉醒来即是沧海桑田。
歌曲《挪威的森林》引发了“我”对青春往事的酸涩回忆,以及对心爱女友直子的伤逝
之痛。小说叙述就在这种哀婉的基调下进行,自始至终充满淡淡的忧伤。这种悲情叙述昭显
了日本人万事皆空的虚无思想。正如学者指出,“村上春树写青春,青春逝去,写生命,生
命不再……他在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同时又是在传递日本文化的特质——无常观。众所周
知,日本人生活在火山、地震频发的岛上,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感到生命无从保证,整个民族
原本就有一种无助心理,佛教传入以后,佛教“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万事皆空”等思
想影响了民族心理,日本人的无常观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无常思想产生对人生的悲哀和伤
感情绪,成为日本人特有的审美心理。村上小说与歌曲一样细腻委婉,也因这种情绪而富有
阴柔之美。
其次,小说中的萤火虫意象也很有韵味。萤火虫是“敢死队”送给“我”渡边的礼物。
“我”将它装在一个空咖啡瓶里,它在夜里散发出淡淡的微光,整个世界因此显得静寂和冷
清。萤火虫是如此虚弱不堪以致“我”放它出来时,它竟忘记了飞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
才“蓦然张开翅膀……飞快地摇曳着光环,仿佛要挽回失去的时光。”这里的萤火虫具有
[16]
[15]
特别的象征意义。它不仅反映了作者孤独无依的内心感受,也是现代社会个体孤单和无助的
精神投射。与其说萤火虫是一只虫子,不如说它是作者本人的灵魂所寄,甚至可以说,反映
了二十世纪六十年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苦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全日学生共同斗争阵线”
(简称“全共斗”)掀起反对运动,从表面看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其实质却是日本
民众长期以来不满日本教育和政治体制的情绪总爆发。这次学生运动既没有纲领性文件,也
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完全凭学生的狂热的斗争激情。在日本当局的高压下,学生的反对运
动最后归于失败。村上与同时代的青年学生一样产生幻灭感,由此滋生空虚、落寞、孤独、
颓废的情绪。作品中萤火虫消逝之后,它那微弱的光亮仍长留在“我”的脑海,“仿佛迷失
方向的灵魂,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村上借助小小萤火虫反映出一代人的内心
呼声,也反映了孤独无助的青春感伤。
尽管村上春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挪威的森林》“也不是青春小说,青春小说这个词实
在用得满是污垢了”,(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18页)
但他又宣称要在青春行将结束之际留下些纪念的文字,所以一些评论者认为《挪威的森林》
就是一部“村上春树对20世纪60年代青春生活的伤情悼时之作。”
总之,小说《挪威的森林》在多层面营造“物哀”氛围,彰显了日本文化传统中特有的
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主要体现为由人、物、景触发的感伤,它与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尽相
同,它不是表现个体人物特别是英雄毁灭的崇高感,也不是要引起观众内心的恐惧从而净化
灵魂,而是通过普通人物和日常生活景物的描写,通过主体与这些人物和景物的交流,获得
[18]
[17]
一种哀伤的情绪感受和婉约的美感。小说自始至终弥漫一种淡淡的感伤和怅然若失的情调。
村上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感兴趣,他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大热衷,他关注一个自杀的年
轻女子,通过含蓄蕴藉的景物描写和她细腻的心理感受,反映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察与感悟,
特别他内心那种如烟如梦的内心感伤。小说呈现出来的独特魅力既反映日本人的美学心理,
也揭示出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
注释:
[1]侯传文.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18
[2]田崇雪.文学与感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3
[3]王邦维.比较视野中的东方文学.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275
[4]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1
[5]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宁夏人民出版,2005.218
[6]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4
[7]谢志宇.解读《挪威的森林》中的种种象征意义.北京:外语研究,2004.75
[8][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69
[9][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47
[10][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5
[11]叶岗.走向文史研究前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06
[12][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7
[13][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21
[14][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71
[15]张士立著. 挪威的森林悲剧探析.安徽:安徽文学,2009.211
[16][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0
[17][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1
[18]叶岗.走向文史研究前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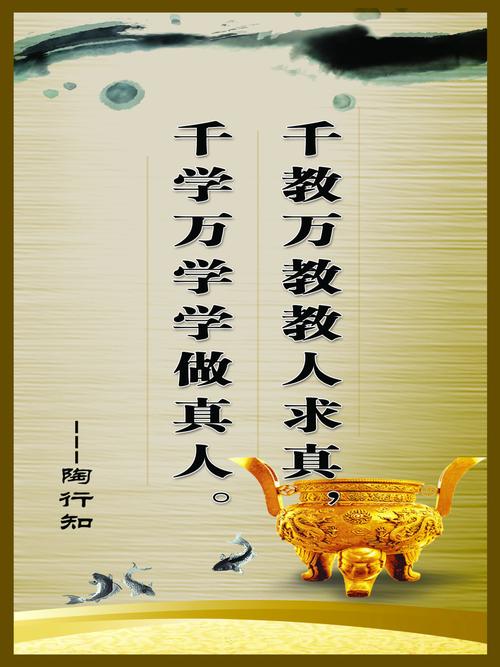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1-28 10:14:23,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1137664228926.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挪威的森林》的物哀之美【毕业作品】.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挪威的森林》的物哀之美【毕业作品】.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