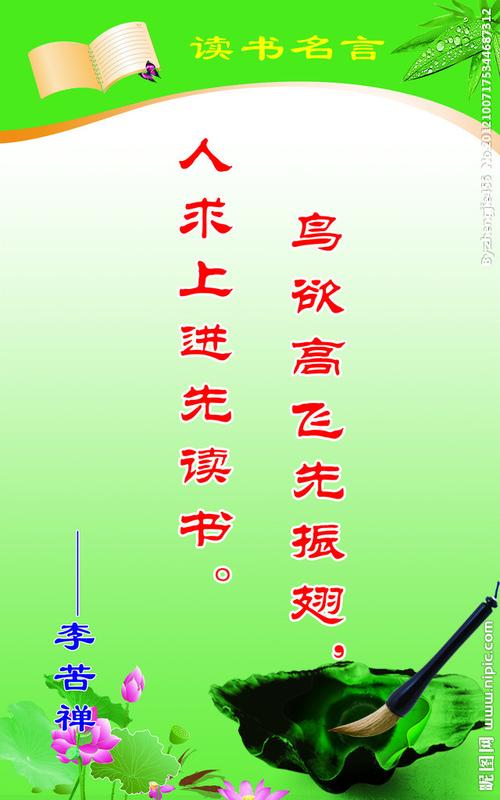
明初黎贞撰《陈博民谷食祠记》与桑园围的水利环境
吴建新
【摘 要】以辨析明初黎贞撰《陈博民谷食祠记》的真伪入手,从文献、人物真实性
等方面,论证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基围和桑基鱼塘区——桑园围在洪武二
十九年筑塞倒流港的史实.通过分析,说明了明初筑塞倒流港导致的西北江下游三角
洲水利环境和治水方式、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防潮和防涝双结合的治水方式,不仅
需要增高、加固堤围,还需通过挖深鱼塘以蓄水防涝.挖出的泥覆向池塘周围,淡水养
殖业和基面种植业结合,引起基塘农业出现.在桑园围的最低洼地区九江和龙山、龙
江等地形成珠江三角洲最早的桑基鱼塘区.明初筑塞倒流港合围动员修围还为清代
桑园围“合围通修”的水利社会形成提供了文化资源和模式.
【期刊名称】《古今农业》
【年(卷),期】2018(000)002
【总页数】10页(P74-83)
【关键词】桑园围;水利环境
【作 者】吴建新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正文语种】中 文
位于广东西北江三角洲下游的桑园围,位跨南海、顺德两县,是珠江三角洲最重要的
堤围,被称为 “粤中大围”。它是明清至民国华南最大的淡水养殖基地、蚕丝中心、
桑基鱼塘区,清代耕地面积6000余顷,是明清至近代广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地。桑
园围的地理基础:西北江从三水平原直下南海、顺德境,沿着西樵山呈从西北向东南
倾斜的地势。西樵山以下直至南海九江一带,远古是一片汪洋大海,中间点缀着不少
岛屿,唐宋元以后海岸线退缩,西樵山以下便逐渐冲积成陆,岛屿变为陆地上的山坡。
宋元时期人们沿着桑园围平原两边的西北江筑成基段,将山陵与人工堤壆连接在一
起,逐步形成桑园围的西基和东基,由于最早的桑园围的出水口水位还高于出水口以
下的部分,故没有必要在桑园围的下游合围。但在桑园围的顶部,在宋元时期就一定
要合围,因为此时西樵山以下平原冲积地已经被开发很多,遍布农业聚落,桑园围顶部
不合围,西北面三水平原潦水一来,西樵山以下地区便汪洋一片。桑园围顶部的合围
可能在宋元之间多次进行。
以往对桑园围的研究多集中在清近代。而对于桑园围的合围时间,以及合围之后明
初的倒流港筑塞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变迁,却少涉及。西樵山下游在南海
九江的出水位在元明之间有一次筑塞工程,即将河水倒灌入围的开口处倒流港堵住。
明初的倒流港筑塞问题,与桑园围水利社会的形成、基塘农业的起源都有极大的关
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有一定的研究。[1]但说法不一。本文主要从
明初人黎贞撰 《陈博民谷食祠记》的真伪分析入手,考证桑园围的合围时间和明初
筑塞倒流港这一事件是否存在,并进一步探讨明初桑园围的水环境和基塘农业的起
源问题。
《桑园围志》卷首的第一篇文章,即明初人黎贞 (1358--1416)[2]撰 《陈博民谷食
祠记》(以下简称 《记》),是研究珠江三角洲水利史重要事件——洪武年筑塞倒流
港的一篇重要文章。徐晓的最新研究怀疑此文的真实性。[3]而笔者认为 《记》的
真实性是存在的。
质疑者的意见依据是,一是明代方志没有记载 《记》,只是清代方志才提到,二是光
绪本的 《黎秫坡集》才收入此文,三是说陈博文 (一作民,民与文,粤语同音)到京师被
皇帝召见,“在当时制度环境是不可能的事”。[4]这些证据都不能确立。下面阐述
笔者的意见,求教于方家。
二、不能以方志没有记载否定《记》的真实性
明代方志没有记载 《记》,却不能否认这篇文章的存在,因为 《广东碑刻集》、
《广州碑刻集》以及东莞、顺德等地的碑刻集中的不少明代碑刻都是在明清方志的
“金石略”中没有的,我们就能说这些碑刻是假的吗?《陈博民谷食祠记》是作为九
江人纪念陈博民祠庙的碑刻存在的,因此,它不为明代方志所记,不足为奇。因为放在
庙宇祠堂中很多碑刻,特别是明代的,大都没有收入明代方志中,但不能据此为伪。与
黎贞著《陈博民谷食祠记》一样,没有收入明代方志的祠堂碑刻,还有黎贞著 《后晋
朝请大夫行录记铭》,民国 《开平县志》卷四十一《金石略》收入,写明是 “正
书”,末署 “永乐九年辛卯 月邑人黎贞攫 (言字旁)”(时开平未从新会分出),“右刻
在沙冈张氏始祖庙”。[5]此文在 《黎秫坡集》卷七。[6]明代洪武年陈博文主持筑
塞倒流港,改变了桑园围尾闾的潮水倒灌状况,后人立 “谷食祠”纪念他,并请诗人
孙蕡的学生,新会人黎贞撰文,立碑在祠中。《记》说 “二三子拳拳若此”,就是指
与陈博文同时的九江乡的大族精英热衷此事。此祠在明初建,后毁,崇祯年又重建,碑
文又立。后又毁,清代乾隆、嘉庆之间重建。祠毁而碑存在,或碑文还流传于民间。
这种情况在珠三角不少碑刻都有。故不能以此文不见载于方志而否定它。
三、黎贞著作散失很多,但不能因此否认黎贞撰 《记》
黎贞在世时,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著作。今本 《黎秫坡集》首序为明初
王进撰,其中提到黎贞其诗 “(以上略)无雕琢浮靡之习,有浑厚谆雅之气。当时名公
无不慕之。惜乎手稿有所不存,其嗣子惠吉深概之。每闻乡之人传颂,辄手录之,间于
旧篋得其一二,遂汇编成集,名 《竹居诗集》。命予友盖孚张君征予言题其端。(以
下略)”,末题 “宣德二年春二月吉旦翰林院侍讲吴郡王进 书”。王进,明史无本传,
惟提到洪熙年, “士奇荐侍讲王进”。[7]据此序,明初黎贞诗名盛于诗歌界,故王进
乐于为黎贞诗集作序。而且从王序看,黎贞在世时,并没有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集以
待付梓。这样,黎贞著作散失就不足为奇了,诗歌也只是在诗界流传,至其子编 《竹
居诗集》时,诗歌亦收不全,更遑论黎贞为人作碑铭之类文章。到陈白沙时,看过黎贞
著作,恐亦是《竹居诗集》,陈白沙成诗四首,第一首云:“曾从父老问前因,说道才情
迥绝伦。今日偶然文字外,分明文字一般春”。[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集初刻
于嘉靖庚戌,岁久散佚。”[9]今本收嘉靖二十九年新会潮连人区越序言:“秫坡著述
虽富,日久拓落,已失锓梓”。区越在致仕之后,搜集其遗稿,“散佚之余,百不存一……
因公之裔孙善积,访求搜录,复得公诗文若干。”[10]则嘉靖二十九年刻 《秫坡集》
时,所收黎贞遗作亦已经十分困难。康熙 《新会县志》卷末 《艺文篇籍》记载有黎
贞 《秫坡集》十卷,《家礼举要》四卷[11],清初 《黎贞秫坡集》尚可见到,但清乾
隆时十卷本的 《秫坡集》已经失传。道光年记载,《秫坡集》,“国朝康熙丙寅,其
后人有搜集重刊,凡诗词赋三卷,杂文四卷,卷八附以赠言。贞少从孙蕡学诗,蕡即其所
编次,虽所造未深而风格尚为遒上。惜此本掇拾于残阙之余,其菁华已失,不概见
矣。”[12]清光绪年其后人重辑《秫坡集》,将散佚的碑刻等黎贞著作收入,是很自
然的事。所以不能将散失的黎贞作品称为伪作,除非能在文章中找出作伪的痕迹和
动机 (《记》中所述人物可考,见下文)。如果九江人要为 《陈博民谷食祠记》作伪,
可以伪托其他有名的人,如陈白沙,为什么伪托比陈白沙名气差得多的黎贞呢?
笔者搜集到一篇黎贞撰 《(开平)儒林余氏族谱序》,内称:余氏为北宋余靖后裔,散居
新会 (时开平未从新会分出),“皇明永乐七年,(余氏)世孙税宁捧其族谱谒请序,”因
为余氏 “瓜瓞蔓衍,子孙胜衣者数百计”。[13]
今本 《秫坡集》卷五 “序”有三个族谱序,分别为伍氏、赵氏、李氏,独不见余氏
谱序。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余氏族谱纂者的伪造。这说明,清代,黎贞的廿一世孙在重
编《秫坡集》时并没有搜罗全其先祖的文献,散佚的黎贞作品可能不少。
四、《记》中的人和事在方志上有记载
《记》所记人和事,都是有史可据的。如 《记》中提到:“里人岑平汉等走邻壤新会,
请记于予 (黎贞)。”岑平汉, 《九江乡志》有传。顺治 《九江乡志》,卷之四 《潜
德列传》:“岑越锐......以粮长奉檄解马料赴军前。......父号云庵亦负气任侠,与陈博
文友善,塞倒流海,皆与有力。”岑越锐的父亲云庵即岑平汉,与陈博文同筑塞倒流港,
并参与建 “谷食祠”,则陈博文年长于岑平汉。光绪 《九江儒林乡志》有三段关于
岑平汉的记载:
乡人岑平汉,义士也。陈博民叩阍大筑桑园围,平汉与有力焉。家富于财,自松冈蚌山、
龟山及大塘数里,皆其产业,乃于平田筑鸭舌基以为保障。乡邻利赖。义士祠墓皆在
凫山。[14]
正统五年,义民岑平汉在广西山东两省大饥,朝廷劝赈,平汉与诸弟 “出谷千石”,得
朝廷 “赐敕褒美,劳以羊酒建坊旌义,蠲免差徭”。[15]
岑平汉, “负气任仪,与陈博民友善。洪武二十八年博民上书塞倒流港,得免西潦患,
平汉实与有力。又独捐资别筑鸭舌围,与桑园围子母相顾,群庆安澜。”[16]
岑平汉大致是洪武初年人,到正统五年他捐谷赈济并被 “赐敕褒美”时,已经九十多
岁了。此人既然在顺治到光绪年的乡志中出现,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绝不可能
造假。
参与陈博文筑塞倒流港的还有另一人,关可达, “好义急公,闾里推为一乡之长,洪武
间陈博民增筑桑园围,可达与其役。”[17]
岑平汉是富户并且曾经为粮长,关可达为 “一乡之长”,岑、关姓皆为九江大户。从
《九江乡志》的记载看,筑塞倒流港是九江全乡的大事,陈博文背后其实是势力雄厚
的九江乡宗族集团。所以九江乡志将此事作为大事记载下来。[18]
五、明初朝廷对广东的水利制度背景证明陈博文上京 “奏筑”的史实
从洪武年到正统年朝廷对岭南的水利管治政策来说,陈博文上京述乡水利事,求准施
工,当时的制度环境允许,面见皇帝则不一定。
明代, “东广未设水利之官”[19],但明代初期民间可以 “奏筑”,请求中央政府派
人令地方政府建水利工程。这是明初水利政策的特点。笔者统计了明代前期广东民
间向朝廷奏筑水利部份情况,列为下表:
资料来源:(1)雍正六年,雍正揭阳县志,卷1,山川 (2)崇祯东莞县志,卷之二,堤坡;(3)道
光 《鹤山县志》,卷之一,建置,水利 (4)顺治 《九江乡志》,卷之四 《潜德列传》;(5)
正德 《琼台志》,卷七,《水利》(6)康熙 《肇庆府志》,卷十六 《水利》(7)崇祯
《肇庆府志》,卷十八,水利志》(8)《宣宗实录》卷25(9)《英宗实录》卷
134______年代 地点 奏筑者 工程名称及其他 资料来源洪武间 揭阳 老人
朱广 洪沟堤,在霖田都,东起洪沟桥,西至赤嵌,长十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奇,障田数百顷。(1)洪武26
年 东莞 老人黄良佐 三村圩,长七千余丈,包围三村,抵捍东江,派分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北,两流潦水,保护田地三百余顷。
(2)洪武二十七年 新会 乡人冯八秀 明洪武二十七年乡人冯八秀等赴告工部,差
员刘永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修筑灌田223顷。(3)
洪武二十八年 南海 乡民陈博文奏筑塞桑园围倒流港,上自丰滘,下至狐狸,绕龙江
三水,周数十里,各筑高五尺。桑园围从开口围变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口
围。(4)__洪武二十八年 琼州府 乡民潭父老 琼山县滨壅圩岸崩溃,请求批准修
复。 (5)__洪武二十九年 新会 乡人黄原善等 坡田小水围。赴告布政司札县
兴筑,灌田7顷。 (3)___洪武三十年 新会 乡人冯元仲 越塘圆州围。差员刘恩
诚同县兴筑,灌田53顷。 (3)永乐间 肇庆府 民严显 永乐间民严显奏筑,水流
二十余里,灌五都民田15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余顷。
(6)___永乐十一年 新会 乡人黄佛成等 麦村小水围。工部差员江渊同县兴筑,灌
田6顷。 (3)永乐间 高要四会 乡人黄阿思 丰乐大堤围,长13837丈,连四会,
共跨四都,田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塘1000余顷。永
乐间乡人黄阿思等奏筑 (7)宣德二年 高要 县民奏 祟化乡田二千余顷地势低,
每遇水患民多艰食,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修筑基围
1700丈。(8)正统十年 海阳县 民萧菇 (王缶)登隆等都俱置沟通水溉田,民其利
焉。惟隆津等都亦去溪不远而无沟,通旱田无所赖。请求令所司开沟亦如登隆都为
便。事下工部核实于潮州府,府称如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言善。(9)
上表所列的 “奏筑”,不少是大型水利工程,如南海、顺德境内的桑园围筑塞倒流港,
牵涉地域还有三水和四会,还修复、新建堤围数十里。揭阳洪沟堤也长十里。高要、
四会的丰乐大堤围,长千丈,共跨四都,田地塘1 000余顷。东莞的三村圩,长7 000
余丈。甚至也有灌溉田地数顷的小型工程。
一些例子虽然没有说明是民人上京赴告,但国家有可能从民间得到信息,或者地方官
直接上奏,中央批准而差官修筑。《明实录》有记载地方的水利建设,表明是中央派
人督修。
这说明在中央专制集权强大的明初,朝廷可以直接根据民间提供的信息,用国家力量
推进水利工程的实施。这对促进岭南这个不太发达地区的水利事业有一定的作用。
广东大规模的陂塘、堤围工程都是在宋元以后才出现,明代前期岭南不少地区的水
利建设还是很落后的,有的地方甚至在洪武年以前从来没有过陂塘设施。如吴川县
“邑旧无陂塘,洪武二十八年工部勘合为民兴利除害,时县令曹定令民修筑,积水以防
岁旱,自是渐称沃壤”。[20]可见明代前期的民间 “奏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
王朝对岭南水利的重视,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发展。[21]明初民间奏筑没有形成经常
性的制度,正统年以后便不见实行,万历 《新会县志》的作者说:“昔陂围多鸣之上,
上使人为筑之,今则皆民力而已。”[22]
认为 《记》为伪者的意见,依据之一说陈博文到京师被皇帝召见,“在当时制度环境
是不可能的事”。[23]但洪武皇帝召见平民,并不是绝不可能。明初的粮长押运粮
食到京仓解运之后 “领取勘合时可以面聆皇帝宣谕”。[24]这在广东族谱有记载。
明初,新兴县税重,“厥后乡老梁成等以其时粮长可见天子也,遂赴京奏奉勘合,察行开
豁”。[25]上表说明,陈博文到京师奏筑倒流港,符合明初的制度背景。但陈被皇帝
召见史无明载,不敢妄测,到工部上奏无疑是可能的。万历新会县志说,修水利的诉求
“多鸣之上”与 “上使人为筑之”相对,就是明代晚期时人对明初广东水利制度的
追述。并不能以 “陈博文到京师被皇帝召见”的不可能就否定奏筑的史实。
《记》的质疑者的意见之一,还认为陈博文只是九江乡后人在乾隆末、嘉庆年间创
造的一个人物。上文已经说明陈博文实有其人,岑平汉、关可达均与陈博文是同时
人,一起进行筑塞倒流港。质疑 《记》为伪者,并没有广搜文献,因此不认识到陈博
文之所以被乡人选送上京奏筑,还因为他是一个民间水利专家。珠江三角洲民间的
水利技术,有因地制宜的技术,如选址避开潮水冲击处而选远离潮水到达的地方以避
免潮水啮食堤围、在潮水上涨时撒谷,潮退时按谷粒下潮退后留下的显示最高潮水
位置的痕迹定堤围水平线、利用山岗丘陵等地势将不同基段连接以便减少堤围施工
量、挖泥筑土壆方法等,都显示珠三角水乡民众的智慧。筑塞倒流港是珠三角地区
一个创造性的水利工程,方志记载陈博文在主持这一工程时吸收了民间智慧:
“陈博民塞倒流港,水势湍急,莫能下手。忽一人挑笠过,笑谓:水势如此安可填筑,惟
移山塞海可耳。陈悟,因取数大船满载石沉之,遂塞。疑为神教。”[26]
还有一记载说明陈博文除了筑塞倒流港,还建设过另一堤围:“鸡公围 在甘竹左滩。
自南海之九江乡分界树起,至阜宁圩止,计长二百六十丈,高九尺五寸,底宽八尺,面宽
三尺。明洪武间里老陈博文创筑。岁久倾圮,乡人黄岐山易以石,堤费至巨万,全堤巩
固,可以经久。乡众德之,名黄公堤,请于县勒石,至今存焉。”[27]鸡公围位于九江乡
堤围与顺德阜宁圩岸连接的地方,是桑园围下游防护北江洪水的重要堤围。洪武年
陈博文筑鸡公围,就是确认了此围的重要性,当时顺德、南海尚未分开。明代景泰年
间顺德从南海分出,修此堤就是顺德人的事,万历年顺德人黄岐山将此土围改为石堤,
也是认识到此堤的重要性。如果陈博文是九江人杜撰出来的,顺德人何以会认为其
真?而且,祭祀陈博文的祠庙不仅在九江乡有,在顺德嘉庆 《龙山乡志》龙山乡志卷
十三,杂志叙述了陈博文的功劳后记载:“吾乡之人追思其德亦莫不曰:此陈氏子之赐
也。其岁设位于大墟祀之以报功。”清代嘉庆道光间顺德龙山、龙江士绅集团还对
“合围通修”是有保留意见的,但在纪念陈博文功绩这一点上却与九江人的态度一
致。这些都说明,陈博文对桑园围的水利建设的功劳得到桑园围南海、顺德两地的
“围民”公认,他是民间水利专家无疑。
六、筑塞倒流港是应对明初西北江三角洲生态环境的需要
从西北江下游三角洲的生态环境史来说,陈博文主持筑塞倒流港,是符合当时生态环
境的。
西北江下游三角洲呈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的地势,桑园围受上游来水的压力,而下
游出水处在宋元水位高于香山西北部的海面,故桑园围在宋元在尾闾没有建堤围。
但随着桑园围以下的西北江下游围垦的进行,特别是香山西北部石歧、小榄以上沙
田的围垦,桑园围尾闾的水位呈逐步抬升的趋势。
西北江三角洲宋代海岸线大致在新会双水—礼乐—江门外海—曹步—小榄—大黄
圃—潭洲一带。这一带是三角洲平原宋代村庄的最南界,往南 (五桂山等山丘、海岛
外),未见宋代遗物和宋代村庄。[28]这条海岸线内—小榄—大黄圃—潭洲一带,即番
禺的南部到香山场的北部一带,已经浮露不少的沙坦可供开发。宋人记载:“番禺以
南,海浩无涯,岛屿洲潭不可胜计…… (有人议在浮虚山建寺庙,官员)请于常平卖其山
及四畔水潬数百顷。”其路程 “未至于香山半程许”。[29]“番禺以南”以下地
区,中心地带是小榄和大黄圃等地,已经有南迁的移民开村和耕作。据20世纪华南
师范大学地理系调查,小榄在北宋已经有曾、罗、杜、毛等土著。宋代的 “香山寨”
即军事设施就设在小榄,大黄圃在北宋嘉佑二年有龙氏墓,潭州在靖国元年已经建村。
[30]邓广荐 《浮虚山》所言在浮虚山建庙,请 “常平”卖其山和山的 “水潬”数百
顷,可见浮虚山的四周有大片可以开发的滩涂。北宋香山已经有“侨田户”即来自
东莞、新会、南海等县豪户前来开发,南宋更多,故在绍兴二十二年立县,石歧、小榄
以上沙田连成一片,宋元香山沙田增加最多。大德年间香山田地山塘为3110.18
顷,[31]此数多为沙田,这对桑园围下游的出水口产生倒灌作用,将九江乡倒流港筑塞,
防止潮水倒灌入围就成为迫切要求。这是水利工程符合明初桑园围下游的水文环境。
筑塞倒流港这一工程牵涉的桑园围上下游生态关系亦见于记载。
对桑园围上游的影响:上游段西江支汊高明河受到筑塞倒流港的影响。高明县的大
沙堤,文献记载为元代至正年间乡人筑。但在明代,“严氏言其祖严福因南海陈博民
奏筑十八堡镇涌等堤,西潦冲激,乃于永乐二年合五都民奏筑此堤 (大沙堤),非元至正
也。”[32]当是大沙堤原建于元代,早期的堤围很低,陈博文筑塞倒流港工程之后,引
起上游水位上涨,上游原堤高度不足抵御潦水,故严氏先祖在永乐二年联合五都居民
加高培厚了大沙堤。反映珠三角下游堤围建设会引起尚有水文变化的现代史料
有,1958年中山县白藤湖 (今属珠海)堵海工程,建造长达5700多米的大堤,虽然解
决了白藤湖地区的农田灌溉和居民的用水问题,却使上游新会、中山等县66.9万亩
耕地和21万人的用水受到严重影响。原因是建围筑闸以后,泥门湾的潮汐吞吐量改
变,西江下游的水文起了重大变化。[33]如果陈博文是九江人伪造出来的,那么明代
远在高明的严氏族人为什么提到筑塞倒流港这件事?因为筑塞倒流港这一水利事件
对上游的高明也有一定影响。
对桑园围上游的影响:倒流港筑塞工程,地点并不限于桑园围,而是沿着西北江正干联
围,牵涉南海、新会、三水县,堤围长达数十里。[37]如果包括后来顺德县的辖地,则
牵涉四县。这一工程位于当时西江河口,引起上下游的水文变化是很大的,如下游段,
影响了位于西江正流的新会,道光《新会县志》认为当时筑塞倒流港,陈博文同时筑
堤筑闸,与桑园围下游的新会天河、横江两围也同时修筑,“殆始于洪武二十九年,王
志 (即乾隆 《新会县志》)以为始于万历时,非也。”[34]道光志作者经过考察,否定
了前代方志的记载,认为陈博文筑塞倒流港一事是真实的。[35]
综合上述,明代洪武二十九年陈博文带头筑塞倒流港是真实的。
七、筑塞倒流港对桑园围水利与农业形态的影响
桑园围合围于元代至正年或以后,洪武二十八年倒流港筑塞工程,桑园围的主要尾闾
倒流港筑塞,标志着桑园围逐步向闭口围转变 (桑园围尾闾之一的龙江乡尚有开口处,
民国才筑塞)。围内的水利生态也发生重要的变化。
(一)围内有围,大堤与小堤各自为政的局面进一步发展
珠江三角洲低地平原内堤围的特征是围内有围。因为珠三角不同江南,前者地势复
杂,河涌众多,为了防潦,各地纷纷筑围以自卫。桑园围地势低下,并且有来自西樵山的
水源,雨水季节来时,防潦与防涝并重。当宋元西樵山下的冲积地被开发时,各地已经
有简陋和高度很低的土壆。当桑园围在至正年以后合围,围内有围的现象已经出现,
只是不普遍。当桑园围筑塞倒流港之后,将围内大大小小的土壆连接起来,但围内有
围变得更有必要。与陈博文同时人岑平汉,“独捐资别筑鸭舌围,与桑园围子母相顾,
群庆安澜。”[36]鸭舌围又称鸭舌基,“自松冈蚌山、龟山及大塘数里。”[37]其实
是九江大围的一个子围,也是自洪武二十八年筑塞倒流港之后第一个见于记载的子
围。元明之间这类子围是很多的,只是不见于记载而已。围内有围虽然捍卫单个水
利社区,但却是水灾加剧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珠江三角洲低地平原水利建设初始阶
段与明清时期必然出现的情况。
(二)筑塞倒流港加剧了桑园围的内涝现象,挖塘蓄水成为水利建设的另一需要,并引
起明代前期基塘农业的出现
倒流港筑塞工程改变了桑园围水环境,特别是下游的水环境。因为九江的出水口被
堵塞之后,虽然能抵挡住潮水倒灌,但却使低洼的九江、顺德的龙山、龙江和甘竹等
地很容易受到涝灾。而桑园围上游在雨季到来时,西樵山上的水流不能迅速宣泄,同
样有涝灾,只是严重程度还不如下游。为了防止涝害,挖深鱼塘蓄水是一个很好的办
法。鱼塘挖深以后,将泥土覆向池塘四周,称为基面。由于池塘要挖得深才能起到蓄
水和适应养鱼的要求,于是池塘的淡水养殖首先从地势最低最易受涝的九江、龙江、
龙山等地发展起来。鱼塘的淡水养殖业有赖于四大家鱼的鱼种供应。而在弘治年间,
西江上捕捞鱼花的疍家不堪鱼课负担,纷纷逃亡。广东当局因此进行了渔政改革,将
西江上的鱼花捕捞权交给九江人承饷,九江人获得了西江段的鱼花捕捞权,并在长期
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捕捞、养殖、运输鱼花的技术,促进了桑园围内以致华南
的淡水养殖业的繁荣。又由于九江等地长期从事蚕桑业,池塘旁的基上种植桑树,桑
叶喂蚕,逐步形成了桑基鱼塘的形式。这是桑园围内基塘农业的开端。
(三)倒流港筑塞工程标志桑园围治水社会的发展
质疑 《记》为伪者,说陈博文只是乾隆、嘉庆之间桑园围士大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物。在这方面,质疑者既缺乏对文献的挖掘,对宋元明前期珠江三角洲水利社会史也
缺乏认识。桑园围合围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在元代至正元年以前可能都曾有过
多次合围,都不成功。以往合围失败的原因是在桑园围西北面西樵山边的吉赞基未
能筑成。吉赞基位于桑园围与三水平原交接点,三水平原上大路峡基刚好在西江、
绥江、三水沧江的合流处,对以下的桑园围有高屋建瓴之势,遇到潦水季节,“居民日
夜戒严”,“大路圩岸修筑于元至正元年,其窦一设于小湾,一设于大路”。[38]大路
峡围长度6840丈,捍护田亩48顷,此围决则桑园围全淹,则桑园围顶部的合围—即
吉赞基筑成,前提是大路峡基筑成。吉赞基筑成必在元至正元年或以后。在此之前
的多次顶部合围失败,是因为大路峡基未筑,以及动员桑园围范围内的民众也需要一
定的条件。清代乾、嘉时人温汝适所纂十七卷的 《桑园围志》乾隆甲寅本,首卷有
两篇重要文章,第一篇是《记》,第二篇是撰于乾隆四十四年 《重修吉赞横基碑记》,
吉赞横基被全围各堡士绅认作是 “合围公修”的基段。[39]因为桑园围的俗例是
各基主业户负责自己所属基段的维修,只有与全围利害相关的基段才 “合围公修”。
《桑园围志》编纂者将 《重修吉赞横基碑记》置于卷首第二篇,足见吉赞基的重要
性。
《记》则置于 《桑园围志》卷首第一篇,因为 《桑园围志》首撰者,乾隆、嘉庆间
曾在朝廷任职,致仕在家的龙山人温汝适希望陈博文成为桑园围的一个热爱桑梓的
人物为乡绅所效仿。宋元是岭南治水社会的 “雏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家与地
方的大族开始结合,形成官府主导的治水行动;同时民间也在村落首领或宗族的头面
人物组成水利建设的组织。但这时无论官府的,民间的治水组织都是松散的,只是需
要治水时才联合行动,治水过后缺乏对水利工程的经常性维护,也缺乏水利组织的经
常性中心或集团主导行动。元代至正年或至正年以后桑园围合围其实就是在宋到元
至正间各宗族独立建设的基段上,将几百丈的吉赞横基修建了,桑园围才真正合围。
但是在吉赞横基修建之后,而缺乏经常性的维护,所以有决围之后全围被淹的情况。
洪武年筑塞倒流港可以说是元代桑园围合围之后,合围通修的第二次全围联合大行
动,标志着桑园围治水社会开始迈出 “雏形”而有所发展。但这一发展是曲折的。
明代景泰年顺德从南海分治出来之后,桑园围的顺德段和南海段形成 “南围南修,顺
围顺修”的俗例,对后来桑园围合围通修的联合治水造成障碍。虽然至此之后,除了
吉赞横基与桑园围李村段等险要基段溃决之后,才有通修行动,但都是暂时性的,灾后
一过,没有经常性的通修。陈博文主持倒流港筑塞,给后代树立了一个 “合围通修”
的榜样。明初 《记》的撰写和刻碑于“报食祠”,只是为了纪念陈博文的功劳,却为
后世人利用这一形象提供了文化资源。乾隆、嘉庆间重修 “报食祠”,并将 《记》
置于 《桑园围志》之首,目的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热爱桑梓的乡土人物形象,打破
“南围南修”,“顺围顺修”的俗例,而不分畛域,培育围众 “合围通修”的观念。
这是治水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 《记》在乾隆、嘉庆以后桑园围水利
史上的重要意义。[40][基金项目:2015年度 〈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
项课题资助项目 《宋元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变革与广州城市发展》,编
号:GZY02;2016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宋元及明代前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变
革与广州城市发展》,编号:16FZS015]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主要著作: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等编 《桑园围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讨论会论文集》广东科
技出版社.1992年;吴建新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26—41,201—
216,232—243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徐晓 《明清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管理机制研究—以西
樵桑园围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48页。还有散见于杂志的若干论文,不一一
列举。
[2]倪尚明 《黎贞及其〈秫坡集〉---兼谈明初珠江三角洲社会文化》,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
8页)。
[3][4][24]徐晓 《明清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管理机制研究—以西樵桑园围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年,第40—48页
[5]民国 《开平县志》卷四十一 《金石略》,中国方志丛书本,336—337页
[6][明]黎贞 《黎秫坡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出版社.1995年,集部25—516
[7](明史卷一四八)
[8][明]陈献章 《读秫坡集》,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691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0]黎贞 《重刻林坡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出版社,1995年,区越序,集部25—516
[11]康熙 《新会县志》卷末 《艺文篇籍》,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本,455页
[12]道光 《新会县志》卷十一 《艺文集部》,中国方志丛书本,第339页
[13][明]黎贞 《儒林余氏族谱序》,《余绍贤堂余氏族谱》,卷二,序,光绪刻本,开平档案馆藏。
[14]光绪 《九江儒林乡志》,卷一 《舆地略》,.光绪九年刊本.
[15]光绪 《九江儒林乡志》,卷2,灾祥,乡事附,.光绪九年刊本.
[16]光绪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三列传,.光绪九年刊本.
[17]光绪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三,列传,.光绪九年刊本.
[18]顺治 《九江乡志》,卷之二事纪,顺治14年刻本.
[19]嘉靖 《广东通志稿》卷三十一 《土产·水利》,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2003年版。
[20]雍正 《吴川县志》卷二 《水利》,故宫珍本丛刊本
[21]关于明代民间乡朝廷奏筑水利的事例,还可参看拙著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
为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266—267页
[22]万历 《新会县志》卷四 《水利》,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本,第86页
[24]梁方仲 《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25]粤东简氏大同谱卷十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
1462—1463页
[26]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二十一杂录上,清刻本
[27]咸丰顺德县志,卷5,建置略·堤筑,中国方志丛书本,第473页
[28][30]李平日,等著 《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变迁》,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75页、第75—76
页。
[29][宋]邓广荐 《浮虚山记》,嘉靖 《香山县志》,卷之七 《艺文》,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
385页下.
[31](嘉靖 《香山县志》卷二 民物志.3,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0页
[32]康熙 《肇庆府志》卷十六 《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33]新会县水利电力局 《新会水利志》,1990年,第162页
[34]顺治 《九江乡志》卷之四 《潜德列传》,清刻本;道光 《新会县志》卷二 《水利》,中国方志丛
书,第52页
[35]按语:论述道光新会县志卷二水利的编纂者对水利的实地考察,见拙著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279页
[36]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三列传,清刻本
[37]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一舆地略,清刻本
[38][明]彭懋淳 《鼎修大路围圩窦记》,嘉庆 《三水县志》,卷十五,《艺文上》,中国方志丛书,第
277页
[39][清]明之纲同治桑园围通修志卷之一(甲寅),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第六册,1997年12月,北京
出版社影印出版,6—53页;6--54页
[40]以上观点参看拙作 《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236—240页;吴建新 《略论〈桑园围志〉的价值与续修》,第二届农业历史遗产保护论坛论文,南
京,2012年。

本文发布于:2023-11-16 15:38:34,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70012031492293.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明初黎贞撰《陈博民谷食祠记》与桑园围的水利环境.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明初黎贞撰《陈博民谷食祠记》与桑园围的水利环境.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