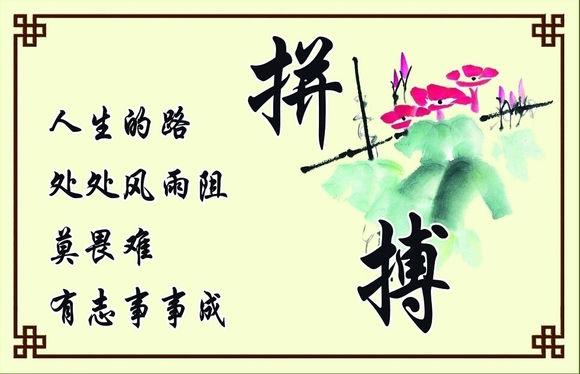
想象乡土的方式
作者:傅华 董爱宇
来源:《艺术广角》2022年第01期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乡村进入剧烈的转
型期,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面临冲击。一些表现新世纪农村的作品应运而生,新
乡土书写暗潮涌动。2005年6月,《佛山文艺》联合《山花》举办“黔东南笔会”,讨论“和谐
社会与文学承担”的话题,一系列关于“新乡土”如何契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讨论由此展开。翌年
六月,由《佛山文艺》发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莽原》及新浪网共同举办“新乡土
文学征文大赛”,众多乡土作家参与其中,文能、王山对“新乡土文学”有所界定。[1]2007年3
月,《佛山文艺》召开“新乡土文学”研讨会。关于“新乡土文学”的探讨在持续发酵。2015年,
《雨花》提出“新乡土写作”概念,面向全国征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并在《雨花·中国作家
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展”的方式连续六期刊发,引起了广泛关注。[2]随后,第二届中国长篇
小说高峰论坛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新乡土写作”是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与会专家一致肯定
“新乡土写作”的价值,“新乡土写作”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综合学界的探讨,“新乡土写作”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从写作时间上看,“新乡土写作”是
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创作。从写作主体上看,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70
年代后期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有短暂的农村生活经历。从写作内容与对象来看,书写的是转
型与裂变中的新世纪农村社会。这里不仅体现了农村范围的扩大:从原乡到城乡接合部再到城
中村,而且也体现了农民身份的变化:从地道的农民到流动在城乡间的打工人再到定居城市的
进城务工者。同时,农村人际关系的变更、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等,都是“新乡土写作”关注的
焦点。从写作视角来看,“新乡土写作”要求作家转换“回看”下的“俯视”姿态,代以平等地、历
史地、整体地展示新乡土经验的写作视角;避免简单情感判断下的一元价值取向,代之对农村
社会现实的智性反思与多维审视。新变的乡土与人心、争鸣的写作与批评,使得正处于进行状
态的“新乡土写作”呈现出多元兴盛的面貌,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这股
蔚为壮观的“新”创作潮流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以期激活传统“乡土文学”的“现代性”。
一、“离土”或“在土”的乡土想象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在不同国别、不同时代有着不一样的书写,纵然
变化多端但其创作之根都植于土地。不管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费尼莫·库珀的“边疆小说”、布
雷特·哈特代表的西部文学,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兴起的“真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文学流派,
[3]还是中国乡土文脉中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型乡土文学、沈从文等代表的抒情型乡土文学,
抑或是柳青等代表的革命型乡土文学和韩少功等代表的寻根型乡土文学,[4]“土地”始终是其叙
事的内核。正如李敬泽所言:“现代文学以来,土地在不同时期的乡土写作中都是一个意义中
心,它是历史的焦点,也是农民可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5]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在千百年
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下形成了对土地近乎神圣的崇拜。传统乡土作家大多书写了自己与土地的深
厚情感。从小与土地的深刻联结,使他们的“根”深扎于土,厚重的乡土记忆和熟悉的乡土经验
让他们的乡土想象都有根基,乡土写作呈现出一种“系于土”的生命形态。
反观“新乡土”写作者,他们虽生于乡村,但乡土经验相对短暂且有限。时间与空间距离的
间隔使乡土记忆与感情淡化,原本就浮在表层的乡土之根渐次松动,作家与乡土逐渐陌生,以
致于产生了隔膜。徐则臣就坦然说出自己的隔膜:“我对当下的乡村越来越陌生,我觉得没有
足够的能力把握好乡村。”[6]这不仅是徐则臣的问题,更是新乡土作家的共同难题。他们未曾
亲历乡土的种种变化,难以感知当下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新乡土写作”一旦失去了具体新鲜
的“在土”体验,就易流于认知的表象,从而在内容、情感的表达上出现隔膜,乃至失真,甚至
走向个人意识与现实乡土的错位。
不可否认,“新乡土写作”中也有不少亲于土、系于土的佳作。叶炜在谈及其“乡土中国三
部曲”的写作时,直言:“我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为了写作《富矿》,我先后多次返乡,深入
煤矿考察;为了写作《后土》,我对老家的乡村干部进行采访,积累了厚厚的一摞资料;为了写
作《福地》,我广泛搜集资料,调动自己的全部乡村生活经验。”[7]实地调查采访、收集资
料,躬身拾掇新的乡土经验,正是叶炜能够写出麻庄这个复杂且真实的典型中国农村的原因。
与乡土存在隔膜是不少新乡土作家真实的写作境遇,付秀莹也感叹过:“这么多年了,我写下
的,大约不过是记忆中的乡土。在那些小说里,更多的是追忆。”[8]童年记忆中的乡土与现今
的乡土无疑千差万别,付秀莹清醒地知道自己与乡土的“隔”,也在努力地修复和逾越这道
“隔”。她每天都与父亲打电话,了解父亲的一日三餐,了解“芳村的每一户人家,婚丧嫁娶,
爱恨冤仇,乡村内部的肌理和褶皱”和“乡村人情世故的每一个拐弯抹角处”。[9]一通通的电
话、一次次的往返,付秀莹直面实在的乡村经验,写出了当下乡村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像付秀
莹这样深度地进入乡土的作家才能写出真实的、鲜活的乡土世界。
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的李娟,正是得益于对牧民生活的完全融入,才能在《冬牧场》中
翔实地展示哈萨克牧民们不断“转场”、一直“在路上”的艰苦生活。为了对当下农村情况进行有
效考察与反映,2008到2009年间,梁鸿回到家乡梁庄,以“非虚构写作”的纪实方式展示新乡
土的变迁。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梁鸿以平等的姿态同老家农民展开了深入的對话与交流,最后
将所有内容集结成《中国在梁庄》。2011年,为完成《出梁庄记》,梁鸿花费了两年时间,
奔赴全国各地探访“出走”梁庄的农民,与之同吃同住,真切体会他们的艰辛。在与土地和农民
近距离的接触中,梁鸿与梁庄建立了深刻的情感与精神联结,这使得梁鸿能够对在现代化冲击
下梁庄的“常”与“变”进行具象的呈示。梁鸿对变迁中梁庄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予以了相对客观的
再现,同时也寄托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下乡土与农民未来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二、“审丑”或理想化的乡土想象
有些作家在谈论乡土时总会下意识地与落后、贫穷、闭塞等相联系,并通过对它們的批判
来呼唤“美”的所在,或者简单地设想乡土未来的光明前景,打造虚浮的乡土“乌托邦”。“审丑”
意识与理想化的期许一直潜藏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中。
新世纪以来,乡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不断遭受冲击和洗礼。在现代文明的映照下,贫
困的乡土裸露出人性的黑暗和丑恶。如果说阎连科的系列传统乡土作品聚焦“耙耧山脉”大量书
写苦难,以“审丑”或苦难意识揭示乡土的落后、愚昧甚至黑暗,那么鲁敏等“70后”新乡土作家
也在“审丑”中追问乡土的罪与恶。“暗疾”是鲁敏一部小说的名字,也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
主题。在小说《暗疾》中,鲁敏夸张化地为每个人都设置了“暗疾”:父亲的“神经性呕吐”、母
亲对记账的病态痴迷、姨婆对“大便”的变态关注。还有《取景器》中,女摄影师对破败丑相近
于变态的痴迷。鲁敏如考究者一般,拿着放大镜仔细观摩众生身心的隐疾,并展示给读者一同
观看。但鲁敏与一些作家仅描绘生理层面的痛苦体验与表象的丑陋不同,她没有一味沉溺于
“丑”的展览,而是试图对其精神动因展开深层的剖析,努力揭示精神“暗疾”。毕竟“丑”的展示
终究不是目的,在人的挣扎与自我拯救中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才是“审丑”的精神诉求与终极意
义。《后土》《中国在梁庄》与《陌上》等作品没有故作姿态地渲染乡土的“丑”,他们更关心
的是乡村在艰难转型中的精神裂变,同样是对乡土“丑”的叙述,但做到了对简单展览式“审丑”
的超越。
新乡土文学的“审丑”还集中出现在对权力、暴力与性的揭露上。《陌上》中芳村首富大全
为一己私利操纵选举,让建信当上村支书;扩军在村委会小白楼前大张旗鼓地分发电饭锅、豆
浆机公然贿选。《陌上》对资本和政治合谋的揭示,呈现了乡村政权中的阴暗面。暴力与性的
符码也大量充斥在新乡土作品中。苦难、暴力与性确是乡土真实面貌的一部分,出现在乡土文
学叙述中本无可厚非,但一味沉沦于“审丑”之中甚至流于单纯的感官刺激则需警惕。他们对乡
土丑态的过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文本的多元意义,丢掉了乡土写作的初衷。旁观的姿
态、对信息的多次加工等,都易使作家不自觉地将乡土的丑恶夸张化甚至妖魔化。这样的创作
显然无法触摸到滋生苦难、强权等“丑行”的乡土大地的复杂肌理,也不能深刻洞察产生这类丑
行的内在动因。
与“审丑”相对的另一写作倾向,是对乡土未来命运的一厢情愿式的美好想象。一些作家看
到了新乡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但囿于他们的“土性”不足,对乡土问题认识表面化,文本呈现
的解决方案相应流于简单化与理想化。叶炜的《后土》也有此嫌疑。他展示了都市文明冲击下
麻庄不断变化的面貌,尽管乡土变迁、人心变化,麻庄的村民仍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梦想在家
门口就能工作,梦想住上漂亮宽敞的小康楼,梦想搭上致富的列车……如何帮助麻庄村民实现
梦想,叶炜给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刘非平的话说,就是:“建设小龙河观光带、苇塘观鸟园、
果园采摘园、马鞍山野味馆、麻庄鱼塘垂钓中心等,以观光旅游带动麻庄的经济发展,带动麻
庄乡亲共同致富。”[10]虽然在小说结尾,这幅美好的“乡村蓝图”确实实现了,小康楼建成、景
观带竣工、旅游公司成立、超级大农场也在筹备中,整个村庄的未来光明无限,这无疑折射出
当今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图景,但又不免有过于理想化之嫌。
凭借乡土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经营生态经济,这种发展模式还散见于众多作家作品之中,
包括一些浸淫乡土写作已久的作家。周大新《湖光山色》中,楚暖暖依靠楚长城和丹江湖建起
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带领楚王庄共同富裕。关仁山《金谷银山》里,范少山凭借传奇的金谷
种,带领大家建设金谷子种植基地,又开山修路、利用天然溶洞发展旅游业。这些作品都畅想
了新农村美好的前景,但其成功致富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与传奇性,毕竟并非每个农村都能坐
拥绿水青山、文化遗址或是“金种子金苹果”。且就乡土旅游业而言,其巨大的资金投入、较长
的建设周期、复杂的管理运营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绿色生态农业、乡土旅游经济毋庸
置疑是新世纪乡村发展的可行思路,但其普适性不高。由此可见,叶炜等对乡土问题的简单化
处理,有捉襟见肘之处,他们笔下的“乌托邦”式的乡土美好理想终究难以应对新乡土现实的复
杂性。但其间呈现出的这群知识分子对新乡土未来出路的关注与思考、责任与担当也不能简单
否定。
相比较走绿色发展道路,开矿挖煤、开山取石、拦河取沙、弃耕办厂这些成本低、见效快
的致富方式明显更容易被农民接纳。但这种破坏式发展带来的污染等生态问题令人堪忧,经济
体制变化和人心浮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暗藏隐患,《陌上》就真实地书写了上述隐忧。在皮革
行业的暴利诱惑下,村北的庄稼地变成了大片的厂房。不少人凭借皮革生意致富,但随之而来
的是无人敢喝地下水、空气又酸又臭、怪病越来越多。芳村的发展困境也是中国大多数乡村面
临的共同难题。对于现实发展的难以把控,付秀莹深感无奈。既然变化无常,付秀莹便以“不
变”应“万变”,以细碎的、片段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即“一种结构的未完成状态”来“遥遥呼应着
这个世界多变现实所蕴含的无限未知”。[11]
在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新乡土作家对于乡土的想象繁杂不一。在未完成状态书写中呈
现新乡土中异质、陌生、未知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这对“新乡土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若只停留于对新世纪乡土问题的简单认识与判断,仅仅是展览式的“审丑”或理想化的处理,
“新乡土写作”将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乡土想象的困境
面对只沉迷于过往经验或单纯地想象乡土、只浮于表面而苍白无效的某些乡土写作,一些
学者发出“新乡土文学距离乡村有多远”[12]的质疑。因为作家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融入乡土
大地,才能契合新世纪乡土变幻的步伐,才能准确揭示乡土变化的新质。“在土”体悟的缺失不
仅会使情感失真,也易导致判断失效。是怀念传统乡土而抗拒甚至恐惧城市的侵袭?还是融入
城市进入城乡一体后的新生?乡土现实的变迁加剧了作家价值取向的裂变与分化,乡土中命运
与情感的困厄困惑也导致了他们价值立场的暧昧与犹疑。于是,在与土地和农民的若即若离
中,在自我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诸多困惑中,部分新乡土作家的创作表现出现代主体的迷
茫。这迷茫不局限于其个人,更是“新乡土写作”难以规避的现实境遇与精神难题。
二、“审丑”或理想化的乡土想象
有些作家在谈论乡土时总会下意识地与落后、贫穷、闭塞等相联系,并通过对它们的批判
来呼唤“美”的所在,或者简单地设想乡土未来的光明前景,打造虚浮的乡土“乌托邦”。“审丑”
意识与理想化的期许一直潜藏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中。
新世纪以来,乡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不断遭受冲击和洗礼。在现代文明的映照下,贫
困的乡土裸露出人性的黑暗和丑恶。如果说阎连科的系列传统乡土作品聚焦“耙耧山脉”大量书
写苦难,以“审丑”或苦难意识揭示乡土的落后、愚昧甚至黑暗,那么鲁敏等“70后”新乡土作家
也在“审丑”中追问乡土的罪与恶。“暗疾”是鲁敏一部小说的名字,也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
主题。在小说《暗疾》中,鲁敏夸张化地为每个人都设置了“暗疾”:父亲的“神经性呕吐”、母
亲对记账的病态痴迷、姨婆对“大便”的变态关注。还有《取景器》中,女摄影师对破败丑相近
于变态的痴迷。鲁敏如考究者一般,拿着放大镜仔细观摩众生身心的隐疾,并展示给读者一同
观看。但鲁敏与一些作家仅描绘生理层面的痛苦体验与表象的丑陋不同,她没有一味沉溺于
“丑”的展览,而是试图对其精神动因展开深层的剖析,努力揭示精神“暗疾”。毕竟“丑”的展示
终究不是目的,在人的挣扎与自我拯救中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才是“审丑”的精神诉求与终极意
义。《后土》《中国在梁庄》与《陌上》等作品没有故作姿态地渲染乡土的“丑”,他们更关心
的是乡村在艰难转型中的精神裂变,同样是对乡土“丑”的叙述,但做到了对简单展览式“审丑”
的超越。
新乡土文学的“审丑”还集中出现在对权力、暴力与性的揭露上。《陌上》中芳村首富大全
为一己私利操纵选举,让建信当上村支书;扩军在村委会小白楼前大张旗鼓地分发电饭锅、豆
浆机公然贿选。《陌上》对资本和政治合谋的揭示,呈现了乡村政权中的阴暗面。暴力与性的
符码也大量充斥在新乡土作品中。苦难、暴力与性确是乡土真实面貌的一部分,出现在乡土文
学叙述中本无可厚非,但一味沉沦于“审丑”之中甚至流于单纯的感官刺激则需警惕。他们对乡
土丑态的过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文本的多元意义,丢掉了乡土写作的初衷。旁观的姿
态、对信息的多次加工等,都易使作家不自觉地将乡土的丑恶夸张化甚至妖魔化。这样的创作
显然无法触摸到滋生苦难、强权等“丑行”的乡土大地的复杂肌理,也不能深刻洞察产生这类丑
行的内在动因。
与“审丑”相对的另一写作倾向,是对乡土未来命运的一厢情愿式的美好想象。一些作家看
到了新乡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但囿于他们的“土性”不足,对乡土问题认识表面化,文本呈现
的解决方案相应流于简单化与理想化。叶炜的《后土》也有此嫌疑。他展示了都市文明冲击下
麻庄不断变化的面貌,尽管乡土变迁、人心变化,麻庄的村民仍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梦想在家
门口就能工作,梦想住上漂亮宽敞的小康楼,梦想搭上致富的列车……如何帮助麻庄村民实现
梦想,叶炜给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刘非平的话说,就是:“建设小龙河观光带、苇塘观鸟园、
果园采摘园、马鞍山野味馆、麻庄鱼塘垂钓中心等,以观光旅游带动麻庄的经济发展,带动麻
庄乡亲共同致富。”[10]虽然在小说结尾,这幅美好的“乡村蓝图”确实实现了,小康楼建成、景
观带竣工、旅游公司成立、超级大农场也在筹备中,整个村庄的未来光明无限,这无疑折射出
当今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图景,但又不免有过于理想化之嫌。
凭借乡土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经营生态经济,这种发展模式还散见于众多作家作品之中,
包括一些浸淫乡土写作已久的作家。周大新《湖光山色》中,楚暖暖依靠楚长城和丹江湖建起
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带领楚王庄共同富裕。关仁山《金谷银山》里,范少山凭借傳奇的金谷
种,带领大家建设金谷子种植基地,又开山修路、利用天然溶洞发展旅游业。这些作品都畅想
了新农村美好的前景,但其成功致富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与传奇性,毕竟并非每个农村都能坐
拥绿水青山、文化遗址或是“金种子金苹果”。且就乡土旅游业而言,其巨大的资金投入、较长
的建设周期、复杂的管理运营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绿色生态农业、乡土旅游经济毋庸
置疑是新世纪乡村发展的可行思路,但其普适性不高。由此可见,叶炜等对乡土问题的简单化
处理,有捉襟见肘之处,他们笔下的“乌托邦”式的乡土美好理想终究难以应对新乡土现实的复
杂性。但其间呈现出的这群知识分子对新乡土未来出路的关注与思考、责任与担当也不能简单
否定。
相比较走绿色发展道路,开矿挖煤、开山取石、拦河取沙、弃耕办厂这些成本低、见效快
的致富方式明显更容易被农民接纳。但这种破坏式发展带来的污染等生态问题令人堪忧,经济
体制变化和人心浮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暗藏隐患,《陌上》就真实地书写了上述隐忧。在皮革
行业的暴利诱惑下,村北的庄稼地变成了大片的厂房。不少人凭借皮革生意致富,但随之而来
的是无人敢喝地下水、空气又酸又臭、怪病越来越多。芳村的发展困境也是中国大多数乡村面
临的共同难题。对于现实发展的难以把控,付秀莹深感无奈。既然变化无常,付秀莹便以“不
变”应“万变”,以细碎的、片段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即“一种结构的未完成状态”来“遥遥呼应着
这个世界多变现实所蕴含的无限未知”。[11]
在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新乡土作家对于乡土的想象繁杂不一。在未完成状态书写中呈
现新乡土中异质、陌生、未知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这对“新乡土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若只停留于对新世纪乡土问题的简单认识与判断,仅仅是展览式的“审丑”或理想化的处理,
“新乡土写作”将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乡土想象的困境
面对只沉迷于过往经验或单纯地想象乡土、只浮于表面而苍白无效的某些乡土写作,一些
学者发出“新乡土文学距离乡村有多远”[12]的质疑。因为作家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融入乡土
大地,才能契合新世纪乡土变幻的步伐,才能准确揭示乡土变化的新质。“在土”体悟的缺失不
仅会使情感失真,也易导致判断失效。是怀念传统乡土而抗拒甚至恐惧城市的侵袭?还是融入
城市进入城乡一体后的新生?乡土现实的变迁加剧了作家价值取向的裂变与分化,乡土中命运
与情感的困厄困惑也导致了他们价值立场的暧昧与犹疑。于是,在与土地和农民的若即若离
中,在自我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诸多困惑中,部分新乡土作家的创作表现出现代主体的迷
茫。这迷茫不局限于其个人,更是“新乡土写作”难以规避的现实境遇与精神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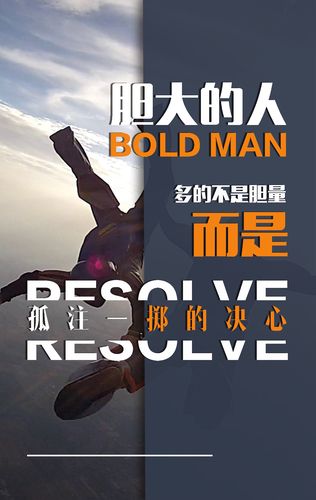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11-12 07:52:2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99746750230539.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想象乡土的方式.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想象乡土的方式.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