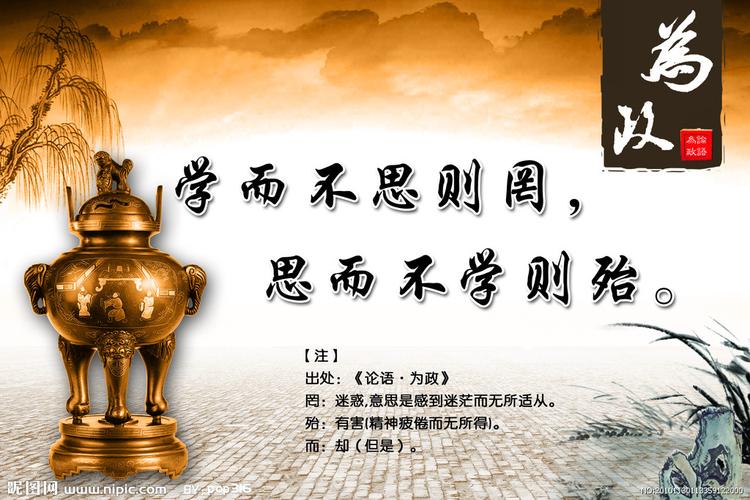
不平衡⽭盾与⼀分为⼆—巴迪欧论⽑泽东《⽭盾论》
巴迪欧认为,正是⽑泽东的⽭盾理论,让他可以在今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盾论》中,⽑泽东强调了
⽭盾的不平衡性,从⽽彻底摧毁了西⽅马克思主义中的唯⼼主义残余,⽽⽭盾的不平衡性意味着现实是⼀种由多种⽭盾
制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解的,为了超越这个⽭盾过程,在巴迪欧看来,就必须抛弃合⼆⽽⼀的思维,将⽑泽
东的⼀分为⼆的辩证法作为思考现实社会和⾰命⽃争的唯⼀理论武器,在⼀分为⼆的辩证法指引下,主体从众多⽭盾中
决定什么是主要⽭盾,什么是次要⽭盾,从⽽为⾛向⼀个史⽆前例的新未来社会开辟了⼀条道路。
2007年,齐泽克将⽑泽东的《⽭盾论》和《实践论》合并成⼀本著作,在英国的著名左翼出版社Verso出版社出版,并
为这本《⽭盾论》和《实践论》的合集撰写了长篇导⾔。不过,在阅读了齐泽克的英⽂版导⾔之后,巴迪欧提出了⾃⼰
的不同看法,他撰写了⼀封长信,与齐泽克商榷。之后不久,齐泽克也回了⼀封信,给出了⾃⼰的回应。于是,在后来
出版的法⽂版《⽭盾论》和《实践论》合集中,除了收录了齐泽克的导⾔之外,同时也收录了巴迪欧写给齐泽克的信
件,以及齐泽克的回信。在巴迪欧的信中,他明确提出:“⾸先提出的问题是⾮常必要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对⽑
泽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巴迪欧⾃⼰回答说:“我们对此只能说⼀句话,⽑泽东具有普遍性。”巴迪欧之所以认为⽑
泽东具有普遍性,他所针对的⽂本实际上就是⽑泽东的《实践论》和《⽭盾论》,尤其是后者,这本⼩册⼦被巴迪欧认
定是⽑泽东创⽴新辩证唯物主义的蓝本。巴迪欧早年从师于阿尔都塞,他⼗分关注⽑泽东的《⽭盾论》,为了向⽑泽东
的《⽭盾论》致敬,他同样以《⽭盾论》为题撰写了⼀本哲学著作,并收录于20世纪70年代马斯佩罗(Maspero)出版
社的延安⽂丛(Yenan synthès)系列中。直到2006年,即在他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中,巴
迪欧仍然坚持认为⽑泽东的《⽭盾论》是建⽴⾃⼰本体论和现象学思想的基础。因此,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巴迪欧哲学,
我们必须从他对⽑泽东《⽭盾论》的解析开始。
⼀、现实⽭盾及其不平衡性
严格来说,巴迪欧对⽑泽东《⽭盾论》的关注并⾮⼀蹴⽽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先受到了导师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道路的影响,然⽽,尽管阿尔都塞将巴迪欧引上了哲学思考的道路,但是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哲学基础并不
牢固,⽽正是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理论主义的⽴场,最终让巴迪欧看到了阿尔都塞实际上⽆法真正解决唯物辩证法的问
题,⽽这促使他转向更为实践的⽴场,即⽑泽东《⽭盾论》中的唯物主义⽴场。
1965年,阿尔都塞出版了他的论⽂集《保卫马克思》。不过,对于巴迪欧来说,他最关⼼的实际上只是本书中的两篇⽂
章,即《⽭盾与超越决定》与《关于唯物辩证法》,尤其是阿尔都塞对⽑泽东《⽭盾论》中的⽭盾不平衡性的解读,让
巴迪欧明⽩了不平衡性理论正是⽑泽东唯物辩证法的内核。所以,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赋予了唯物辩证法新的活
⼒,也就是说,阿尔都塞坚决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对⿊格尔的唯⼼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即将⿊格尔的以抽
象观念和绝对精神为根基的辩证法,变成以现实社会存在和市民社会的辩证法。
“我因此认为,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相同的⽅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
质(⿊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是从辩证法本⾝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
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阿尔都塞的这段话有着明确的指向,因为阿尔都塞坚决
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格尔的历史哲学严格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格尔的历史哲学所依赖的是形⽽上学,将历史的
辩证运动看成某种精神辩证演化的结果。⿊格尔说:“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种历史已
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的,⽽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
了它这种单⼀和同⼀的本性。”⿊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不是⽆规律可寻的,在历史漫长的演化过
程中,它们最终体现为“世界精神”的同⼀性。在⼀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那⾥,这种唯⼼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被简单颠倒
为⼀种庸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他们仍然认为历史是受到某种客观的历史规律制约的,不过决定这种历史规律的,
不再是⿊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精神”,⽽是市民社会。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对⿊格尔的唯⼼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简单颠
倒,将⼀种唯⼼的历史辩证法变成所谓的“唯物”的历史辩证法。
相反,阿尔都塞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根本找不到由某个单⼀因素起到决定作⽤的历史规律(即便是恩格斯意义上
相反,阿尔都塞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根本找不到由某个单⼀因素起到决定作⽤的历史规律(即便是恩格斯意义上
的“归根结蒂”或⼒的平⾏四边形的决定作⽤)。阿尔都塞所看到的:“在各有关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盾’(这些不同⽭盾
也就是列宁谈到的‘⼀系列’⽭盾)虽然‘汇合’成为⼀个真实的统⼀体,但并不作为⼀个简单⽭盾的内在统⼀体的简单现象
⽽‘消失’。这些‘不同⽭盾’之所以汇合成⼀个促使⾰命爆发的统⼀体,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
状和特殊的活动⽅式,它们在构成统⼀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的根本统⼀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盾’是
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盾
的影像,它在同⼀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和各领域,同时⼜被它们所规定。”在阿尔都塞看来,真实社会
的运动并⾮由单⼀的因素来决定的变化,社会统⼀整体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盾”只是社会中众多⽭盾中⼀个⽐较突出
的⽭盾⽽已,它并不⾜以构成整个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阿尔都塞对唯物辩证法的重新解读,还有⼀个更为深刻的含义,辩证法本⾝的⽬的并不是指向⽭盾的最终解决,相反,
⽭盾才是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在⿊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他们总希望⽭盾能得到最终解决,
即⽭盾双⽅最终⾛向和解,⽭盾消逝在最终的统⼀之中。在阅读了⽑泽东的《⽭盾论》之后,阿尔都塞将这种概念改变
成⽭盾的“不平衡发展”。按照阿尔都塞的定义:“不平衡性是社会形态的内在性,因为复杂整体主导的结构的不变性本⾝
是构成主导结构的各种⽭盾的具体可变性的条件,也就是各种⽭盾的转移、压缩、交替……的条件。”从阿尔都塞的⽭
盾“不平衡性”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
(1)⽭盾是社会现实的根本特征,即任何现有的社会形态都⽆法摆脱⽭盾,⽽⽭盾构成了社会形态演化的“合理内核”,
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要素,也是阿尔都塞坚决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绝⾮对⿊格尔的辩证唯⼼主义简单颠
倒的原因。
(2)与庸俗决定论不同,阿尔都塞并不认为“不平衡性”的⽭盾变化是⼀种有规律的变化。这样,我们⽆法在规律性的层
⾯上来简单把握社会形态的变化,⽽将历史演变的规律表述为⽣产⽅式的演变规律,在阿尔都塞看来,恰恰是⼀些庸俗
的理论家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形⽽上学化的表现。
(3)阿尔都塞虽然强调了存在着不变性,并且将这种不变性看成是各种具体⽭盾可变性的前提条件,但对于具体的⼈
来说,这种不变性是难以把握的,然⽽,这些⽆限多的⽭盾的不平衡带来的⼀个现实结果是,我们实际上⽆法简单从这
些多样性的⽭盾中梳理出完整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脉络,⽽这种脉络只能依赖于阿尔都塞的另⼀个核⼼概念:超越决
定。
不过在这⾥,巴迪欧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了。巴迪欧表⽰,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仍然是僵化的,与⽑泽东在《⽭盾
论》中鲜活的辩证法相去甚远,巴迪欧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这位声名显赫的阿尔都塞⼤师背后,我们发现⽑泽
东所谓的‘僵化的列宁主义’。也正是他的这个想法,让他脱离于运动,认为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不是内在于
⼯⼈的知识之中,这个外部就是社会历史的实证科学,换⾔之,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
的⽭盾的不平衡性实际上是⼀种僵化的不平衡性。这样,阿尔都塞所宣扬的诸多不平衡的⽭盾,被视为⽭盾在社会形态
中的⾃发性变化,⽽历史科学只能被动地理解这种⽭盾的⾃发性变化。与阿尔都塞不同,巴迪欧选择⾛向⽑泽东的⽴
场,正如巴迪欧指出的:“对于⼀个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写的⼀就是思考对⽴统⼀,即将运动视为⼆分。辩证思维是
唯⼀的主体过程的思维,因为它撼动了⼤写的⼀的全能性。” ⽽唯⼀能实现这种辩证法的,只有⽑泽东。
⼆、⼀分为⼆与合⼆⽽⼀
有趣的是,巴迪欧对⽑泽东的《⽭盾论》的理解,是由⼀位中国哲学家做中介的,这位中国哲学家就是张世英。1978
年,⽩乐桑(Joël Bellasn)和路易·摩梭(Louis Mossot)将张世英《论⿊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译为法⽂。尽
管不懂中⽂的巴迪欧并没有参与翻译,但在阅读了译稿之后,他为这本⼩书撰写了两篇序⾔。巴迪欧之所以如此关⼼这
篇⽂章,是因为张世英理解的⿊格尔,代表着不同于当时法国,乃⾄整个欧洲对⿊格尔的理解。不过,巴迪欧也发现在
中国对⿊格尔的理解也不是完全⼀致的。实际上,“在1949年解放以前,⼀种⼗分‘经典’的新⿊格尔主义是主流,哲学家
贺麟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害怕辩证法的⾰命性,重视⿊格尔的国家理论,重视《精神现象学》,⽽不看重《逻辑
学》,或者说,他对《逻辑学》的结构和概念体系病态地猎奇”。巴迪欧的意思是,在中国存在着贺麟的⿊格尔的解读
与张世英的⿊格尔的解读的区别。贺麟的⿊格尔哲学与张世英的⿊格尔的解读的关键区别在哪⾥?⽤巴迪欧的话来说,
其中的核⼼仍然是⽭盾。巴迪欧指出,贺麟的⿊格尔⾛向了统⼀,将辩证法锁定在“正题—反题—合题”的枷锁之中,⽽
张世英看到了⿊格尔辩证法中更为根本的东西,即“辩证法⼀分为⼆”。⽽在⽭盾基础上的“⼀分为⼆”正是张世英认定的⿊
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张世英说:“⿊格尔断⾔:在现实中,⼀切具体事物都是⾃相⽭盾的……但是,现实中所存在
的实际⽭盾则与形式逻辑的⽭盾律所要排除的⽭盾根本不同,这种⽭盾是⼀种‘必然的,内在的⽭盾’……这种⽭盾不但
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且是正常的现象,它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在张世英那⾥,外在的现实世界是⼀个充满着各
种各样⽭盾的世界,不可能⽤连贯的形式逻辑来彻底穿透,也不可能将充满诸多⽭盾的现实社会统⼀在⼀个抽象的概念
之下。现实就是现实,⼀个在⽭盾中运动变化发展的现实,不能⽤我们头脑中的抽象观念或逻辑来消灭,⽽这正是⽑泽
东在《⽭盾论》中提到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盾及为此根本⽭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到过程完结之⽇,是不会
消灭的”的原则最⽣动的阐释。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他⾃⼰的《⽭盾论》⼀书中,巴迪欧概括了⽑泽东的⽭盾论:“我们可以⽤五个根本的辩证法命
题来概括⽑泽东谈的对⽴统⼀规律,这五个命题是:(1)所有现实都是过程。(2)所有过程归根结蒂都可以归结为⽭
题来概括⽑泽东谈的对⽴统⼀规律,这五个命题是:(1)所有现实都是过程。(2)所有过程归根结蒂都可以归结为⽭
盾的集合。(3)在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盾中),总是存在着主要⽭盾。(4)所有⽭盾都是不平衡的:换句话说,⽭
盾中的⼀⽅总会⽀配着⽭盾的总体运动。这就是⽭盾的主要⽅⾯的理论。(5)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盾,这些⽭盾的分
解来⾃于不同的过程。其中最终的区分是对抗性⽭盾与⾮对抗性⽭盾。”
对于巴迪欧概括⽑泽东的《⽭盾论》的内容,我们不需要⼀⼀解释,但是其中有两个内容需要注意:
(1)巴迪欧认为,现实过程并不⼀定要求最后的统⼀。⽭盾是⿊格尔辩证法思想最核⼼的“合理内核”,也被张世英描述
为“⿊格尔哲学的⾰命性”。⿊格尔的问题是,他总希望⽤⼀种绝对整体的观念来解决现实中的⽭盾,但是,倘若这个绝
对观念不存在,在纯粹的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种对⽭盾的终极解决,即庸俗意义上的对⽴统⼀规律。这种统⼀
性,即便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在巴迪欧看来,仍然是⼀种形⽽上学。
(2)这样,更为重要的是,巴迪欧认为⽑泽东的《⽭盾论》最核⼼的思想就是“⼀分为⼆”:“唯有了解‘⼀分为⼆’的原
则,我们才能理解作为过程的现实。⼀分为⼆并不是⼀⽣⼆。⼀分为⼆代表着:统⼀体的分裂。现实不仅仅是⼀个过
程,⽽且也是分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任何预先给定的“⼀”都不能统⼀分裂出来的“⼆”,分裂的“⼆”本⾝是⼀个异质性
的存在,它已经⽆法回归到“⼀”的框架下。在此,巴迪欧肯定了⽑泽东的“⼀分为⼆,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
法”的判断。
相对于“⼀分为⼆”,巴迪欧反对将辩证法理解为“合⼆⽽⼀”。1964年5⽉29⽇的《光明⽇报》刊载了杨献珍的⽂章《⼀分
为⼆和合⼆⽽⼀》,提出了“事物既
是⼀分为⼆,也是合⼆⽽⼀的”。巴迪欧按照⾃⼰对⽑泽东《⽭盾论》的理解,批判了杨献珍的观点。巴迪欧说:“为了
达到对⽴统⼀的平衡,杨献珍正好终结了⽭盾的普遍性,也即是说,终结了整体⽆法阻挡地分解为⽭盾的诸项的过程。
”巴迪欧认为,⼀⽅⾯,杨献珍提出“合⼆⽽⼀”,是为了找到⽭盾各⽅的共同点,从⽽找到让⽭盾各⽅和解的⽴⾜点,但
是巴迪欧坚持认为:“⽭盾各⽅的交集为空集。”我们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可以让⽭盾各⽅共同依存的基础。另⼀⽅⾯,巴
迪欧认为杨献珍试图找到⽭盾共同点在动机上是错误的,因为相互依存的交集,始终指向⼀个未分裂的过去,⼀种维持
过去不平等状态的⽴场。真实的⽭盾指向的⼀种从未出现过的未来,这个未来并没有保证⽭盾的最终解决,因为⽭盾的
发展必然是对既定现状的打破,去⽣成⼀种从未出现过的未来。⼀分为⼆,即指向未来的⾰命运动。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论对于⽑泽东的“⼀分为⼆”还是对于杨献珍的“合⼆⽽⼀”,巴迪欧都从⾃⼰的⾰命⾓度有着不同程
度的误读。但是“⼀分为⼆”的主张⼀直贯穿着巴迪欧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始终。后来,巴迪欧曾多次谈到了⽑泽东的“⼀分
为⼆”:“如何综合(合⼆⽽⼀)被当作主体性的公式,这是对⼀的欲望,……对⼀的欲望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
在‘合’的外表下,呼唤出来的是⼀个古⽼的⼀。这种辩证的解释因此是复古的。为了不⾄于保守,为了在今天成为⼀个
⾰命派,都必须要⼀分为⼆。”在这⾥,巴迪欧⾃⼰的理论意图已经⼗分清楚,他所希望的是不断前进的⾰命,因为⾰
命需要不断地创造出新事物(即⼀分为⼆),与当下决裂,“它在独⼀⽆⼆的⾏动中开创⼀个新的过程,通过⾏动,让
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价值”,这是⼀个⾯向未来的政治,⼀种创造出新的进程的政治,也是让之前⽆价值的东西获
得价值,这是巴迪欧的辩证法,即⼀分为⼆。
三、超越决定和主体介⼊
或许,从⼀分为⼆的⾓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巴迪欧与齐泽克在⽑泽东的《⽭盾论》理解上的细微差异。在英⽂版
导⾔中,齐泽克指出:“这就是⽑泽东的关键论点:主要的(普遍的)⽭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特殊⽭盾所掩盖——普
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种具体情况下,⼀种不同的‘特殊的’⽭盾是最主要的⽭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
要⽭盾的⽃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盾作为最主要的⽭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争都必须降⾄从属地位。
”显然,在齐泽克看来,这⾥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各种“特殊”的⽭盾。尽管在《⽭盾论》中,⽑泽东曾谈过主要⽭盾
和次要⽭盾的关系问题,即“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盾都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
住主要的⽭盾”。齐泽克指出了⽑泽东的这个论断的两个层次:(1)任何既定状况都可以分为主要⽭盾和次要⽭盾,在
⼀定的历史时期,在⼀定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捉住主要⽭盾,才能解决问题。(2)由于⽑泽东不认为主要⽭盾和次要
⽭盾的区分并不是某种客观规律决定的,⽽是针对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做出的判断,⽽且他认为主要⽭盾和次要⽭盾的关
系在⼀定时期会发⽣转换,原先对抗性的主要⽭盾在⼀个新的背景下会变成次要⽭盾,让位于新的主要⽭盾,反之亦
然。那么,齐泽克认定,⽑泽东并不认为存在着某种统⼀的综合体。这样,如果没有否定之否定在更⾼阶段的综合,齐
泽克判定⽑泽东“坚持认为⽃争、分离是⾼于所有分析或综合的”,即⽃争是永恒的,⽽综合和调和才是暂时的。
巴迪欧基本上认可齐泽克的评价。但他认为,⽑泽东的主要⽭盾和次要⽭盾的区分,实际上是从中国⾰命的⽃争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早年的巴迪欧就认为,真实世界就是⼀个有着多种多样⽭盾的世界,不能⽤单⼀观念加以解决。巴迪欧在
六⼗年代阅读了⽑泽东的《中国的红⾊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的⽃争》,看到了“⼆⼗年代的中国”复杂的状
况,这样,⼆⼗年代的中国并不是由单⼀⽭盾或对⽴决定的历史状况,⽽是⼀种“⽆序状态”,在《世界的逻辑》中,巴
迪欧指出:“在中国⼆⼗年代,⽑泽东的⽴场依赖于⾟亥⾰命事件:清政府的崩溃,以及民国的诞⽣。但是,它绝不能
简单等同于断裂。1912年之后,在‘中华民国’时期,实际上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对此,⽑泽东写道:“帝国主义和国
内买办豪绅阶级⽀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军阀混战超越决定了
内买办豪绅阶级⽀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军阀混战超越决定了
(surdéterminé)萦绕在中国历史世界中的实证性特征:在这样⼀个分解的反动⼒量的空间中,明显指明了⾰命军队的
道路。”
实际上,在巴迪欧看来,⽑泽东在《中国的红⾊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年代的中国”的真实状况是⼀种近
乎⽆解的状况。这⾥的超越决定已经被巴迪欧赋予了数学上的含义,即⼀种类似于数学上超定⽅程(équation
surdéterminé)的状况,按照数学上的定义,超定⽅程是限定条件(如⽅程数量)超过了未知数的情况,这样的⽅程组
通常是⽆解的。在巴迪欧看来,超定⽅程的⽆解,对于理解⽑泽东的⽭盾论,是⾮常有启发意义的,即⾯对存在诸多⽭
盾时,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强⾏考察所有制约因素。恰当的做法是类似于数学上解超定⽅程中使⽤的最⼩⼆乘法,找出诸
多⽭盾中最重要的决定因⼦,并依照这些决定因⼦给出⽅程的近似解,相反,那些次要的因⼦被回归到决定因⼦的范畴
下。
⽑泽东⾯对⼆⼗年代中国⾰命的状况处理⽅式与此⼗分类似。当谈到中国红⾊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时候,⽑泽东并不
是希望⽤红⾊政权或井冈⼭的⾰命⽃争⼀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如⽑泽东谈到井冈⼭⾰命根据地的复杂⽃争形势
中,“边界的⽃争,完全是军事的⽃争,党和群众不得不⼀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怎样作战,成为了⽇常⽣活的中
⼼问题”。简⾔之,将井冈⼭的⽃争主要作为军事问题,就是⽑泽东在那个时期指出的⽃争的主要⽭盾,尽管在井冈⼭
根据地还存在着⼟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乃⾄中国⾰命性质的问题,但⽑泽东认为当时最主要的⽭盾就是⽤
武装割据的⽅式,在井冈⼭地区站稳脚跟,打退各⽅⾯敌⼈的进攻。所以,巴迪欧指出:“我已经分析过,青年时代的
⽑泽东在1927年的井冈⼭的⼈民战争中的讨论。对于⽑泽东来说,‘红⾊政权’是由各种不同因素组成的,⼯农兵的代表
会与党组织⼀样重要,但军事问题在那个时期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于是,抓住主要⽭盾的⽅式,是⽑泽东解开⼆三⼗
年代中国⾰命⽃争的超定⽅程组的最⼩⼆乘法。这就是“⼀分为⼆”,将所有⽭盾变成主要⽭盾和次要⽭盾,变成⽭盾的
主要⽅⾯和次要⽅⾯,⽽对于复杂的不连贯的现实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在所有⽭盾中决定什么是当时中国⾰命⽃争
的主要⽭盾,将所有的⽭盾都放在这个主要⽭盾的框架下来解决。巴迪欧对⽑泽东的评价是:“我们如何了解⼀个元素
和事件痕迹之间关系的价值?⽑泽东的回答是:通过讨论、集会和政治教育。⽆论他们原初成分是什么,关键在于要让
⼠兵们知道‘都知道是为了⾃⼰和⼯农阶级⽽作战’。”
也正是在这⾥,巴迪欧给出了他对⽑泽东“⼀分为⼆”的理解,⼀分为⼆绝不仅仅是⼀种⽃争哲学,也是⼀种在诸多不定
因素中找到⼀条出路的⽅式,将所有的⽭盾⼀分为⼆,分出主要⽭盾和次要⽭盾,分出⽭盾的主要⽅⾯和次要⽅⾯,抓
住⽭盾的主要⽅⾯,也抓住主要⽭盾,才能⾛出眼下的困境,找到⼀条出路。巴迪欧认为,⽑泽东的⽭盾解法实际上是
⼀种主体介⼊的⽅法,就像那个著名的“⾼尔丁死结”⼀样,所有⼈都解不开弗吉尼亚城那个系在⽜车上的死结,正是他
们都企图找到⼀个绳头,在绳头的指引下,将死结依次解开,但是亚历⼭⼤⼤帝的解法很简单,他拔出佩剑,⼀下
将“⾼尔丁死结”劈成两半——这就是⼀分为⼆!这也正是⽑泽东《⽭盾论》中的核⼼:⼀分为⼆。
砍断“⾼尔丁死结”的亚历⼭⼤⼤帝和⽑泽东都有着明确的主体介⼊。在这⾥,齐泽克认为⽑泽东“陷⼊了简单的、完全⾮
辩证的、‘恶的⽆限’的观念的⽃争中。”巴迪欧并不赞同齐泽克的评价,巴迪欧的回答是,只有⽤主体介⼊的⼀分为⼆,
才能从诸多纷杂的⽭盾和决定因⼦的复杂⽽⽆解的环境中开辟⼀条新的道路。这样,新时代在⼀分为⼆的辩证法中开启
了,他们不再在诸多细微因素⾯前徘徊不前,⽽是⽤暴⼒的⽅式在复杂⽆解的现实状况中⼀分为⼆,让未来可以在⼀条
明确的线索中以新的⽅式降临,在这个⼀分为⼆的主体的⾝体之下降临。
【作者:蓝江,南京⼤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研究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导师。本
⽂原载《⽑泽东邓⼩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发布于:2023-11-01 04:02:42,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9878256320275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不平衡矛盾与一分为二—巴迪欧论毛泽东《矛盾论》.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不平衡矛盾与一分为二—巴迪欧论毛泽东《矛盾论》.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