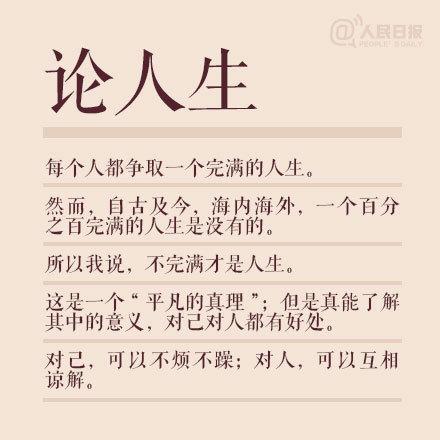
修辞在多⼤程度上与真理相关——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
作者张⽂喜|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
⼀
1.⾃从公元前五世纪修辞(辩论)作为西⽅⽂明的⼀门艺术诞⽣以来,关于该学科的合理性就引起了很多争议。也许,最
早为⼈接受的恐怕要数修辞是“使真理更有效”的⼀种⼿段这⼀观点,或者,像理查德·威佛在其对柏拉图的评论中所说的
那样,“修辞是加到真理上的⼀种冲动”,这些观点所包含的意思是,“真理”是早就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修辞的功能是劝
说⼤众或次⼀等的⼈。这种或其他⼀些贬低修辞的观点可以被称作“旧修辞”观的修辞所特有的。
因此,从语⾔研究的层⾯来说,注重逻辑、语法并且⽤逻辑、语法压制修辞,是西⽅传统哲学的特点,据信,语法的真
正本性应该是“把⾔语的彻底可能性归于确⽴表象的秩序”,(注:福柯《词与物——⼈⽂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
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它管的是语词在短语和句⼦中的位置,为⼈的话语规定规则,恰如⼈为⾃⼰的判断规定
规则的逻辑学⼀样,它们涉及的是语⾔的形式⽅⾯的问题,就其语⾔⾃⾝的形态⽽⾔,语法和逻辑与时间、地点和使⽤
环境⽆关,由此,契合了“真理只有⼀个”的传统看法,既然真理只有⼀个,岂能与⽤什么话去说它发⽣关系?
我们这⾥提出的问题是:源于古希腊哲学、经过启蒙运动以求真观念为核⼼的西⽅传统哲学,假定了真理跟修辞没有关
系,跟语⾔本⾝、跟做语⾔游戏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去理解⼀篇哲学⽂献,也许恰恰就是去理解有关论证的确实性和它
的概念的融贯性,逻辑的精确性、透明性是真理的标准。就像笛卡尔所以为的,“⼀切真实的东西,⼈们都可以清楚、
准确地理解。”实际上,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对于任何⼀篇其作者希望不仅像⼀架有⽣命的图灵机——⼀种可不受储存
容量限制的假想的计算机——⼀样作出论证,⽽且希望通过说服,使我们有所相信的作品来说已是明摆着的,这种观点
将某种特有的真理优先权判定给作为典范的柏拉图主义,即通过理念来解释⽣活。理念就好⽐是哲学之线上的⼀
个“点”,各种这样的“点”依照逻辑推演,沿着⾃⼰的整个长度复制⾃发的认识线索和普遍纽带,从此以后,“哲学”家们便
处于⼀种窘境之中:哲学家们总要追溯源头,“只要你没读过这个或那个,没读过关于这个的那个和关于那个的这个,
你就不敢以你的名义讲话。”(注:德勒兹《哲学与权⼒的谈判》[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页。)
因此,⼈们不免感到惊奇,在哲学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从根本上说出来的都是同⼀回事,⾄于如果倒确证了哲学史在哲学
上⾏使着这种明显的“同化”或“镇压职能”,那么此见对于⽇常理解⽽⾔却⼜是⼀种粗疏的过分要求。如果胡塞尔、康德、
笛卡尔和柏拉图⼀样,说的都是同⼀回事的话,或者说,⾃古以来的哲学就存在于替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中的话,那
么还要这部纷然杂陈的西⽅哲学史⼲什么呢?那么“⼀个”哲学就够了,⼀切都总是已经说了嘛。(注:参见海德格尔《形
⽽上学导论》[M],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8页。)显然,不待说的是,这种看法提⽰了:对在哲学家
中哲学写作的风格和多义的隐喻,包括对⽭盾语的特殊运⽤所致的⼀切⽅法论⽅⾯的后果,西⽅传统哲学注意甚少。直
到现在,⼤多数批评家都还坚持把具有超逻辑的倾向之“诗化的”和隐喻的写作风格看作是“⽂⼈”所爱、但哲学家却要竭⼒
去忘掉的那种修饰。
2.⽆论原因如何,从历史上说,真理和修辞之间的这种对峙关系起源于两种正好相反的⽣活⽅式——⾸先是巴门尼德然
后是柏拉图所解释的哲学家的⽣活⽅式和智者的⽣活⽅式:由于⼈们中的⼤多数都不精思明辨,也⽆熊熊热情要懂得真
理,就有必要编排出表述⽅法的种种⽂学形式,⽬的在于活⽣⽣的、进⾏中的“说话”或“规劝”。“传授修辞学的”智者的本
质⽣存样式就是异乎寻常地、⾼度亢奋地、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说话中,智者和演说家是同⼀类⼈,他们“不需要知道事
情的真相,⽽只要发现⼀种说服的技巧,这样他在⽆知者中出现时就能显得⽐专家更有知识”。(注:《柏拉图全集》(第
1卷)[M],王晓朝译,北京:⼈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照柏拉图的这种解释,修辞学之基本的前提条件在于,⼤
多数⼈都有依附于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区的普通、正规或正统观念即意见的倾向。但这些意见因时因地⽽⼤不相同。相
反,与⼤众对于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意见针锋相对的是哲学家的真理,这些真理就其本性来说是持续存在的,因⽽从
中可以引申出赋予⼈类事务以稳定性的原则。
3.从散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对修辞学的评述来看,柏拉图将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对⽴,实际上铺陈为(特别是在《⾼尔吉
亚篇》中)“对话”(dialogue)形式的沟通和“修辞”(rhetoric)形式的沟通之间的对⽴,哲学对话的令⼈满意的极点就是真理或
启悟,⽽不是演说家对⼤众的说服。在真理之启悟的上升过程中,任何可能的提问都得到了回答,并且提问的论友们也
得到了联合,即启悟产⽣了使理念匹配、安排形式之间的⽣产能⼒。这种启悟不能仅仅在“规劝”意义上理解,⽽必须坐
实在既推⼜拉:作为推,就是服从逻辑约束、以及在哲学对话中应和论友之提问的必要性,如果有⼈拒绝,那么这是因
为,甚⾄说也不⽤说,他已经漠视了⼈之最可贵的理性天赋,⽽且不准备遵守涵养着平等的⾃由思想的辩证法;作为
拉,就是受敞开的真理的吸引,就像飞蛾扑⽕。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家“在领悟每⼀个事物的本性之前,不会松懈强烈的
爱,这种爱也不停息,……⽽⼀旦靠近它,并与真正的存在结合,⽣出了理智与真理,他就会懂得真理,真正地⽣活,
得到滋养,从⽽他的劳苦才能平息”。对于柏拉图,哲学就是⼀门关于爱情的⽞秘学问:哲学就是对于爱情的最⾼的、
最纯粹的形态——智慧——的爱,也就是爱理念,爱⾄善⾄美的eidos,或者去爱神。因此,在《斐德诺斯篇》中,柏
拉图虽然也从发难修辞学开始,但是,柏拉图在这个对话中阐述了他理想的修辞学:真正的修辞来⾃神灵的启迪,真正
的修辞家在演说时,是神在说话。换⾔之,如果说真理是客观的绝对的,⽽“坏”的修辞学可以使真理失去光辉,那
么“好”的修辞学必然是对真理的⼀种服从性的解释。
么“好”的修辞学必然是对真理的⼀种服从性的解释。
4.相应地,“⾔说”不具有本体性,⽽不过是作为私⼈⼒量的⾓⽃,所以,修辞学的本质是什么?能⾔善辩是不是⼀件好
事?这⼀肇始于柏拉图的道德上和哲学上的追问,穿越历史⼀直反复地被提起,反复地被回答。
所谓“修辞学”,亚⾥⼠多德将其归⼊到“政治学”,视修辞为“在每⼀件事上发现可⽤的说服的⼿段的能⼒”。(注:
Aristotle:Rhetoric,in Rhetoric and Poetics of Aristotle[M], Roberts(New York:Random Hou,1954),P.24.)
这⼀实⽤修辞观透露了修辞发展的城邦政治背景,即在城邦公共⽣活中:公民⼤会、法庭等等地⽅,要赢得成功,必须
以说服的⽅式赢得⽀持。于是,对说话技术的探讨便成为修辞术,如果说修辞术的技术性特征,作为政治上达成普遍协
调的基础,那么,说到底,“协调”不过是⼀种“技术信仰”的表达。按今天的语⾔⽤法,千篇⼀律的“技术性”是现代性的标
志,让⼈们马上想起施⽶特的话: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为什么在政治空间中需要“权威”?因为正是意见,⽽不是真
理,属于所有权⼒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因⽽,“所有政治的观念、提法和说法都有⼀个论战的含义;它们眼中有具体的针对性,与具体的处境联系在⼀起,其
最终结果是(在战争或⾰命中表达出来的)敌友阵营。如果取消这⼀处境,所有政治的观念、提法和说法就成了空洞的、
幽灵般的抽象。”(注:施⽶特《政治的概念》[A],载《施⽶特:政治的剩余价值》[M],刘宗坤等译,上海⼈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44页。)⽽如果没有那些具有同样的⼼向的⼈们的⽀持,即使是最专制的统治者或独裁者也不可能获得权
⼒,更不要说维持权⼒了。这意味着,在所有政治⾏动中,我们难以避免政治争论或⾃说⾃话,为避免⾃说⾃话,⼈们
却需要某种共同的东西,或⾄少理想地预设⼀种和平的、终⽌了任何此类争论的共同⽣活。但是,这样⼀种完全⼀致的
理想恰恰不适合于政治争论的特性。在伦理学的奠基之作《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多德早已在原则上把运
⽤在政治讨论上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与“知识”(episteme)区分开来,因为他认为⼈类事务复杂多变⽽不可能精确地研
究它们。
可见,在亚⾥⼠多德那⾥,我们仍然可以读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能⼒”之间的区分:即“可靠的理性”和“有⼒的雄辩”之间
的区分,前者建⽴在真理的原则基础上,⽽后者建⽴在意见和⼈们的热情和兴趣之上,也就是建⽴在⼈类事务的流转变
迁中。但是这⼀区分本⾝仍然基于⾃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直梦想着的有关统治政治共同体的“科学”,原因即在于⾝
为学者的他们追求着⼀种在原则上克服分歧的真理中的共同性。不过,亚⾥⼠多德的政治著作有意使⽤了“反语”,掩盖
其对“⼈具有在⼈类事务的流转变迁中展⽰规律或秩序的‘⾃然’(本性)”的根本反思。(注: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
治哲学史》(上卷)[M],李天然等译,⽯家庄:河北⼈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除⾮我们理解了他的修辞,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在亚⾥⼠多德伦理学中,虽然作出了关于“实践哲学”(phronesis)与“理论
科学”之区分的根本性解释,但有⼀点始终是不清晰的: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政治知识,同专家的技术知识究竟关系
如何?在这⼉应该看到,实践哲学并不是在语法或修辞学当中的技艺意义上的⼀种对⼈类社会实践规则的知识。相反,
它是对这样⼀种知识的反思,并因此说到底是“普遍的”和“理论的”。另⼀⽅⾯,亚⾥⼠多德承认,这种实践哲学固然是⼀
种“普遍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是批判性的。因此,修辞,正如⾃古以来清楚地显⽰的那样,引发了情绪激奋,但它绝
不会由此跳出合理性的范围,倘若说修辞学具有某种规劝因素,那么这种规劝因素乃社会实践之必需。在这⼀意义上,
亚⾥⼠多德就不把修辞学称作技艺(techne),⽽是视为⼒量(dynamis),(注:参见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选集》[M],邓安
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153、537页。)就是说,“好”的修辞以真理为依据,以避免受“坏”的修辞如诡
辩修辞的影响。正如亚⾥⼠多德在他为修辞所作的辩护中说的那样,真理本⾝往往能胜过谬误;但是在与谬误的竞争过
程中,当熟练的⼈们想让谬误取胜时,真理就必须求助于⼀个尽量吸引⼈、尽量说明真相的环境。在天堂的王国⾥,真
理也许是⾃⼰惟⼀的拥护者,但它若要在尘世中健康地⽣存就需要强有⼒的帮助。在这⼀意义上,柏拉图和康德⼀样是
⼀个雄辩家(rhetorician)。
5.遗憾的是,传统的西⽅哲学因为把真理视为⼀种绝对的、形⽽上学思辨的产物,所以,修辞学要么被假想为真理的“敌
⼈”,要么被贬低为对真理的⼀种服从性的⼯具。这⼀点与逻辑和语法的传统要求相符合:在传统哲学⾥,符号与符号
所指称的东西是严格地区分开的,因为符号是在时空中,⽽符号指称的观念则被设想为超时空的。这⼀论点预设了德⾥
达对“先验所指”的搜寻和批判。
⼆
1.当后现代主义将真理、知识、现实锚定在种种符号结构中,界定为各种符号的“模拟展⽰”(鲍迪亚,Baudrillard)或“话
语”(福柯)时,后现代主义实质上也就变成了修辞学,也即新修辞学了。在新修辞学中,⼈们把概念话语的意义特征称
为“隐喻性的”,伽达默尔在对“概念史与哲学语⾔”的考察时指出,“⾃从赫尔德以来,语⾔之⼀般的隐喻意义越来越多地
从根本上得到承认。”隐喻的认识功绩“源于对原初意义域的继续聆听。这构成了话语的有关成就。”(注:参见严平编选
《伽达默尔选集》[M],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153、537页。)隐喻的修辞效果是:它能把某物
从⼀个领域带到另⼀个领域,也就是说,只要记住背景本⾝,就能记起意义的原初领域。隐喻从中取义,并由此进⼊新
的领域。不过,我们应避免⼀种印象:似乎只有当词语在隐喻使⽤中扎了根,并失去其被吸收、转义的特征,它在新语
境中的意义才始成“正确的”意义。⽐如,按其我们语⾔中所使⽤的特定表述来看,“开花”只在植物界使⽤才有其正确的功
能,把这个词⽤在更宽⼴的别的领域,就被某些语法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不合适的,只不过是⼀种⽐喻的⽤法。如果站
在修辞学的⽴场上来批判逻辑学的传统,那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解释不了德⾥达所论述的缺席(abnce),即意义
在修辞学的⽴场上来批判逻辑学的传统,那么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解释不了德⾥达所论述的缺席(abnce),即意义
的离散(dismination)。语⾔产⽣意义不是通过对某⼀对象的指代或某⼀真正所指的在场,⽽是由它本⾝的性质所决定
的。这样⼀来,德⾥达的解构,说的就是采取⼀种语⾔学的相对论⽴场:⼀切皆⽐喻,在我们⾃⼰的⽂本之外没有任何
优势的⽴⾜点,“先验所指的缺席⽆限地伸向意谓的场域或游戏。”(注:德⾥达《书写与差异》(下册)[M],张宁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5页。)
2.在这⾥,解构说隐含着⼀种“战⽃的⽆神论”,它从各个向度向关于先验性所指或者意义的终极实在,或者“存在——神
学”(注:德⾥达在《论⽂字学》等著作中将海德格尔哲学直呼为“存在—神学”。)全⾯宣战。它有赖于尼采式的权威批判
和尼采对诗意识的虚⽆主义的肯定,使逻辑学传统希求达到单⼀的修辞⽽避免迷失在诠释的⽆底深渊的可能性变得不可
能,从⽽⼏乎⽆可挽回地使话语失去了作为真理的载体或媒介的功能。从这⼀意义上讲,⼀位演说家所说的“紧急情
况”永远是⼀种虚构。
职此,德⾥达的著作在修辞学者中的影响微不⾜道就是意料之内的事。因为,德⾥达也许能⾯对意义的离散所陷⼊的诠
释的⽆底深渊,可那些如海德格尔那样仍想抓住正在作品⾥发⽣的真实的⼈却希望相信修辞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存在,正
是这⼀点在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评论中被断定为“⽆⾮就是把⽆意义性当作意义来赞美”的存在的神话。(注:参见阿多尔
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8页。)事实上,我们也清楚海德格尔和德⾥达⼒图推
翻什么,可是我们不清楚德⾥达想肯定什么。相反,海德格尔指出了新的道路,在此道路中,他为了以⼀种新的⽅式提
出问题,以改变传统对形⽽上学的批判,并由此发现他⾃⾝是处于通过语⾔的途中。
我们知道,这条语⾔之路并不关注表述判断,或把语⾔的意义归为有个什么对象,⽽是使⾃⾝总是关注“存在”的意义问
题。这倒不是说,传统的形⽽上学忽视了存在论,恰恰相反,每⼀个构造形⽽上学体系的本体论的必要构架是要谈存在
论。但是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受逻辑学传统诱使,传统的那种谈法,显然总是处⾝于理智贬压情感,并迷失在关于世界
的理论静观⽴场和模式化的形⽽上学的真理概念之中,谈了半天实际上谈的是存在者——那东西已经发⽣过了,意义已
经现成地摆在那⼉,然后去谈存在,实际上这是根本不成⽴的。存在的意义永远⾛在谈论之前,传统哲学之所以遗忘了
存在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到那“前”维度⾥头来。在海德格尔看来,“前”维度的特性在于它的原本性,没有别的东西可以
依靠,它⾃⼰在那⼉发⽣,(注:参见张祥龙《朝向事情本⾝——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
232-233、221页。)如果不是先有它的发⽣,我们怎么能够谈得上是合乎真理还是不合乎真理?
3.《存在与时间》的第29节,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亚⾥⼠多德的《修辞学》的讨论,寻找“情绪”本体论的资源。他把
《修辞学》有关“激情”的讨论,视作第⼀部⾮“⼼理学”系统解释情绪现象的著作。在这⾥,我们看到,“作为常⼈的存在
⽅式的公众意见不仅⼀般地具有情绪;⽽且公众意见需要情绪并且为⾃⼰‘制造’情绪。演讲者的发⾔⼀会⼉⼊乎情绪⼀
会⼉出乎情绪。演讲者须了解情绪的种种可能性,以便以适当的⽅式唤起它,驾驭它。”在情绪变迁中,在某⼈感觉到
⾃⼰如何如何时,他的“存在”就到“场”了。情绪是“⽣存”常态,是“场”的打开,情绪打开了“存在”。在“知”、“情”、“意”之关
联于真理问题上,海德格尔由此将“情”摆到了更原始的位置上。在这个⾓度看,海德格尔的全部思想应该在这样⼀个“⽆
区别”或“不计较”的“前”维度中来理解,这是⼀个“前反思”、“前判断”、“前概念”、“前主客体之分”等等所有这之“前”的⼀个
维度,⽽这个维度⼜是在发⽣之中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海德格尔的修辞艺术中有⼀种空域,⼀般⼈都会觉得他的话
是“诗意”的、“舞蹈”的、悬空的、形式显⽰的。简⾔之,“它讲什么不在乎讲个具体的什么,但是它给你讲出了⼀个充满
了关系含义、冲动含义、趋向含义的那么⼀个境界。”(注:参见张祥龙《朝向事情本⾝——现象学导论七讲》[M],北
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3、221页。)
从修辞学的⾓度看来,海德格尔著作的关键处有两个问题:
第⼀,它意味着不管什么,只要是不使⽣活经验本⾝变成⼀个对象的思想话语就都是好的,只要能“使思想流动”的都是
好的。海德格尔式的表达⽅式很少谈到与另⼀个⼈交谈的可能性的唯⼀⽅⾯是:我们都有某事(某种具体的东西)要对彼
此诉说。所以我们阅读做着各种各样语⾔游戏的海德格尔著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想理解他想说什么,他为什么想
说,否则,我们就成了在那⾥接收信息的⼈,以此⽅式语词⼜如其在观念形⽽上学那⾥⼀样变为束缚性的。
第⼆,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语⾔单元不是句⼦,⽽是词语”。(注:图根哈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
[A],转引⾃孙周兴选编⿊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2页。)因⽽,⾔说的原始
⾏为不是命题性的联结,亦即陈述情形下“关于某物说什么”的语义形式,⽽是纯粹诗意的命名,也即“道说”(Sage)。“道
说”意味:“显⽰、让显现、让看和听”。(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2、
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页。)“道说”是某种与我们的说相分离的、⽽必须架设⼀座桥梁,⼀座从
存在论意义上的发⽣现象学的桥梁才能通达的东西。
这说明了⼀个事实:⼈若不⾸先学会⼀种语⾔就不能谈论这种语⾔,更不⽤说像使⽤⼯具那样使⽤这种语⾔。虽然,语
⾔⽆可否认地与⼈类的说维系在⼀起,但是“如果⼈(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是通过他的世界敞开状态成为⼈的,并
且这种世界敞开状态本⾝是在⽆⼈称的⾔说中得到联结的,那么,就可以猜测:⽆论是在有所引发的命名中还是后来的
命题性句⼦构成”,都是以⼀种原始的⾔语⾏为,即“道说”为基础的。根据⿊尔德的阐释,这种原始⾏为的考古学的回声
就显现在“亮了”、“真可怕”之类的所谓“⽆主语的”或说“⽆⼈称的”句⼦中。因⽽,“真正的语⾔单元就是单词句,在其当下
情调性的展开状态中的世界整体是靠这种句⼦被唤起的,也就是说,⼀种世界的命名⾸先变成了事物的命名。”(注:孙
周兴选编⿊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2页。)
周兴选编⿊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2页。)
由此⾓度来理解的语⾔之本质,同时就显⽰了海德格尔的“⾔语交际”观之⼏乎尚未被⼈们思虑到的东西。对海德格尔⽽
⾔,“相互说”意味:“彼此道说什么,相互显⽰什么,共同相信所显⽰的东西。”“共同说”意味:“⼀起道说什么,相互显⽰
在被讨论的事情中那种被招呼者所表明的东西,那种被招呼者⾃⾏显露出来的东西。”(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
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2、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页。)我们很清楚,根据
这⾥提出的“⾔语交际”,它绝⾮是在古典意义上的规劝或说服听众,或笼统⽽⾔,使概念适应⼈、⼈适应概念,让“他
们”接受某⼀观点或采取某⼀⾏动,相反,海德格尔由此得出结论,“某⼈能说,滔滔不绝地说,但概⽆道说。”(注:孙周
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2、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
页。)
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总是特别显⽽易见的:由于⾔词有它“世俗的”(worldly)存在,所以,⾔词整体就像上⼿事物那样摆
在⾯前。语⾔可以被拆碎成现成的⾔词物,陈述主张、讲演、传达、说情、警告这类话语“不会没有它的‘关于什么’”。
(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9、193、194页。)⽆论真⾔、空⾔,
⼀旦达乎⾔辞或做成“像话”就变成了从某种⾓度、在某种限度内说到的现成事物,这与希腊以后⼈们把逻各斯整理为关
于现成事物的逻辑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反过来要使话语这种现象从原则上具有⽣存论环节的原始性和⼴度”,⽽真正了
解⾔说这种原始⾏为,就必须“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
联书店1999年版第189、193、194页。)这⾥考究⾔语的意义仍然是让(⼈)看见、显⽰、解蔽,这⼀点在海德格尔后期得
到强调,并把语⾔和真理从根本处连在⼀起:不是符号同被指⽰的东西的符合,更不是作为辩论的结论,⽽是⾔词让事
物如其所是地显现。
因此,海德格尔⾸先不是把语⾔理解为开⼝说话,⽽是理解为说话的原始根据。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为了追问“事情本
⾝”,“哲学研究将不得不放弃‘语⾔哲学’”,(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版第189、193、194页。)将不得不把如哈贝马斯之流的评判⼈⽣种种对话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性的标准忽略掉,
真理与宣传真理的适当的修辞⼿段之相互对⽴或相互⼲预的传统看法,在海德格尔做的“存在论区分”中业已显得问题重
重。
4.在如此显露中,⽤诗的语⾔(Sage)来谈说真理,成了现今反对概念思维⽽引⼈注⽬的见解。但是,诗的语⾔拥有⼀种
与真理的特殊的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精细的解说,按照⼀般的意见,真是认识的真,⽽认识就是判断,“判断
是真理的本来处所”。倘若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我们就难以离开概念思维,⽽去设想另⼀种关于真理的⾔说⽅式,与
此种态度紧密联结着的是古⽼的柏拉图对诗和诗⼈的异议——即“诗⼈常常撒谎”。
但是,此说涉及到哪⼀种“真理”?说诗的语⾔的形式不是“真实的”,这意味着什么?在此援引伽达默尔的询问是恰逢其时
的。(注:参见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选集》[M],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153、537页。)伽⽒所维
护的真理是⼀种前科学的、或者说前苏格拉底的真理。真理的原初意义,在于我们谈说真实,我们谈说我们意指的东
西,⽆论什么东西,只要它将⾃⾝展⽰出来,它就是真的。关键在于诉诸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
性的努⼒以解放固定的语词和语句。海德格尔曾反复论述过这⼀主题,并在后期著作中从30年代⼀开始主要还是谈真理
问题到50年代就直接谈语⾔问题,⼏乎把存在等同于语⾔,即“只有在合适的词语说话之处才有(es gibt)存在”(注:孙周
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2、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
页。)(“es gibt”即“给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词语从哪⾥获得它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资格?
海德格尔在《语⾔的本质》⼀⽂中,对格奥尔格(George)的题为《词语》的诗的探讨指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
语之中。所以才有下述命题——语⾔是存在之家。由此⽽来,我们或许就为⼀个我们早些时候道出的思想之命题提供了
⼀种从诗那⾥得来的最美丽的证明。”(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2、
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页。)但是,海德格尔这样说显然不是把诗贬降为“思想的附庸或思想的证
明材料”,在海德格尔那⾥,语⾔的本质是存在通过语⾔对我们所做的⾃我表达。对此的理解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格奥尔
格的诗。这⾸诗⼤意是说,“我”(指诗⼈)很幸运地在边缘状态得到了对词语的某种领会,那是远古的命运⼥神授给我的⼀
颗宝⽯,这颗宝⽯丰富细腻,她久久地惦量,然⽽向“我”昭⽰:在这个宝⽯的渊源深处⼀⽆所有。于是那宝⽯从我指间
滑掉,我的故⼟再没有得到那些宝藏,从此我哀伤地学会了弃绝,“弃绝”什么?“弃绝”那词语指称对象的传统语⾔看法,
最后神告诉“我”,“词语破碎处,⽆物存在。”(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
1132、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页。)
简单地说,诗中⽤神话⽅式表达了语⾔即本体的思想。因为语⾔是神赐给诗⼈的⼀件宝物,语⾔给我们带来原本的消
息。⽤约翰·麦奎利的话说,海德格尔在解释格奥尔格的神话意义时,强调的是诗⼈的解释就像圣保罗谈到的解释⼀样,
都是神赐的。也就是说,语⾔是古⽼的命运⼥神为诗⼈选择并传授给他的,语⾔不是诗⼈选择的,眼下我们听到了这样
⼀个重复的叠句:“语⾔的本质——本质的语⾔。”(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1132、1132-1133、132、1068、1068、1069、1079页。)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强烈地表明:“本质”⼀词具有的动词
和动态意义,他不能再跳到语⾔外头去,⽤别的东西⽐如“⼈”来解释语⾔,他只能就语⾔⾃⾝来说语⾔⾃⾝。对追问语
⾔的起源的问题的第⼀个有决定性意义的答案也在这⾥:“这个起源始终是谜”,“谜的性质就属于语⾔的起源之本质。”⼀
切都包含在语⾔中,海德格尔说,在语⾔中,“活的词语在打仗,在决定什么是神圣的、什么不是神圣的、什么是伟
⼤、什么是渺⼩、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崇⾼、什么是卑微、什么是主⼈、什么是奴仆。”(注:菲⼒浦·汪德
⼤、什么是渺⼩、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崇⾼、什么是卑微、什么是主⼈、什么是奴仆。”(注:菲⼒浦·汪德
尔《现代批评中的意识形态转变》[A],载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修辞学:话语演讲与批评》[M],常昌富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43页。)存在在语⾔中发⽣,将它与原始⼒量融合。
晚年的海德格尔⼏近⼊迷出神,不闻⽇常⽣活,不闻语⾔既源于现实,⼜服务于思想。从中透露了海德格尔沉迷于存在
的充实,他对那最初的事物于其中⾃动向孩童般的希腊先哲们显现的灵光的沉迷,所显⽰的不就是⼀种类似于对原始可
能或者说⼈类社会“曾如何⽣活”的沉迷?但是不管存在多么迷⼈,它并不伐⽊、荷锄、商业往来。履⾏这些⼯作的是⼀
些具体的活⽣⽣的⼈。海德格尔可以说存在揭⽰了这⼀切的可能性,语⾔就是原始诗作,诗是⼀种展现或提⽰,然后,
柏拉图的说法不是已经说了,诗的多功能的真实性并不能解释现实的问题,在战⽕硝烟和权⼒⽃争⾯前是没有诗⼈的位
置的。
现须追究,这是否说海德格尔把哲⼈现象学地还原为诗⼈,因⽽传统哲学和哲⼈孜孜索求的“何为值得过的⽣活”的问题
也就被取消了?要讲明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能⼒之范围。但是,⾮常明显,我们在此找到了回答此⼀问
题可以相类⽐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奠基于⼀个迥然不同的基础。在此,归根到底需要提及前述业已说到的诗的语⾔作
为提⽰,也就是要求诗的词语如何才能恰恰通过拒斥任何⼀种具体所指⽽找到它的实现。
因此,问海德格尔所“意想的”⽥间劳作、⼈际交往、城市建设以及国家的各种权势调度所牵扯到的各种相互竞争的⼒量
之间的选择等等事务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这种问法是毫⽆意义的。这⽆疑等于否定了“海德格尔的修辞艺术中有⼀种
空域掩盖着它与经历过战争的可怕的毁灭的听众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量”(注:菲⼒浦·汪德尔《现代批评中
的意识形态转变》[A],载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修辞学:话语演讲与批评》[M],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43页。)之评断。

本文发布于:2023-10-27 17:13:40,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98398020198259.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修辞在多大程度上与真理相关——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修辞在多大程度上与真理相关——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