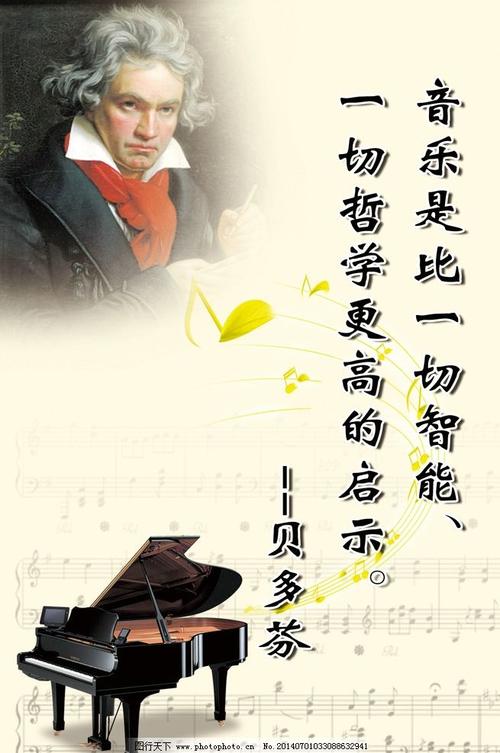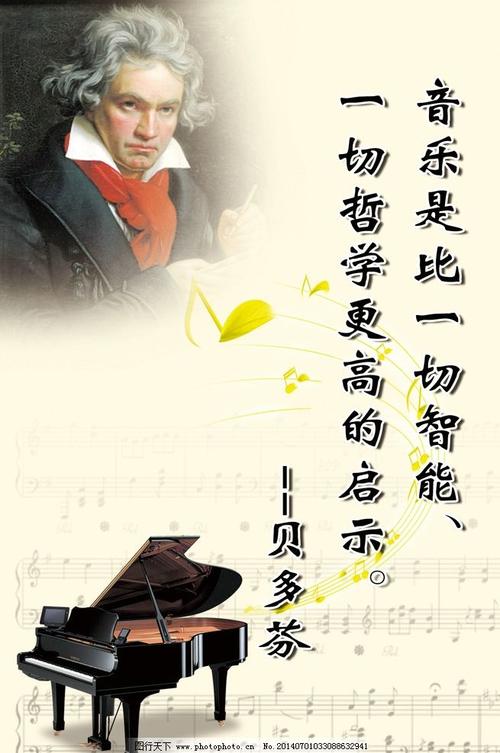
赵益:从⽂献史、书籍史到⽂献⽂化史
吴昌硕:《灯下读书图》
⼆⼗世纪中期以降,西⽅史学界关于⽂献、图书特别是印刷书的社会、⽂化研究——“书籍史”——逐渐兴盛,并成为⼀个专门的领域。近⼆⼗年来,以“书籍史”的⽅法视⾓对中国古代⽂献图书史进⾏研究,也成为海外汉学的热点之⼀。中国本⼟学术界对此⼀直予以密切,并在近⼗年以来渐次展开此⼀新领域的探讨,但相关研究始终不能超越中国学术固有传统的⽂献研究和⼀般意义上的“专史”研究如⽂献史、书史、出版史、印刷史、藏书史的层⾯,“书籍史”的新观念并未得到明确,“⽂献”、“书籍”、“出版”、“印刷”等概念的内涵始终未能得到统⼀,“⽂献史”、“出版史”、“书籍史”、“书籍⽂化”、“出版⽂化”等领域之间的精确的界线⾄今晦涩不明,真正意义上的以社会、⽂化视⾓为主导的“书籍史”研究仍然相对沉寂,与传统⽂献史、图书史、印刷出版史等领域研究的持续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
某种学术状况的存在不⼀定是合理的,但⼀定是具有⾃⾝内在原因的。由此我们必然要思考的是:本⼟学术中这种⾃成系统的⽂献、图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理路”及其强⼤惯性,从⽽使新⽅法、新视⾓的引⼊发⽣某种观念上的歧异和实践中的困惑?或者,中国学术在借鉴西⽅书籍史观照视野的过程中,是否未能充分反思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献、书籍——的客观属性,以⾄于没有提出适合于这种对象属性的新问题?
(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化》,北京⼤学出版社,2009年。
显然,对上述现象及内在原因的认真思考⾸先在于梳理中国⾃有的传统,并由此回到我们的对象本⾝中,去发现其所以区别于他物的⾃性。它将不仅有助于借鉴新的⽅法,加深对既有问题的思考,⽽且能够促使我们开辟真正富有意义的问题领域,最终获得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
⼀、传统⽂献研究的属性与“⽂献史”研究
中国是⽂献昌盛的国度,这缘于其崇尚经验的农业⽂化传统、⽂字和书⾯语的早熟以及载籍技术的不断进步。⽂献是精神成果的书写和物质化集成,所以⽂献发达与中国⽂明的发展延续,⼆位⼀体,不可分割。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意识到⽂献的重要性,始终予以⾼度关注。这种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
⼀是视⽂献为知识、思想、学术的代名词,⽂献的进化历程,即是知识、思想、学术的发展过程;整理⽂献即整理学术,研究⽂献即研究学术。⼆是以⽂献既为思想知识及学术的载体,欲对其内容进⾏研究,⾸先必须对载体本⾝予以考证,以奠定内容研究的学理基础。
第⼀个⽅⾯表现为经典形成以后⼀以贯之的阐释传统。这种阐释在清乾嘉以后尤其⽣发成为⼀种反思视⾓,即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核⼼,如余英时指出的,是“厘清古今的源流,进⽽探⽂史的义例,最后由⽂史以明‘道’。”毫⽆疑问,它属于⼀种逐渐发展完善的中国学术独有的研究⽅法和观照视⾓,具有内在合理性。
第⼆个⽅⾯即清以降所谓⽬录版本校勘之学(今谓⽂献学或校雠学)。尽管不可避免地以⽂献历史描述为基础,同时也必然涉及⽂献的内容,但⽂献学或校雠学在根本上仍属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作。⽬录学之实质,⽆论是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的编⽬实践,还是郑樵、祁承㸁、姚振宗的⽬录条例归纳,总体上约略等同于西⽅近现代学术所形成的historical bibliography、deive bibliography 及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的综合。⽽版本学的核⼼意义是揭⽰版本源流,版本源流的考察建⽴在版本实证的基础之上,客观⽬的仍是为学术研究服务。⽂本校勘则旨在解决⽂献⽂本长期流传以后所产⽣的⽂字讹误,⼒求恢复原始的⽂本,亦属于学术研究的前提性⼯作。
同样,在西⽅学术系统中,⼀般意义上的⽂献研究原本亦属于狭义⽂献学或图书馆学范围,与书志学或⽬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 、⽂本校勘( Textual Criticism)并列。这种⽂献学以历史描述性⽬录、善本鉴定为内容的书志学为基础,旨在为“⽂本校勘”提供实证依据。总之,在中西学术中,⽬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献考证都是各种学术研究特别是⽂学、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西⽂献学具有相当的⼀致性。
⽆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法视⾓还是中西⽂献学⽬录描述、版本谱系和⽂本校勘的基础实证,都是就事论事,并不将⽂献作为⼀种整体观照对象。将古代⽂献本⾝视为客观历史现象⽽加以考察,我们姑且称之为“⽂献史”,与上述两种关注有所不同,属于近现代兴起的新史学研究。
当然,如果推本原始,这种研究在中国渊源亦早。刘向歆⽗⼦主持进⾏的第⼀次⼤规模的校书,不仅意味着对⽂献本⾝研究的⽂献学的发端,也标志着对⽂献发展史整体观照的滥觞。班固《汉书》取《七略》“以备篇籍”,开创出⽂献是历史组成部分的史学观念,也可以说就是⽂献史的真正起步。此后政府及私⼈藏书、校书,往往编有⽬录;隋唐以降的历代正史,均以经籍、艺⽂志纪存⽂献,传统⼀脉相承。
王承略、刘⼼明主编:《⼆⼗五史艺⽂经籍志考补萃编》,清华⼤学出版社,2014年。
另⼀⽅⾯,宋以后学术发展,学者的个案研究特别是清乾嘉时期兴起的主张考镜⽂献以明学术源流的⽂献观照视野,均既重⽂献校雠,亦重⽂献历史。在郑樵《通志》艺⽂、校雠略、胡应麟《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章学诚《⽂史通义》、《校雠通义》等著作中,⽂献总体的发展历程,始终是⽴论的背景。尤其值得⼀提的是章学诚的例⼦:章⽒具体的修史实践,表现在他对地⽅志编纂的体例探讨上,与戴震惟重地理沿⾰不同,⼗分强调对⼀⽅⽂献发展的记录,“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势不两全,⽆宁重⽂献⽽轻沿⾰⽿。”( 章学诚《章⽒遗书》卷⼗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在章学诚看来,⽂献的历史可以取代⾏政沿⾰⽽成为地⽅史的重要内容。此是对历代正史皆重⽂献记录的进⼀步发展,将⽂献史提到了⼀个相当⾼的地位。
尽管如此,古代的⽂献史观念仍然是不⾃觉的。中古以后的“史志⽬录”主要是以档案材料(国家藏书⽬录) 的编集为主要形式,它与各种整理性、考辨性的⽬录在总体上的做法基本相似。辑录体《⽂献通考·经籍考》和⼤⼩序、提要俱全的《四库全书总⽬》集⽬录编纂之⼤成,或“先以四代史志列其⽬,其存于近世⽽可考者,则采诸家书⽬所评,并旁搜史传⽂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 马端临《⽂献通考》⾃序),或“叙作者之爵⾥,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酎今古,辨章学术,⾼挹群⾔”。所以,即使在这些⽬录中存在宏观性的历时总结,很⼤程度上也是以⽂献所承载的内容⽽不是⽂献本⾝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简⽽论之,这种研究或者是⼀
种学术史,或者仍从属于⽂献学。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献史研究应该是从⼆⼗世纪才真正开始。⽂献史并没有专门的名义,⽽常常以“书史”、“图书史”冠称,并以印刷史、出版史为主要内容。每⼀种⽂献专门史研究⼜⽣发出各种分⽀。其中出版史中有偏重于传统⽂献
的“编纂史”,有“藏书(典藏)史”( 包括“图书馆史”) 、“散亡史”等。晚近出⼟⽂献⽇多,以⾄于还有关注于早期简帛图书的各种专论及简史。另外,新史学专门史的出现导致各种分科学术史的产⽣,因此⽂献学也产⽣了⽂献学史,其各个分⽀如⽬录、校勘、版本、辑佚、辨伪之学,均各有史。
在根源上,“⽂献史”是⽂献的重要意义以及重视经验的⽂化传统的延续和扩展。中国学术是⼀种经典阐释之学,⽆论是通过⽂字训诂、史地考证还是⽂献校雠,不外以明古代圣贤之“道”为旨归。中国古典传统不仅范围⼴⼤、历时弥久,⽽且五千年的历史构成⼀个整体,不像西⽅⽂化中的“希腊—罗马”表现出明显的“古典阶段”,⽽它的⼀切都承载于丰厚的⽂献之中。因此,尽管在西学冲击和政治⼲预下遭受了某种损害,但对⽂献本⾝的重视⼀直是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
就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变的客观过程⽽⾔,“⽂献史”⼜是⼆⼗世纪新史学所主张的各种专门史的开拓结果。中西史学本来传统迥异,但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史学却⾸当其冲,整个⼆⼗世纪基本上以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为主流,⽽这种史学观念的主要倾向之⼀就是对专门史的强调。
这种⽂献史如果采取⼴义的范围和宏观的视野,当然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社会与⽂化的内容。以当代学者所倡导的“出版史”为例:
其研究领域既有专业系统性,⼜有综合系统性。其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两个⽅⾯:其⼀是历史出版活动内部诸⽅⾯的联系;其⼆是出版事业与⼈类社会政治、经济、⽂化及科学技术等⽅⾯的相互联系。具体地说,研究并叙述出版事业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记述历史上有重⼤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在⽂化创造、⽂化积累、⽂化传播⽅⾯的业绩,记述各类型重要典籍编纂出版的过程,揭⽰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化形成中所起的作⽤,从⽽揭⽰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因此举凡⽂字的产⽣、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典藏保护、流通利⽤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都是出版史的研究内容。(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前⾔)
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表⾯看来,这种研究具有将出版史、图书史的研究“与⼈类社会政治、经济、⽂化及科学技术等⽅⾯相互
联系”的初衷,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字的产⽣、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抄写印刷、贸易发⾏、流通利⽤等,以及主要研究⽅法如经济考察与计量统计等,亦和当初开辟“书籍史”的年鉴史学取径有相同之处。但就实际情况看,此⼀⽂献史研究仅仅关注⽂献或图书的外在发展和物质形态演进的历程,它仍导源于近代史学的“专门史”扩展,⽽⾮形成于当代⽂化史观念的变⾰。“专门史”的内在要求是尽量集中于各种历史事相的专门化描述,⽽不是进⾏意义的阐发,因此当它越来越集中于专题性的历史描述时,局限性就必然凸显出来。这种天⽣缺陷使此类研究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视野。
与此类似,西⽅传统⽂献史或书史的主导倾向同样是关于⽂献或书籍的“物质性”的历史描述,如书籍的制作⽣成,载体的历史进程,版本和异⽂状况等等。尽管在传统⽂献史研究中也早已出现了关注“书”作为⽂化符号的历史亦即书的内容意义、传播、接受与评价、历史地位等等的倾向,但在主观上仍然是不⾃觉的,并在很⼤程度上仅仅是作为⽂献历史描述的补充⽽存在的。
对⽂献特别是更加社会化的“书籍”予以更⾼层⾯的⽂化审视,是⽂化⼈类学所带来的“⽂化转向”思潮的⼤背景下,年鉴史学特别是⼆⼗世纪⼋⼗年代以降“新⽂化史”兴起,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史学观念进步变⾰以后的结果。⽏庸讳⾔,尽管进化论⼈类学很早就传⼊中国并得到⼴泛的响应⽽导致“⽂化”思潮的出现,但由于本⼟语境的作⽤和政治的影响,整个⼆⼗世纪后半叶中国并未与西⽅实现同步的转向。⽽近⼏⼗年来,史学观念虽然已有重⼤突破,但以线性时间为原则、以原始史料的科学实证分析为根本⼿段、重在进⾏
历史描述、填补历史空⽩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强⼤的存在的合理性,并未以史学的⼈类学转向(或“⽂化转向”)和后现代发展⽽消减。更重要的是,由于“⽂献校雠之学”作为中国学术的内在⽅法,与中国史学传统和科学主义史学观甚相契合,因⽽具有强⼤的⼒量,促使⽂献史及其种种专门史始终保持⼀贯的趋势。
⼆、“书籍史”的核⼼意义与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
近代西⽅新史学诞⽣以来,特别是年鉴史学提倡社会、⽂化观照视野以后,开始出现以“社会”、“经济”、“⽂化”取代传统历史编纂学叙事关注的倾向。“新⽂化史”兴起后,各种⽂化现象诸如政治、知识思想、语⾔、性别、科学技术、物质、⽇常⽣活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献”特别是印刷书籍更加成为⼀项重要的反思对象。书籍史研究的开创著作公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 及马丁(Henri-Jean Martin) 所著《印刷书的诞⽣》(1958年出版) ,其研究的核⼼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书籍印刷史本⾝,⽽是从宏观的⾓度试图解答印刷术的发明对整个欧洲历史究竟造成什么影响这⼀意义深远的问题。
《印刷书的诞⽣》开辟了此后各种书籍史如印刷品使⽤史、出版⽂化史、阅读实践史、写作⽂化史之先河。此后各种研究不断从多⽅⾯进⾏拓展,如唐·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 率先从⽂本社会学的⾓度探讨书籍“形式”的社会意义,伊丽莎⽩·爱森斯坦(Elizabeth Einstein) 明确指出印刷在欧洲近代
史上的重要性。⼆⼗世纪中期以后,⼴义历史研究的“⽂化转向”进⼀步明显,诸如图书阅读史、图书接受传播史、图书商品贸易史特别是图书对社会⽂化影响的研究成为⼀种重要的学术思潮,代表作如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a ) ,以⼗⼋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出版过程及流通的⾓度,探讨了图书出版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历史。
罗伯特·达恩顿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书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将书籍的传播过程,视为理解思想、社会以及历史的最佳途径及策略。罗伯特·达恩顿认为,由法国历史学家开创的“书籍史”不同于图书馆学、⽬录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是⼀种典型的⽂化史观照。最近⼏⼗年,西⽅“书籍史”研究发展很快,在理论、⽅法及实践等各个⽅⾯都有很多新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