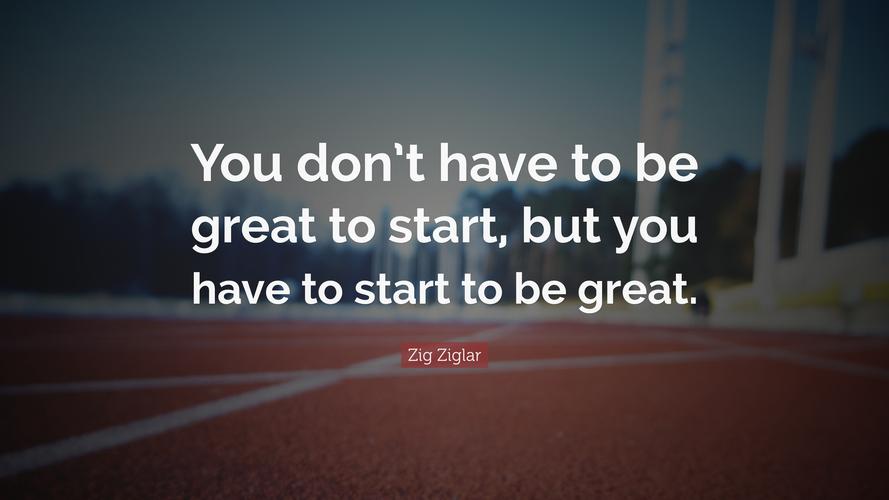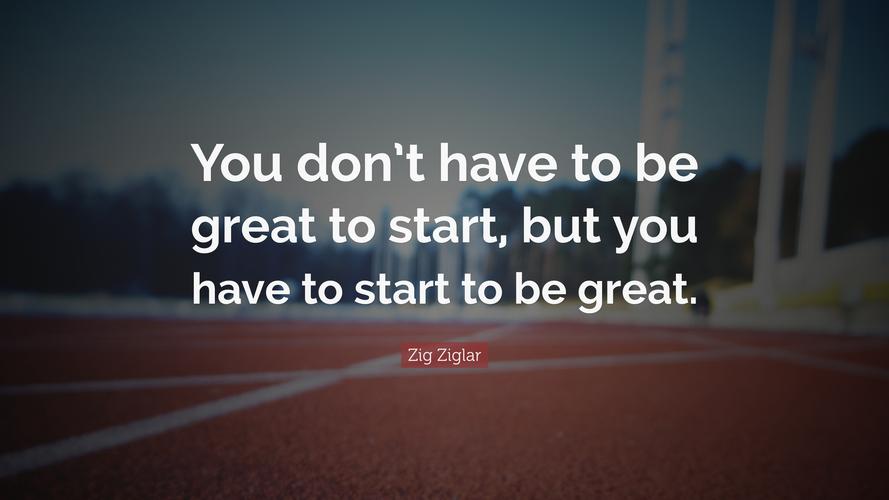
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手法
———《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新读解
周琦玥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纪昀站在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上讥讽《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然而随着时代推移,此语多被后人借以概括《聊斋志异》兼熔两重文体的写作特色。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可以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将史传文学色彩与非虚构叙事手法整合为一。通过对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蒲翁在叙事策略、叙事时间线、叙事视角以及相关的论赞品评等方面颇有史家风范。具体来说,蒲氏善于利用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事件,融入作家的文学想象,既以事为本、于史有征,又由正而奇、由文而幻。从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特点出发阅读《聊斋志异》,可以对“一书而兼二体”之说阐发新见。
关键词: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史传文学;非虚构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人言人异。自唐朝起便有学者认为小说缘起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
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1]935嗣后,刘知几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并指出“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
别,殊途并骛……”[2]253胡应麟同样认为某些小说“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
收稿日期:2020-09-15
作者简介:周琦玥(1997-),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文献研究。
·《聊斋志异》研究·
文章编号:1002⁃3712(2020)04⁃0046⁃14
志传者”。小说缘起史传之说虽然存在着因材料缺乏而难以确证其完全真实性的问题,但纵观中国古代
小说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带有很强的史传文学特色,特别是早期小说的“志人”“志怪”内容更是如此。随着文学自觉的增强与作者对创作技法的追求,加之文学创作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日臻完善,其史传文学色彩逐步淡去。但后世仍有部分作品自觉赓续了这样的特色,《聊斋志异》便是如此。蒲松龄充分借鉴和继承史传文学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融入诸多文学想象的成分,恰如孙锡嘏所言:“文理从《左》《国》《史》《汉》《庄》《列》《荀》《扬》得来。而窥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瘅恶,期有功于名教而正,并非抱不羁之才,而第以鬼狐仙怪,自抒其悲愤已也。”[3]602除却文理上对前代史传作品的效仿,蒲松龄以“异史氏”自称,对文中所涉人物、事件的品评,与司马迁以“太史公曰”形式的论赞也颇为相类。这样的处理方式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评论传统,在体例上因袭史书风格,正所谓“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3]587蒲松龄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招致了一定的非议,其文体上的杂糅性特质更是为纪昀所诟病,《阅微草堂笔记》对《聊斋志异》评论便涉及到对“一书而兼二体”特色的暗讽: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
《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
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4]408
纪昀的批评乃是从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与视角所发,所谓“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的深层含义,乃是严格区分以“志怪搜异”为要旨的“小说”和以“述往事,追来者”为旨归的“传记”。具体考论其批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聊斋志异》文体不纯,其中不仅有类似于《搜神记》的简略叙述,也有篇幅较长类似于古代传奇故事。所以《聊斋志异》既是“笔记体”,又是“传奇体”,进而导致“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的内部矛盾。纪昀此说应和者颇尠,“一书而兼二体”之语虽为后人广为
引用,但此言原本所带有的暗讽意味渐已减弱,变为单纯的叙述文辞。
前人对《聊斋志异》叙述特色的考察,多集中于蒲松龄创作过程中对史传文学手法的继承,以及该书“笔记体”与“传奇体”二者得兼的艺术特色。然而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我们发现,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收录的众多作品体例不尽相同,既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融入文学想象所撰成的带有史传文学特点的作品,又有切近历史真实、以白描手法详尽记载虽看似奇诡但却实有其事的非虚构写作。选取相关篇目予以厘析,可以廓清《聊斋志异》中两类不同创作倾向下创造的叙事成果,
进而为“一书兼二体”的成说提供新读解,也为《聊斋志异》叙事学特色的多样阐释提供新的可能。
二、既有史实,杂以想象:《聊斋志异》部分篇目的史传文学特色
极尽推崇史学叙事,将其提升到“六经皆史”高度的章实斋,以“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之语为历史著作叙事方法对古文辞之术的影响作了绝佳注脚。[5]767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绝不裹足于提供创作所需的人物、情节、环境等素材,更因其记叙层面的成熟为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此外,史传虽是叙述历史事实的“写远”之作,但并不排斥“追虚”,也即合理想象的熔铸。刘勰曾指出“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6]151,“伟其事”“详其迹”的重要材料来源,便是民间传说、作者想象等与“秉笔直书”“董狐之笔”不同的文学想象成分。恰如钱钟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庶几入情合理。”[7]272-273柯林武德对史家的这种有意为之评论道:“正是这种活动(有意虚构)沟通了我们的权威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8]1133除却补上历史著述中受制于材料欠缺而形成的阙环之外,这种以史为据,但又杂有文学趣味和入情合理想象的创作范式,也使得史传文学作为特殊文体具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为尘封既久的“青史”带上了一抹文学的色彩与温度。这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作者往往以“稗官野史”自称,即使是以“花样全翻旧稗官”作为自我标榜的著作,仍是在“旧稗官”基础上的“新翻”。因此“野史”的“史”内涵,是小说作家无法规避,也不可能彻底割裂的文化资源,更不乏自觉将史
书特色与文学意趣融为一炉的小说出现。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中深受前代史籍影响,将“史官式”技巧与创作实践相融合。蒲松龄选择部分与真实存在的事件与人物有关的材料作为创
作蓝本,而在进行叙述时融入虚构笔法进行类似于史传文学的“虚实相生”叙事,继承了史传的虚构艺术,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尚奇”叙事风格,于“狐鬼花妖”之作中“钩爪锯牙,自成锋颖”,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新高度。恰如蒲立德称《聊斋志异》一书:“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状,而无所遁隐。”[3]578
(一)线性叙事时间与全知叙事视角
“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如果不顾及它与史传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深得中国小说的壺奥。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传统。”[9]67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源头的史传文学,在文笔技巧上对后世小说家创作的影响自不待言,模仿《史记》《国语》等文法笔法特色从事小说创作者甚夥。在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方面中,史传文学的叙事方式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也最为深远,这与史传作品在叙事性上达
到的高度密不可分,“史传乃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真正渊薮,中国古代的叙事艺术最集中地表现于古史之中”。[10]33具体到《聊斋志异》论,其中叙事时间序列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便明显带有继承史传作品的特点,对史传作品“深明体裁作法者”阅读到相关篇目时,自会“方知其妙”,可见清人便已以曲笔点明《聊斋志异》与前代史传作品的深层次关联。
史书的创作目的在于“写远追虚”,因此最常见的叙事时间序列是按照时间发展忠实记录历史事件的线性顺序,正所谓“叙事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线上”。[11]506《聊斋志异》的诸多篇目中,以线性时间链条作为叙事依傍者为其大端。虽然以时间先后串联事件发生关键节点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不乏先例,但多为长篇世情小说所用,且往往掺杂有多条并行不悖甚至相互龃龉的时间线,如《金瓶梅》的“多事并举”、《红楼梦》的“时序倒流”等。但《聊斋志异》的叙事特点却与此不同,极尽谨严。蒲松龄十分重视叙述故事的始末由来,相当篇目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的叙述严格按照时间推移顺序,展现出完整、详尽的线性时间链移。这种以时为序的写作方法与正史中的列传,以及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作方式颇为相
类,有如史家著述,可谓是《聊斋志异》受到史传文学影响的外在表现之一。
《祝翁》开篇简练点出祝翁姓氏、里籍和年岁,五十有余便已离世,进而说明其“死而复生”的原因:“
我适去,拚不复返。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故复归,欲偕尔同行也。”[员2]86将此篇立意托出,祝翁心系妻子不忍其独身过活,然而此举却得到“媪笑不去”“媳女皆匿笑”“家人又共笑之”的反应,衬托此事的荒唐。而后老媪携手祝翁离世,这也是作者叙述最为详尽之处:“媪笑容忽敛,又渐而两眸俱合,久之无声,俨如睡去。众始近视,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在数句之中运用大量诸如“忽”“渐而”“久之”“始”“已”等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文中其他地方还曾使用“又促之”“俄视”等字眼串联情节,使得全文顺序了然,最后又以“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之句作结,既增加了该事件的真实性,又为这一故事提供了长时间段上的节点作为参照。这样的叙事方式以时间线串联起故事的因果逻辑,整体结构明晰,而在重点观照的主要事件发展与结果之处更是条理井然、援事随时,与史书的记事方法高度一致。
除却时间视角选择上深受史传文学影响外,《聊斋志异》的叙事角度选择也颇可玩味。石昌渝先生指出,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叙事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9]69-72实际上采用全知叙事视角乃是各民族历史叙事作品的共性特征,各类英雄史诗的叙述模式也往往采用这样的方法。这与历史叙事本身对清晰勾勒历史事件、使读者或听者身临其境的要求,以及作为讲述者的叙事主体采用较为客观的叙事立场、游离于事件之外、在叙述过程中尽可能较少干预事件发展的超然地位密切相关。《聊斋志异》在讲述客观事件时也是如此,作为作者的蒲松龄采用全知角度,从全知视角出发对各类事件予以叙述。如《聊斋志异》中的各类狐鬼花妖,在
叙述的开篇便已经明确点出其异于人类的特点,甚至在题目中便明确称其为“画皮”“庙鬼”“鬼令”,或称其事为“狐嫁女”“狐入瓶”,可以说除了文章主人公不知道自己乃是与鬼怪打交道外,讲述者和读者均已心知肚明。而在叙述不带有灵异色彩的故事时,蒲松龄同样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如《黄将军》一篇中,仅用不足百字之文叙述黄将军之勇猛:“黄怒甚,手无寸乒,即以两手握骡足,举而投之。贼不及防,马倒人堕。黄拳之臂断,搜索而归。”对黄将军的描写仿佛置身于战场上空,以俯视的角度冷眼旁观、如实记录古战场的场景。又如《佟客》中开篇即讲董生“好击剑,每慷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