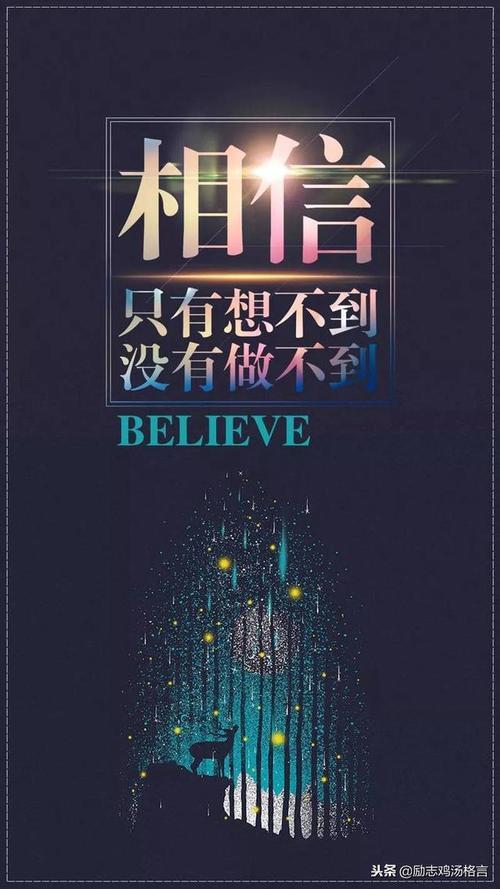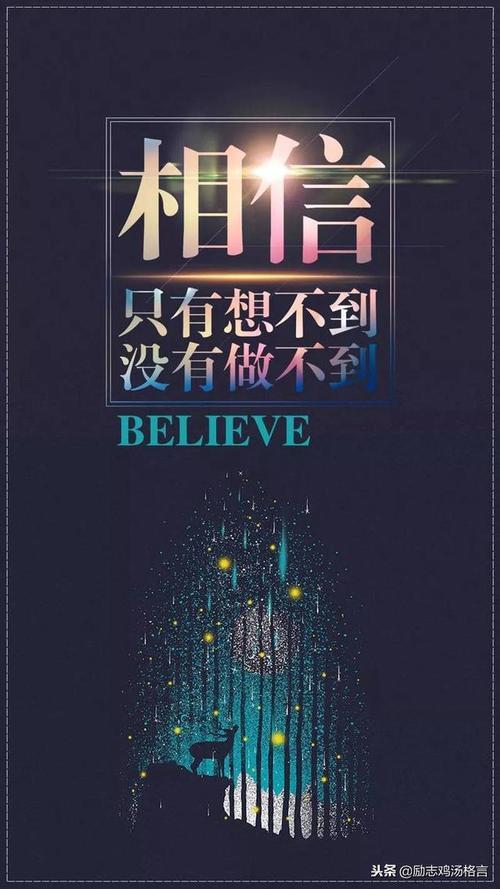
青年诗⼈、⽂艺理论家章闻哲答诸暨⽇报问
诸暨⽇报.⽂化周刊.访谈“探寻艺术在⼈类发展史中扮演的⾓⾊”
——诸暨籍青年诗⼈、⽂论家章闻哲访谈录
Q:社会主义美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美学的?
A:这个时间应该始于2012年,也就是我在写《散⽂诗社会》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然切⼊到这个主题⾥。当时我的前辈兼诗兄——⼈民⼤学哲学系教授林美茂,提出让我来写⼀本散⽂诗⽅⾯的理论,他之所以让我来写,我想有三个理由:⼀、我写散⽂诗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创作上颇有新锐之⽓,同时我在诗歌理论上所持的见解也⼤多为他以及我们周围的师、友所认同;⼆、正是由于这种认同,他和“我们”散⽂诗群主要发起⼈周庆荣,⼀致觉得让我来阐发“我们”散⽂诗群的创作理念以及散⽂诗这⼀⽂体的意义会⽐较可靠。三、我相对来说⽐他们更有时间,同时我⼜是刚进⼊这个⽂体的写作不久,还有⼀个⽐较客观的距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散⽂诗这⼀⽂体内部的争端与发展根源,乃⾄局限。我很庆幸⾃⼰可以在⼀个外⼒的推动下去从事这个研究,在研究散⽂诗的过程⾥,我发现了这⼀⽂体的最早起源其实是⼀种过渡社会⾥由于社会的复杂性⽽产⽣的、符合社会⼼理表达需求的⼀种综合性⽂体。这种综合性,简⽽⾔之,它正是“现代性”的⼀种体现——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个“现代”,因此“现代性”源远流长,同时⼜必然是时代之最新的属性。就这种“最新”来说,我们有必要讨论⼀下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的社会与时代,是否也是这种“最新”的表现,也
就是说,是否“⾜够现代”.——这样,我便进⼊了⼀个社会主义美学的议题⾥。我⾸先探讨的当然是诗歌领域的⼀个重要的历史性表达——政治抒情诗。这⼀类型的诗歌,它的⼀种显著的特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命传统及其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简⾔之,⼀般的理解⾥,政治抒情诗是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或者它是带有⽆产阶级⾰命情感的。其⽂学性在改开以来⼀向颇受争议。我作为⼀个有志于诗歌或⽂学批评的写作者,讨论这个问题是我的本务。然⽽,我所讨论的,当然不仅仅是要把社会主义美学与政治抒情单独地对应起来。社会主义美学有其更⼴阔的含义。
Q:您接触社会主义美学的契机是什么?
A:这个答案已然在第⼀个问题的回答中。但我可以再补充⼀点,那就是与贺敬之前辈的友谊可能也是促使我关注这个议题的关键因⼦。众所周知,贺⽼是⼀位政治抒情诗⼈,他创作的⽬的或动机都与⽆产阶级⾰命⽂学的历史宗旨⼀致。如果要谈论他的作品,我们必须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由⽆产阶级⾰命中诞⽣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在⼀种⼈民的⽴场上被创建时所呈现的基本的审美情趣与德性,乃⾄价值和意义所在。假如有⼀种否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审美态度,那么我们既然已⾝处此种社会,我们就越发有必要检查⼀下我们⾃⾝在此位置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从审美本⾝来展开论证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避免在⼀种上层建筑的主观命令中来决定我们对社会的种种价值评判。
Q:作为⼀名青年诗⼈,您是怎么想到研究社会主义美学这样⼀个看起来⽐较严肃的课题?
A:你提的问题有点像俄罗斯套娃,你会发现,你提的每个问题其实都可在上⼀个问题的回答⾥找到答案。不过,⽆⼀例外,尽管在上⼀个回答中已然有了这⾥的答案,我还是要再⾏补充,在当前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有⼀个更正统的回答:也许当下许多⼈对社会主义本⾝的可审美程度有些错误的理解,换⾔之,就像吴帆,你作为⼀名90后,⼤脑⾥可能根本没有打算对“社会主义”这类术语产⽣兴趣。因为你是在⼀个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长⼤的。这个环境它叫“特⾊社会主义”——但你们可能只想领略开放的氛围,领略全球化语境⾥相同的⽂化⽓候,⽽对地⽅、民族那些狭隘的概念与界限表⽰拒斥。然⽽,我们得有⼀个更客观的理解与态度,在⼀种制度下的社会种种是有其实际的界域的,它不会完全雷同于经济流通中的貌似⽆界的场域。我们得有我们的⾃信,确⽴我们所认为的价值坐标。这就是我作为⼀名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要阐述社会主义美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说到这⾥,我们不妨重复⼀下总书记的观点:要有制度⾃信。⾃信从何⽽来,从审美中来。这种审美不是简单地评价⼀下你这个服装、姿态造型美不美,⽽是在与历史社会的⽐较⾥,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检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究竟有何优越性,究竟有没有可能让⼈类⾛向更光明的前景。⼈类最美的风景在于福祉本⾝,我们的美学的根源也在这个对于福祉的追求⾥。
Q研究社会主义美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A:根据上述,它的主要意义也就在于从诸历史社会的审美观照⾥,揭⽰社会主义本⾝对于⼈类造福⾃⾝的科学性可能。因此它不仅是美学,⽽且是社会学与⼈类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美学的研究中,
看到⼀些社会主义社会本⾝的不⾜,或者说看到⽭盾。现代社会最⼤的理性在于正视问题,正视⽭盾,然后解决。因此这种美学研究并不回避社会问题,相反,它须把它当作基本任务。
在你提到这个问题时,我怀疑你再次把社会主义美学理解为⼀种社会主义创建初期带有诸类历史遗留问题时的那种单纯的⽂化改⾰运动中所揭⽰的美学。或者说你把它理解为⼀种单纯的公有制社会所曾经呈现过的带有激进倾向的历史审美形态。我要重申的是:我们所处的当下就是社会主义,或者特⾊社会主义,我们的⼀切⾏为和思想,都与这个制度下的社会运营有关,因此,你我都不能脱离这个名号——社会主义,来谈论我们的本质。就社会整体⽽论,认识我们⾃⾝当下的存在本质,我们才能进⼀步确认我们要⾛向的未来。对个⼈⽽⾔,研究这个美学不是要对每个⼈构成⼀种⼈⽣向
下的存在本质,我们才能进⼀步确认我们要⾛向的未来。对个⼈⽽⾔,研究这个美学不是要对每个⼈构成⼀种⼈⽣向导,⽽是⾄少让⼈们清晰他⾃⾝是⼀种怎样的存在——如果在世界化趋势⾥,我们的存在是先进的;那么这种先进正是特⾊社会主义本⾝的先进。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就⾃觉⼟鳖——我们须从制度的审美⾥——确切地说是在制度框架下的⽂化与⽂明的现代表述⽅式的审美⾥,重新确⽴我们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存在美学。
Q:贺敬之是⼀位伟⼤的诗⼈和剧作家,我们都读过他的《回延安》,看过他的《⽩⽑⼥》您在和贺敬之、峭岩等⼈的接触中,有什么启⽰和思考?
A:我对贺⽼的印象⼤致可概括为: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性格爽朗,豪迈,⼀看就是光明磊落之⼈,很有⾰命家之风采。⼜较平易近⼈,对后辈不吝关怀。他周围有许多诗⼈,可以称为左翼,但贺⽼本⾝作为曾经的⽂化部长,他的⽴场实际上不能论左右,⽽更以国家⽅针政策为马⾸是瞻,在他的⽂章或理论中是不能够见到⽚⾯之词的。就峭岩⽼师来说,他是⼀位军旅诗⼈,创作颇丰,可谓著作等⾝。他⾝上兼有军⼈之豪迈、帅爽及诗⼈之丰沛、细腻的情感。故其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两种品性。纯粹的集体主义政治抒情与个私化的抒情诗,他都驾驭得很好,是位在诗创作中充分把⼀种社会责任与个⼈⽣命情感乃⾄职业道义使命的表达视为同等重要、并以此为修⾝齐家之道途的典型诗⽂家。
Q:您在和研究对象交流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A:交流的困难吗?我想说这种困难是被我以⼀定⽅式回避的。实事求是地讲,我缺乏与⼈交流的技巧与耐⼼,但是,这个不⾜并不威胁到我的研究。因为⼀般的交谈,接触,以及作为旁观者仅仅站在⼀边观察,从中收集相关信息或数据,这种操作⽅式,恰恰正是作为研究的⼀般途径。这很可⽐作中医的望闻问切,在中医的四个诊断法⾥,问,排到第三位;切,作为触摸法,排到最后。这说明,研究诊断⼀种情况,主要的⽅法还在于望与闻。问,只是为了进⼀步确诊——但是,⽂艺批评不是精确科学,它实际上反⽽需要“不确定”来更宽⼴地赋予⽂本意义。我的研究维度主要在作品上,我不会通过作者去确认⼀种判断,使得意义单⼀化,这对⽂艺作品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对优缺点的评价并不是基于⼀种流⾏很久的单纯的⽂本或语⾔学上的判断,⽽通常会从其时代、历史的渊源与背景中来分析其产⽣的条件与
社会功能。这同样是为了避免⽂学作品本⾝被简化、单纯化。然⽽,这⾥亦有⼀种辩证法:我相信我作为⼀位评论者⾄少是把“充分理解并且努⼒客观”视为评论⾸要原则的⼀个⼈。这实际上就是说——我在对作品更周详的评价中实现了与作者本⾝的沟通。
Q:您接下来在社会主义美学⽅⾯还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A:这是⼀个系列,会陆续地随着有所发现,⽽有所⽣产。我要介⼊的不仅仅是诗歌,还有绘画、舞蹈、电影等。不过也有可能暂停,去从事其他创作。
Q:您是什么时候离开诸暨的?并选择在北京发展?
A:对诸暨,实际的情形是不能描述为“我曾经离开”——在我的个⼈感觉中,成为⼀个异乡⼈或移民的那种实质才可称得上“离开诸暨”。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有些⼈早上在中国,中午在法国,晚上⼜回到了中国——实际速度也许还要稍微慢⼀点,但差不多是这样,这是交通的趋势。它意味着我们的活动空间并没有把⼀个故乡或哪个地⽅隔离到⼀个可称之为“离开”的地⽅。我认为你提的这⼀点是在⼀个传统的地理交通体系⾥才可能。就像从前,⼀个⼩说家的叙述⾥通常会有“离乡背井”这种迁移逻辑。
我们会有多种理由离开——但都不是长久的。也许我不喜欢在⼀个地⽅呆许久,因为会感到束缚,长期在⼀个地⽅呆着相当于长期服从⼀种秩序。我必须寻找新的场所,在新的秩序⾥发现我们⾃⾝的新的可能。
去北京是因为我的诗友很多都是北漂。很久以前,当我第⼀次冲进腾迅诗歌论坛时,我认识的第⼀批诗⼈,就有⼀部分在北京,有的则在福建。选择北京,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的现任伴侣是⼀位⽼北漂。
Q:就像我们经常写的那样,⽂学是您从⼩的梦想吗?
A:“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记得有⼀次放寒假,我⽗亲让我就⼀次家庭合影事件写⼀篇作⽂,我很苦恼这种⽆聊的⼩事居然要诉诸作⽂。可见,那时之⼩,尚未有⽂学之好。但我在⼩学阶段,确实看了⼀些书,包括《天⽅夜谭》《聊斋》《红楼梦》(连环画本),以及像《许茂和他的⼥⼉们》这类⼩⼈书。我⼩时候接触的书⾥,童话是最少的。我外公那时订了画报,上⾯亦常常有⼩说改编的故事,⼈物、风物、⽂字,凡此种种,也许不⽆建⽴了⼀个我⼩时候的⼀种启蒙建筑。其实我想说,每个⼩孩都会喜欢⽂学,因为⽂学叙述的⽬的就是要引⼈⼊胜。区别仅仅在于接触不接触,接触什么,你被什么吸引,以及理解⽅式与理解能⼒的不同。
Q: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A:看理论书。⽂史哲,历史与哲学⽅⾯居多。⽂学只是作为⼀个必须了解的对象去阅读。也许你会觉得我⽐较功利,不过——我的乐趣还真是在抽象阅读⽅⾯。如果有⼈告诉我谁谁写得⼩说⾮常好看,我⼀定不会去看;但是如果有⼈告
不过——我的乐趣还真是在抽象阅读⽅⾯。如果有⼈告诉我谁谁写得⼩说⾮常好看,我⼀定不会去看;但是如果有⼈告诉我,谁谁写得⼩说写得像蒙⽥的随笔,或者像卢梭的《⼀个孤独漫步者的暇想》等,或者像《⽡尔澄湖》,那我可能要去看,因为这样的⼩说或叙事已然接近哲学。但是⼀般来说重复的还不如原来的——我们当代⼈,不能被随随便便的故事抓去坐两个钟头。这样说当然,太过⾃命不凡,其实我现在也只是在絮叨,也企图浪费别⼈的时间。
Q:您是有灵感了才进⾏创作的,还是给⾃⼰规定任务进⾏创作的?
A:就诗歌来说,初期创作肯定源于灵感;⽽以后灵感将不再是唯⼀的途径。只是没有灵感,诗⼈之诗必然不堪⼀读,不能称诗。⽽在评论或理论性的写作,看上去不能依赖灵感,但实际上,你的陈述或者论述,调遣所有的词汇来完成或认证⼀种东西时,确实,依然需要灵感的在场。否则就是迟钝。我的写作有两个⽇常动⼒:⼀是受托写评;⼆是发现新命题,必须上升⾄理论,以正观瞻。⼤的计划也在这种动⼒的⽀配中。
⼈到中年,作为⼀名写作者,思考得东西会⽐较多,甚⾄⽐较神经质,这种状态下,灵感可能是⼀个常态,因为太多,可能在⼀个⽂本⾥已然不能显出是⼀种灵感的产物。就像⼀朵⿊玫瑰在⼀⽚红玫瑰中是奇特的,⽽在⼀⽚⿊玫瑰⾥却是平凡的。
Q:您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A:⽐较得意的著作也许是⼀部尚待筹资出版的百万余字艺术哲学类撰述:《梦、艺术、⼈本主义》。我在撰写它时,颇认为我在⼀种最彻底、最明晰的⾓度上阐明了艺术规律——较之以往的艺术哲学更透彻——它之所以透彻,是因为它不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去谈论艺术,⽽是从历史、社会、⼈类的发展⾓度去谈论艺术,这样艺术的阐述便与社会、⾃然的宏观发展结构发⽣蝉联,可以更本质地看清艺术乃⾄⼈类活动之存在维度。不⾔⽽喻,我的这本书依然带有⼈类学与社会学的痕迹。艺术的谈论看上去更像⼀种揭⽰后者的载体。我在这部著述⾥也探讨了“梦的原理”——这个主题源⾃⼀种反弗洛伊德的意见。我从个⼈经验与⼼理学界及精神分析学迄今为⽌的成就出发,试图对经典的弗洛伊德释梦⼼理公式进⾏⼆次推论,从⽽寻求以新的学说来替代弗洛伊德学说。也许你会奇怪,这个论述与⽂学乃⾄美学关系不⼤,与艺术也不存有直接的⼲系,那么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放到与艺术、⼈本主义相提并论的位置上呢?——因为所探讨的都是关于⼈类及其社会发展的⼀些根本的动⼒引擎的构成机制。⾥⾯的问题都是现代科学尚未对其做出充分解释的领域。但我不是科学家,从科学的⾓度解释这种问题不是我的任务;所以,我只是从艺术的⾓度,去探讨这个问题;谈论艺术者⼗分普遍,但是把艺术作为⼀个⼈类及其社会的本体论的逻辑推导载体,⽽且⼜在⼀种“如果不是从艺术的⾓度就⽆法揭⽰这类现象的根源”之逻辑上说明⾓度⾃⾝与纯粹的科学与科学哲学之探索⽅式的不同⼜殊途同归,即使不是前⽆古⼈,也必然为数不多。它是⼀个发现的过程,起源于我对艺术之癖好,终结于我对艺术在⼈类发展史上扮演的根本⾓⾊与启动机制的发现。这本书初稿完成于2014年,今年⼜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个⼗万多字的序⾔。
Q:您第⼀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如何?
A:第⼀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2006年吧,诗歌作品,发在了河北省刊《诗选刊》。还是倍受争议的梨花体诗⼈赵丽华先⽣编选刊发的。⼼情不如何,因为赵编刊发别⼈的诗作远⽐我多。但是⽼实说,当有⼈
⾼兴地通知我什么刊物录⽤了我的作品时,我对刊物的认识也是⽐较模糊的。我那时更喜欢论坛上的交流与⾃由发表。你知道吗,初写就倍受关注。所以论坛满⾜了我的表现欲。只是后来才从他⼈的态度⾥发现,发表在刊物上才是件⽐较了不起的事。曾经有编辑在编选我的诗歌时要求我取⼀个特别的笔名,说是万⼀成名了呢——他说这话虽然近似玩笑,但确实,在诗歌界,⼤家都有这么个认知,就是在⼤刊上发⼀作品,⽴马全国闻名。这也许是传说。就像我⼀直怀疑⾃⼰已成显家,但是总是有⼈更怀疑。
Q:您在⽂学创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对⼥性作家有什么看法吗?
A:创作中的印象深刻事件?也谈不上特别印象深刻。不过我对⼀种现象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对于⼀个写作者来说,当她很快写完了⼀本书,⽽有的⼈却在⼤势宣传某位专家花数⼗年功夫呕⼼沥⾎完成了⼀部煌煌巨著——这让我觉得好像有⼈在批评我写得太草率,太不严肃,于是乎仿佛可在学术质量上充分质疑我所撰述的东西等。其次,是作为⼥性,⼈们会觉得她的⽂字应该表现出⼥性的魅⼒——这是⼀种可辨性别的⽂字,带有母性、柔软的、包容的,甚⾄胭脂的味道等等。这真是令⼈⽆可奈何的事。如果我这样写,⼈们势必觉得“这是⼥性作者写的”。这种判断⾥本质上含有对⼥性视野与格局的某种轻视。当然,也不是说,⼥性特征的陈述就没有⼒量,就不能有深度——这当然也是⼀种谬解。我没有在⼥性的位置上想要⾃贬⼥性,但是如果有⼈因此质疑我的作品,那我是很不⾼兴的。
Q:在您⼼⽬中,诸暨是什么模样的?
A:如果我有⼀个⾼⾳喇叭,我会把诸暨的⼏⼤特⾊经济板块经常性地对外⼴播:枫桥衬衫、⼤唐袜业、
店⼝五⾦、⼭下湖珍珠、直埠鞋业、阮市炒货,乃⾄我们的农庄,我们的园林。这些板块经营的规模程度都算得上全国的佼佼者——在我看来,这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诸暨。如果我们⽂学⼀点,那我们就要像詹姆斯叙述法国印象⼀样,诸暨是什么?是西施的故乡,是草籽炒年糕,是马剑发糕,团圆果,清明饺。如果我回到故乡,没有西施,没有这些⼩吃,我就会抱怨我的故乡已然⼈是物⾮,或者相反。
我的故乡已然⼈是物⾮,或者相反。
Q:谢谢您接受采访。欢迎您常回故乡看看!A:那是⼀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