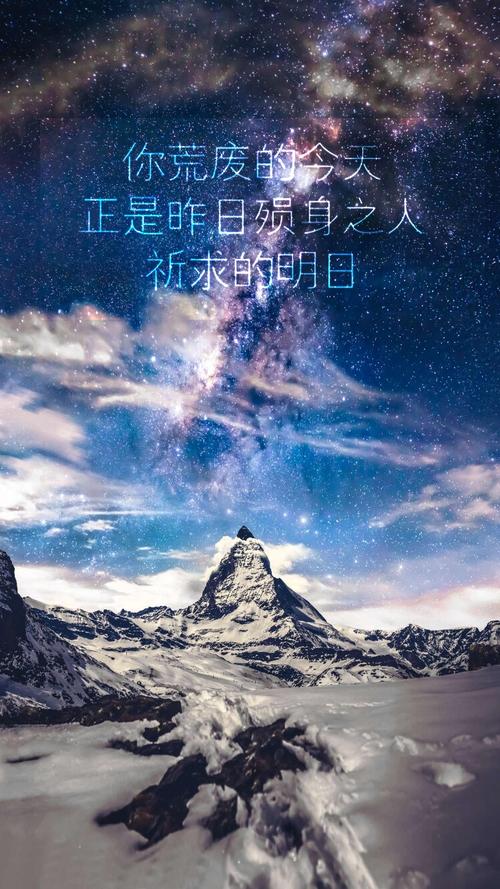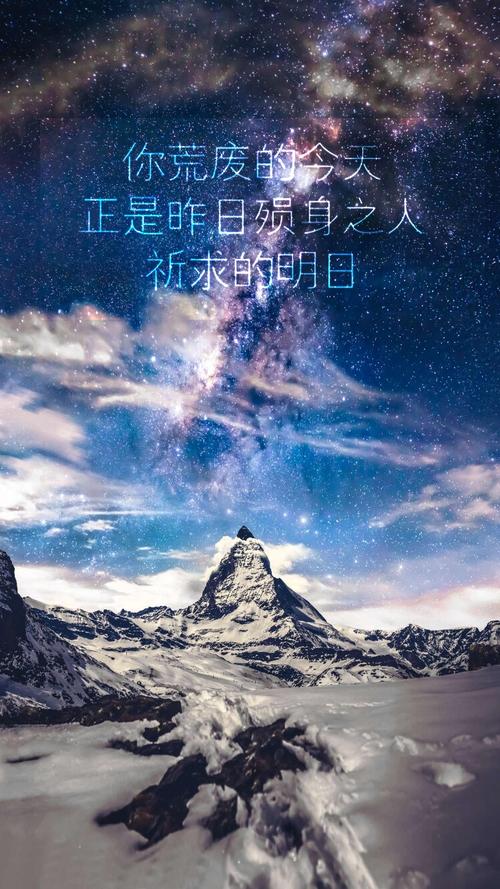
第19卷第4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l.19 No.4 2013 年 8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Aug. 2013 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曹莉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5;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知物哀”论是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在幕府封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 “知物哀”论是作为以儒佛为中心的“劝善惩恶”论的反话语而被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包含着强调文学自律以及 注重现世、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因此“知物哀”论具有时代的超前性,对日本近代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本居宣长;知物哀论;反话语;文学自律;现世;诗学主题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95−06
本居宣长(1730—1801)是日本的国学大师之一 ① , 他建构的“知物哀”论也被认为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 的诗学理论。就目前对本居宣长及其“知物哀”论的 研究成果来看,多从历史的、哲学的以及比较诗学等 角度进行。相比之下,却鲜有从文学理论角度出发关 注其诗学主题内涵的研究。因此,本文着眼于其诗学 理论本身, 采用文本细读法,对其诗学主题进行考察, 以究明其诗学特征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反话语建构: “知物哀”论的
生成及哲学基础
本居宣长生于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这一 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日本町人阶层的出现。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掌握了经济实力。与掌握政 治权力且倾向儒教文化的武士阶层不同,町人阶层注 重现世主义,肯定人欲,以人情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 取向。出生町人世家的本居宣长,二十三岁游学京都, 学习儒学和医学,师从朱子学派的名儒堀景山 ② 。日本 国文学者日野龙夫在其著作《宣长与秋成》中指出, 在京都游学中,宣长作为汉学书生培养了一种文人意 识。而这种文人意识,对其建构“知物哀”论(主要体 现在《紫文要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135) 。所谓文人 意识,其主要特点就是排斥政治、道德等“公”的价 值世界,而将自己置身于“私”的立场,享受其中开 放的自由。实际上,文人意识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 而町人阶层的注重现世、肯定人欲及人情的价值取向 才是宣长这类町人出身的文人思想形成的根基。正是 由于这样的出生,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使得町家出 生的文人们不像武家那样依附政权,而更倾向于个人 价值的追求。
宣长在京都游学期间,通过其师堀景山接触到了 契冲的国学研究以及荻生徂徠的古文辞学。学界公认 这两人对宣长影响较大。契冲(1604—1701)是日本国 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学问方法在于追溯日本古典, 利用文献学的研究来把握古典精神的真髓。宣长在京 都游学期间,广泛深入涉猎契冲的著作。契
冲的研究 学问的方法论的影响自不消说,其在国学研究中所表 现的文学意识,尤其是在著作《源注拾遗》中反对以 儒佛道德价值观评判《源氏物语》里的人物,突破了 以往各种教诫说,对宣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宣长在其 著作《紫文要领》中评论道:
“该书新见颇多,对近世 各种虚浮妄说一概不取,而引古书加以论证…读此书 则近代诸多浅薄妄说皆不足一取。
” [2](26, 27) 另一位对宣 长有影响的荻生徂徠,则是江户时代儒学中的“古文 辞派” 。其主要功绩概括来说, 主要是在学问方法论上 的发明。徂徠认为要研究和把握中国儒学古典精髓, 必须学习中国古文辞,熟悉原典。其“古文辞学”不 仅运用在对儒学经典的解释上,
同时运用在文学领域, 并提出了文学在于道人情的真实的主张。对此,加藤 周一指出,如果没有徂徠在学问方法论上的发明,也 许就不可能有同一世纪后半叶本居宣长的实证主义文
收稿日期:2013−02−19;修回日期:2013−04−25
基金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项目”(B706312001086);湖南大学“201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曹莉(1975−),女,湖南湘乡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 文学.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4 期 196
献学。 [3](20) 实际上,宣长在其有关“知物哀”论述的 著作中,对“情、人情、実情、本情”等词汇的运用, 无不体现了徂徠的人情论的文学观的影响。所以,可 以说宣长是从契冲及荻生徂徠这二人身上找到了做学 问的方向和方法的。
然而,就当时江户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言,朱 子学为当时统治阶级幕府所推崇并上升至官学。且幕 府或藩的高等教育机关绝大多数不接受町人的子弟。 文学方面,朱子学注重经世致用,推崇所谓的文学三 论即“载道论、劝惩论、玩物丧志论”
。幕府尤其偏重 文学作品所含的道德伦理要素,以之与佛教中的因果 报应说相结合,自上而下推行“劝善惩恶”的文学观。 劝善惩恶论也因此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一种定 式。
武家所推崇的这种儒学意识形态与劝善惩恶的文 学观,显然与町家出身且在宽松学术氛围的私塾接受 儒学教育的宣长所研究关注的学问不会是同一事物。 那么,宣长关注的是什么呢?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应 该能看出端倪来。宣长的早期作品是《排芦小船》。在 《排芦小船》中,宣长断言:
“歌之道, 应是知物之哀, 而弃善恶之议论。…源氏物语之部分旨趣即是以此贯 穿之,而别无其他。
” [4](55) 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小林秀 雄指出,在这儿,宣长的“知物哀”论思想已开始萌 芽,并在此后的《紫文要领》中进一步深入,呈现出 清晰的姿态。 [5](129) 笔者认为,从宣长的这段言辞可以 看出:一,宣长关注的对象是“和歌”及“物语”
。二, “应是知物之哀” 、
“弃善恶之议论”等措辞,明显表 明宣长之所主张以及所排斥。针对与当时新儒们所倡 导的“劝善惩恶”的文艺观,宣长的这番言辞的有所 指向则不言而明。而这些,应该可以说是宣长早期在 京都游学期间关于学问的一些主要思考。
随后,宣长撰写了《安波礼辩》(物哀辩),从词 源的角度考察“物哀”一词的由来。并在此基础上, 于1763年几乎同时完成了重要著作
《紫文要领》 及
《石 上私淑语》。在《紫文要领》中,宣长继承和发展了契 冲《源注拾遗》的文学主张,重新诠释《源氏物语》, 认为紫式部写作的真实意图既不是“劝善惩恶”
,也不 是“好色之劝诫” , “一言以蔽之,即知物哀” 。 [2](95) 同时,在歌论《石上私淑语》中,对于“和歌之缘何 而生?”的提问,宣长答曰“和歌是知‘物哀’生 的” 。 [4](176) 明确了和歌之道在于知“物
哀”这一思想。 由此,宣长从早期的《排芦小船》,《安波礼辩》再到 物语论《紫文要领》以及歌论《石上私淑言》,逐渐明 晰了其独特的“知物哀”论思想。其主要思想内容, 概而言之,就是:一,对于万事万物,人心皆有所思 有所感,所思和所感就是“知物哀”
;二,和歌与物语 文学皆是“知物哀”而产生;三,
“好色”乃为人心所 感中最为浓烈,故“好色”者最知“物哀”
。
从宣长建构的“知物哀”论来看,其讨论的文学 对象限定于日本传统的和歌与物语这两种文学形式。 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强调基于儒教思想的任何注释都 是附会之说,和歌与物语的本质在于“知物哀” 。 而 对于和歌,更是追溯到“神代”
,认为自神代始,和歌 就源起于“知物哀”
。而所谓“知物哀” 就是感知外 界事物而触发的人的各种真实自然情感,即“心有所 思”或“情有所动”。具体而言,即“或喜或悲,或怒 或悦,或愉快有趣,或恐惧担忧,或爱或恨,或恋或 憎,各种所思之事。 ” [4](177,178) 同时认为“自奈良时代, 万事皆仿效唐朝。唯和歌与当时万事不同,其言其意 与我国神代以来自然而生之情趣相合” 。 [4](264) 这里体 现出宣长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企图通过和歌与物
语来 “探寻古意”
。 具体而言就是探寻日本固有的文学思想 和精神世界。 但这些又不是根本, 他说 “世人以此道(和 歌之道)为我国大道。但堪称大道的是‘神道’” 。 [4](266) 显然“神道” , 才是宣长展开 “知物哀” 论的哲学根基。
关于神道,简单来说,它跟佛教不同,是一种注 重“此岸” ,肯定自然、现实,把“现世”作为理想世 界的一种日本土著世界观。这种土著世界观的精髓就 是“真实(まこと)” 。值得注意的是,此“真实”并非 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直接转换外部世界。 “真实”(まこ と)的“ま”是真的意思,是指事物中真善美的东西, 最本质的东西。在日本古代社会,
“言”(こと)与“事” (こと)不分,都意味着人“心”的具体表现。因此“真 实(まこと)”也即是人心的真实,意味着人性根本的 真实性。 [6](156,157)
宣长提出的“知物哀” ,强调感知外界事物而触发 流露的人的各种真实自然情感,就是建立在神道“真 实(まこと)”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
“真实”可以 说是“知物哀”论的哲学中心,并成为其文学审美活 动判定的标准及核心。而当时盛行的劝善惩恶论,是 基于佛教的因果之理以及以儒学的劝惩为目的的文学 观念。本居宣长提出“知物哀”
,
正是以“真实”为根 本,与盛行的劝善惩恶说划清了界限,构建了自己独 特的诗学理论。
然而,宣长在构建“知物哀”论的同时,其实也 意味着对“劝善惩恶”的文学观点发起了挑战。宣长 的这一挑战,应该说与町家的出生有着必然的联系。 町家出生的价值观决定了宣长以儒家为假想敌,因而 诉诸于理论,
“知物哀”论可以说是宣长针对儒学为基 础的“劝惩论”而建构的一种反话语。如前所述,宣
文学艺术 曹莉: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197
长受契冲《源注拾遗》的影响,
“读此书则近代诸多浅 薄妄说皆不足一取” 。这里所说的“近代诸多浅薄妄 说”自然是指当时盛行的“劝善惩恶”之说。 按照富 永仲基(1715—1746)的“加上”理论 ③ ,宣长必然在以 儒学为基础的“劝惩论”的内容上,
“加上”自己的新 观点,创立自己的新说。他针对“劝惩论”所主张的 文学“载道、劝惩” ,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知物哀”
, 道人情的真实;针对《源氏物语》是“好色劝谏书” 的说法,提出“好色”最知物哀,最能体现人的真
实 本性,源氏最是知物哀的好人的观点,等等。纵观宣 长所著的《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无不体现宣长 对当时以儒学为基础的“劝惩论”的批判和纠正。当 然,也正是在这种批判的反话语叙述中,宣长建构了 自己独特的“知物哀”论。
富永仲基是日本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宣长在其晚 年随笔《玉胜间》里提到过他,称其著作《出定后语》 “看了所悟之事甚多” [7](249) 。虽然宣长阅读《出定后 语》的时间是在“知物哀”论提出之前还是之后无从 考证,但对富永仲基的“加上”理论显然是有共鸣的。 针对“劝善惩恶”论,宣长建构一套自己的“知物哀” 论话语,从实践上印证了这一点。
二、
“知物哀”论中文学自律的
诗学主题
在《紫文要领》中,宣长一再反对用道德训诫说 来评判《源氏》。他说:
“然古来注释,皆阅儒佛之议 论书籍,羡其教诫之道,强使物语陷入教诫之窠 臼。 ” [2](94) 强调《源氏》的宗旨就是‘知物哀’” 。对 于和歌,他认为“歌之本,非在于辅政、非在于修身, 唯言心中所思,而别无其他”
。 [4](11) 进而在《石上私淑 言》中说和歌之缘起在于知物哀。 同时,宣长认为和 歌和物语与儒、佛的百家之书截然不同,是日本独有 的文学形式,要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物哀”
,唯 有和歌、物语这样的文学形式。当然,这里也包含着 宣长意欲摆脱汉文学影响的意图。通过这样的论述, 宣长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劝惩”论,标榜了自 身诗学中的独特审美理念,划定了自己的诗学疆界。
实际上,当宣长批评“劝惩论”的“载道,劝惩” 观,而提出物语、和歌的本质在于“知物哀”
,道人情 的真实时,毫无疑问也就否定了文学的外在功利性目 的。而文学作品一旦失去外在功利性目的,没有了他 律作用时,文学审美活动必然转向内部,呈现自律的 特性。文学的自律,也就是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 与灯》中所说的“客观化走向” 。具体而言,
“即在原 则上把艺术品从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 作一个由部分按照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 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 它” 。 [8](31)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宣长的“知物哀”论当然不 是简单地归入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观说”一类就行 了。事实上,情况要复杂些。在此,借用《镜与灯》 中对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悲剧”艺术形式的评论 方式来分析。宣长的“物哀”论首先是用“物哀”即 感知“物之心”及“事之心”确定了作者与世界的关 系;继而用“知物哀”又确立了与欣赏者的关系。然 后, 宣长的方法才变成向心的, 呈现出 “客观化走向”
。 例如,他对《源氏物语》极力推崇,将其喻为“精美 器物” 。 [2](165) 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对此分析指出:
“它 (指《源氏》)的表现世界,就好像‘精美器物’那样, 完全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不仅如此,令宣长惊叹 的是,仔细观看这个器物的人,就好像听到‘工艺人’ 在诉说其‘制作方法’ 。 ” [5](142) 这里所谓的“制作方法” 显然就是表现“物哀”美之道。而这里所说的“精美 器物”的客观存在,笔者认为也就是“原则上把艺术品 从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
。
那么,这种“孤立”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在 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中,认为文学不是单纯 的模仿、再现一般的日常生活,而必须是切实地表现 出受到感动的深层感情。他认为物语文学“整体虽虚 构,但其中有感觉真实之处;即便是假,所言真实合 理,读之亦徒然心动”
。 [2](37) 同时,宣长对说《源氏物 语》是紫式部自己对当时所见所闻的纪录的看法进行 了强烈否定,认为那是以只言片语为依据,以偏概全 的谬见。宣长赞成文学中的虚构描写,他说:
“即便无 一见闻之事,以感同身受之心而写,则也无妨。
” [2](47) 并进一步强调:
“(紫氏的)所谓‘看不厌,听不足’应 是非现实存在,而用心揣摩所写之事。
” [2](47) 在宣长看 来,文学并非单纯地模仿现实。相反,文学艺术纵然 虚构,不真实,但能让人感知“物哀”
,产生情感的共 鸣。这样,文学世界从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
其次,在宣长的诗学领域,把文学作品的道德价 值与传统道德价值进行了分离。这也正是学界公认的 宣长“知物哀”论的伟大独创之处。在早期著作《排 芦小船》中,宣长就开宗明义地表明:
“歌之本体,非 辅政、非修身、唯言心中所思而别无其他。
” [4](11) 断然 否决了文学的外在功利性。然而对于世俗的道德,宣 长却并没有一味地进行否决,他在《紫文要领》中说: “儒有儒之本意,佛有佛之本意,物语有物语之本意, 勉强相混,则胶柱鼓瑟,牵强附会。 ” [2](182) 可以看出,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4 期 198
宣长承认儒佛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但同时又认为文学 有文学自身的标准,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正如日 野龙夫指出来那样:
“宣长树立了文学与道德管辖范围 不同的理论。这样,防止了劝善惩恶侵蚀文学评价, 同时自身的感动也能够正当化了。” [1](188) 文学也就从 道德论中解放出来,充分地体现了其独立性。
当文学世界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具有自己的道德 审美标准时,文学作品也就成功地“从外界参照物中 孤立出来”
,成为自我决定的整体。这样一来,文学作 品的各组成部分自然也将会围绕着自身的目的而展 开。
首先,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材,必然会拒 斥为道德训诫等外在功利性目的服务,而以服务于文 学自身的目的为原则。如前所述,
“知物哀”论诗学范 畴里,文学审美就在于“物哀”
,即真实、自然地表现 外物对人情感的触动。那么题材的选择自然也就围绕 “物哀”这一目的而进行。宣长认为《源氏物语》之 所以强调好事坏事之分,是因为“对于这些事物,感 知好事好,坏事坏,悲事悲,哀事哀,(读者)才知物 之况味,知物之哀” ,即“知物哀” 。 [2](48) 同时,他指 出,正是因为“‘好色’者最感人心,也最知‘物 哀’” , [2](109) 所以紫式部为了体现源氏“知物哀”之美, 而极力渲染其“好色”不伦之恋的。那些不伦之恋的 描写,恰似蓄积污泥浊水,是用于培植美丽的“物哀 之花”的。而“爱‘物哀之花’的人,对恋情之水之 清洁污浊,并不过于理会” [2](123) 。另外, “源氏有离 经叛道之
不义行径,多好色风流之事,却一生荣华富 贵,世事无不遂其心,且子孙繁昌盛,获得‘太上天 皇’之尊号” 。 [2](127) 这里,宣长认为紫式部写《源氏 物语》,对主人公源氏的不伦、悖德之恋用笔墨居多, 却又没有落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俗套。言外 之意表明,紫氏是按文学自身标准选材的。
从宣长对《源氏物语》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 主张以“知物哀”为目的而非世俗道德标准来处理题 材。那么,在这种纯审美状态下,世俗标准的所谓善、 恶、美、丑任何题材都可以自由地进入作品,其中包 括了儒佛标准下的不伦之恋等大逆不道之事。显然, 较“劝善惩恶论”宣长对题材处理显得宽容得多,这 样无疑扩大了审美的范围,题材自由的闸门由此而打 开。必须提到的是,宣长的这种创作主张自然也就体 现出对自然人性的一种广泛的包容与理解。
其次,为了充分体现“物哀”之美,宣长也十分 注重语言材料的精雕细琢。对于物语中为何对四季及 人物衣物进行细致描写的疑问,他认为:
“四季推移与 风景描写,皆为使人‘知物哀’
。…人物等细致描写亦 如此。即便脆弱器物,制作精美者让人观之亦喜,此 乃感知‘物之心’ , 知‘物哀’之一端,万事皆如 此。 ” [2](65) 而对于和歌形式,宣长也赞成《愚问贤注》 的观点 ④ , 认为 “所谓歌之物, 使听之人感知物哀为要, 追词之文采、声调之优美,乃和歌本然,神代以来一 直如此”
。
[4](198, 199) 除此之外,宣长认为紫式部在风俗 人情、情节安设等方面用心巧妙,无不以体现物哀之 美为目的。
另外,文学创作不能单一模仿现实生活,创作过 程中对想象力加以强调与推崇就成了必然。正如古希 腊批评家斐罗斯屈拉特所说:
“想象比起摹仿是一位更 灵巧的艺术家, ……摹仿只能造出他已经见过的东西, 想象却能造出他所没有见过的东西。 ” [9](152) 本居宣长 也是非常注重想象力的运用,他在《紫文要领》中说: “即便无一见闻之事,以感同身受之心而写,则也无 妨。 ”“紫式部所谓‘看不厌,听不足’ 应是非现实存 在,而用心揣摩所写之事。
” [2](47) 小林秀雄分析指出: “事物的知觉作用,不是感觉到什么就停止了,而是 ‘看不厌,听不足’那样变化。事物的知觉没有割断 同对象的关系,而是在想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对 事物的事实判断中,是无法阻止这种发展的。 ” [5](167) 对于本居宣长在《紫文》中所说的“心动” ,他认为就 是上述那样的自然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朴素的 认识能力即想象力。同时,加藤周一也评论道: “ (宣 长)他认为要逼真地表现古代人的‘真实感情’还必 须启动想象力,活用直觉。 ” [3](151) 而这种“真实感情” 在物语与和歌中的体现就是“物哀”
。
因此,可以说宣长的“知物哀”论“重技巧、重 词,通过形式的规范性来研究人的内面的真实性,将 真情与技巧调和而达到统一”
。 [10](171) 也就是说技巧与 形式结合,充分呈现出物哀之美。
综上所述,在宣长的“知物哀”论中,无论是从 文学批评角度,还是文学创作角度,都排除了外在的 功利性目的。他否定文学是对生活的单纯模仿,认为 文学自有文学的审美标准,从而割断了文学与生活的 联系。进而把文学当作独立自足体看待,只关注文学 自身目的,追求特定形式,注重文学内部技巧、辞藻 等因素,从而使得文学自律的诗学主题得以彰显。
三、
“知物哀”论中注重现世、
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朱子学被幕府所赏识推崇而 处于官学地位。具体而言,朱子学的“理本体论”和 “天人一理”理论“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
文学艺术 曹莉: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199
利用自然界的秩序,即天地的空间、上下的关系,来 说明人类社会的价值上的上下关系, 从理论上把君臣、 父子、夫妇的上下贵贱之义加以合法化”
。 [11](7) 朱子学 这种重大名义,讲究严格的君臣等级关系以及天地自 然法则的世界观,为规定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 用,因此受到幕府统治阶级推崇。较之此前占主流意 识形态的佛教,朱子学为当时的日本提供了现世主义 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政治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重 群体而抑制个人的思想。 ” [12](30) 朱子学从学问转为一 种国民的社会规范,稳定了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束缚 了将军以下的武士、町人和民众的思想的自由发展。
社会结构方面,如前所述,那就是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出现了町人阶层。町人重视现世主义,肯定 人欲。尤其到江户中后期(元禄时期),商品经济进一 步发展,町人阶层得到了勃兴。 掌握经济实力的町人, 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一种商业社会的合理主 义精神和个人情感自由的社会价值观。
“合理主义的发 达,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朱子学,将重点从主观的 ‘义理’位移到客观的‘真实’(まこと)上” [13](166) 由此掀起了自由探索人性本质的潮流,并渗透到文学 创作、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
宣长的“知物哀”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背景 下,针对以儒学为基础的“劝善惩恶”论建构起来的 反话语。如前所述,宣长的“知物哀”论是基于神道 基础上。神道是一种现世主义的世界观。对于神,宣 长认为“但凡所谓神,是在古文献等所看到的天地诸 神为始,或说坐在祭祀它的神社里的御灵。又,人更
不消说,海山鸟兽草木之类等,其余何足稀,不寻常, 将优秀之德,可畏之物称为神” 。 [3](148) 加藤周一对此 分析认为,从宣长对“神”的解释来看,在宣长的哲 学世界里,神和人是的关系是连续的,世界是由神和 人创造的。而在这个神、人创造的世界里,神意难以 预测,唯有“真实”的人心和“时势”的现实化,在 现实中起作用,这就是现世。而这些又正是宣长取得 诸多经验的来源之处。因此,从中体现出他的现世本 位主义思想。 [3](150−153)
基于这样的信仰,因而探寻“真实”的人心就成 了宣长毕生的追求之一。而“物哀”论显然是宣长在 文学领域为自己的追求所付诸的实践之一。他在《排 芦小船》、《紫文要领》、《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一 再强调物语、和歌的本质在于“知物哀”
,即人情的自 然、真实流露。在宣长看来“人之真心如女童般幼稚、 愚懦。坚强自信非人之真心,乃表面装饰之物。深入 内心,则何种贤人,皆与女童无异。
” [2](154, 155) 进而, 对于基于儒佛中心的“劝惩”的道德训诫说,他认为 “大凡儒教、佛教之教诫,多有抑制自然的人情之 事……” [2](181−182) 且“儒佛之教,助长人情之善,抑其 之恶并加以改之。循其教,恶之人情化为善。而和歌、 物语则不问人情之善恶、邪正、贤愚,只道自然真实 人情,将人情真实呈现。人读之知人情实态并知‘物 哀’”
。 [2](156,157)
以上引文,无疑体现了宣长的主要文学观:一, 宣长的文学本体论观,即文学的本质在于表达人情的 真实即“真实的人心” ;二,宣长认为,儒佛为中心的 “劝惩”文学观对自然的人性进行了抑制和压迫。因 此,可以说,以“人”为主,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是宣 长理论核心。
正因如此,宣长才会从客观的角度评述《源氏物 语》中对私通、乱伦等悖德之恋的描写,认为是体现 人的自然真情,是一种“物哀”之美。同时,对于“好 色” ,他也采取一种包容的心态,认为好色是一种最为 浓烈的自然情感,最能体现“物哀” 。以当时的社会背 景以及盛行“劝惩”论而言,无疑宣长的“物哀”论 表现出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种广泛包容。正如宣长在 《直毗灵》所说的“生来随心所欲,若是力所能及, 自知好自为之” [14](304) 的那样,个人自由得到认可,人 的主体性无疑也就显现出来。
加滕周一指出“本居宣长注目的,不是佛教的彼 岸性,而是日本人的世界观的此岸性。他探求的不是 儒教的善恶,而是土著文化传统的调和。
” [3]146 这种调 和被宣长运用到文学世界,必定是关注现世,人性得 以解放,人作为主体在文学世界里得以获得自由,从 而相应地建立起追求现世本位的价值体系。因此,注 重现世、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四、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宣长的“知物哀”论是针对以儒 学为基础的“劝惩”论而建构的反话语,它表现出否 定文学功利性,讲究文学的自律以及注重现世、以人 为本的诗学特征。虽然“知物哀”论完全排除文学的 社会功效,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局限性,但就当 时幕府统治下的封建时代而言,
“知物哀”论仍具有超 时代性和近代人文主义色彩。日本近代第一部小说理 论著作《小说神髓》,排斥劝善惩恶说,提出“小说的 主脑在于人情”的观点,学界公认与本居宣长的影响 分不开。其次,日本小说理论偏重于个人内心深层的 开掘,尤其是私小说远离社会、超脱政治的特点,也 是与“知物哀”论的影响分不开的。另外,20世纪初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4 期 200
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东渐,在日本能够生成唯美主义流 派并产生重量级唯美主义作家,也是与传统诗学“知 物哀”论的诗学特征具有一定契合性有关。正如叶渭 渠先生所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文学及文学思潮走 向近代,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距离,但与过去的传统 文学及文学思潮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而且是一脉相 承…” [13](210) 作为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 宣长的 “知 物哀”论不仅对近现代文学思想产生影响,对今后日 本的文学发展也必将继续产生影响。
注释:
①日本文学史一般将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
称作“国学四大师” 。
②堀景山,江户时代名儒。反对朱子学的道学观,主张以人情为
主的诗学观。
③富永仲基,江户中期的思想家。
“加上”即将某种东西加在另 一东西之上。 加上法则是思想的历史性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论 问题。意思是思想家的思想都并非源自天启或者独觉,而来自 于他所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对其内容进行了加法或减法。
④《愚问贤注》:日本南北朝时期歌人顿阿回答二条良基提问的
问答体歌论著作,出于1363年。
参考文献: [1] [日]日野龙夫. 宣长与秋成[M]. 东京: 筑摩书房,1984.
[2] [日]本居宣长. 紫文要领[M]. 子安宣邦校注. 东京: 岩波书
店,2010.
[3] [日]加藤周一. 日本文学史序说(下)[M]. 叶渭渠, 唐月梅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4] [日]本居宣长. 排芦小船· 石上私淑语[M]. 子安宣邦校注. 东
京: 岩波书店,2003.
[5] [日]小林秀雄. 本居宣长(上)[M]. 东京: 新潮文库,1977.
[6] 叶渭渠, 唐月梅. 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M]. 北京: 昆仑出
版社,2007.
[7] [日]日本思想大系 第40卷 本居宣长[M]. 吉川幸次郎, 佐竹
昭广, 日野龙夫校注. 岩波书店, 1978.
[8] [美]艾布拉姆新. 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张
照进,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 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 北京:
商务出版社,1980.
[10] 叶渭渠, 唐月梅. 日本文学史(近古卷下)[M]. 北京: 昆仑出
版社,2007.
[11] [日]日本近代思想研究会.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M]. 马
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2]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上)[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5.
[13]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4] [日]吉川幸次郎编集. 日本の思想 15 本居宣长集[M]. 东京:
筑摩书房,1963.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me of Motoori Norinaga’s Theory
“Mononoaware”
CAO Li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China;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Mononoaware”,with its Japan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as propod by Motoori Norinaga, Japane poet and literary Scholar. it was brought up as the counterdiscour of the theory “promoting kindness and punishing evils”. The theory emphasizes literary autonomy, worldly being and humancenteredness. It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modern Japan ever since.
Key Words: Motoori Norinaga; Mononoaware; Counterdiscour; Literary autonomy; Worldly being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