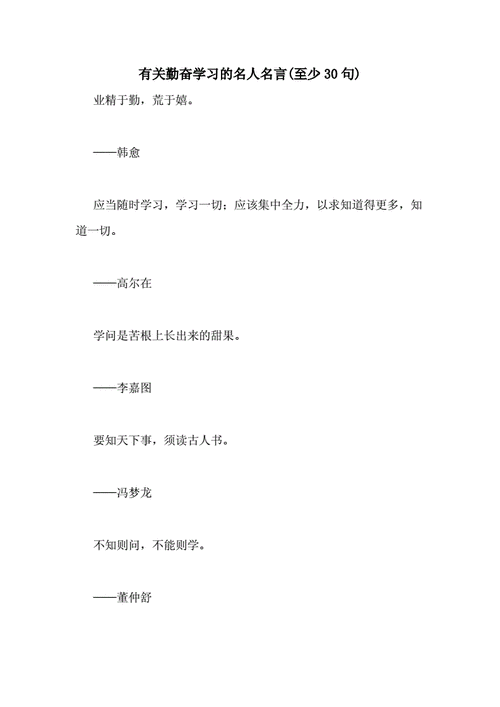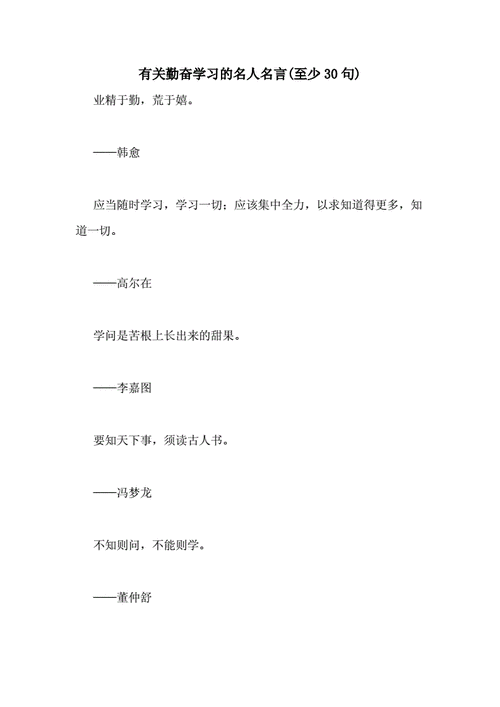
“刀下留城”:平遥古城护城记
从1980年开始,全国一片拆掉旧城建新城的形势,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那个时候盛行两句话,就是“要致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样一来,到处都在开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拆掉旧城建新城,拓宽原来的旧马路变成新马路。但是很多城市不大理解怎么样是正确的城市建设方式,在此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无序拆迁。实际上,我们需要做好城市规划,要有一个详尽的能合理指导城市建设发展的城市规划。
欲拆平遥城?且慢
在拆山西平遥城墙的时候,我正带着学生在榆次做总体规划教育实习。平遥古城离榆次很近,我向当地借了一辆小车,走了一圈去看一看,一看就吓了一大跳,所有的东西都在拆。因为我跟我的老师董鉴泓先生1962年去平遥调查过,就认识了平遥古建文物队的队长李祖孝和李有华,他们看到我都还认识,他们就来跟我讲,说这里要救一救,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拆啊,太可惜了。我说你们怎么拆房子的?你们的规划图拿来我看看。当时平遥建设局的工程师王中良把规划图拿出来,王中良是一个很老实的地方干部,但是这个干部不懂规划技术,他是搞市政管理的。当时说要开马路,要开多少米?开24米宽的路,就拆掉了房屋,然后就把城墙拆掉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李祖孝、李有华就带我去看已经拆掉的许多明清时代建筑的残址。
1980年平遥刚刚拆了一条大街,从西城门拆起,进去180米,这一段路已经拆掉了300幢明清建筑。
平遥城里大多数房屋都是明清建筑,要着重说一句,山西省的古城里所有的房舍、建筑大多是明清建筑,像现在你去找找看明代建筑,到哪里去找?这个地区各个古城都是明清建筑,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就希望他们能很好地做城市规划。当时,山西省建委的规划处处长赵晋普,曾是我们同济的学生,我教过他。他说,正好你们同济的老师来了,可以帮助我们搞一搞建设。他就把山西省各个城市规划部门做的图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一看又吓了一大跳,忍不住生气骂起来,我说这种图还能叫做规划图?你是学城市规划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图?他说他也没办法。我一张图一张图地看,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悲哀,就是所有的图几乎都是不合格的。赵晋普说,阮老师那你看看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先停下来。他就请示了一下省政府,回复说不可能。后来,我说,我们换个方式,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地方进行试验建设。
到了平遥不久,古建筑就不拆了。因为没钱了。平遥当时很穷,城市领导是主张要拆的,但是拆也要工钱。我说,平遥现在停止拆老城了,城市照样可以现代化发展,你不要用这种拆了旧城再建新城的办法,你不拆旧城也可以建新城,我们要有合理的规划办法。
当时就是这位赵处长找了山西省建委主任,这个省建委主任同意由我来做一个合理的规划,但是要求是要快,这个规划要一个月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按不按照这个执行,不能确定。我想虽然结果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让拆老城的事情停一停。那个时候正好放暑假了,我就赶快回到学校招兵买马,挑了12个优秀的学生。我对学生们说,第一是没有钱,咱们是去义务劳动;第二是会很辛苦,都要吃苦耐劳,并且技术水平要高,能画能写;第三,你还要有一点特长。当时所谓的特长其实不是指别的,主要是指会骑自行车、会摄影、会做模型。那
个时候不是人人都会骑自行车,因为调查要跑,会骑自行车肯定会快一点。然后会拍照,以前的照相是用胶卷,自己要会冲印,要会放大,因为没人帮你做这个事情,只能我们自己做。还有一个就是会做木工、做模型,因为到那边要自己动手做。当时挑出来的12个人后来全出了成绩:“其中就包括同济大学现任的副校长吴志强、上海规划院的院长、广州市规划局的局长,还包括张庭伟,当时他是研究生,现在是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
“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
我那个时候也有四十几岁了,我在念大学前当过兵,年龄比学生大得多。去平遥要花钱,买火车票、吃、住,就预支了教学经费3000块钱。回来要用教学经费慢慢地还的。我每年进行的全国各地古城调查的经费要花掉一辆小汽车的钱。都是我自己贴钱的,每年在这个项目上花去15万到20万元之间,所以我买不起房子,用不起车子。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100多个古城镇的调研和规划,做好了就把材料上报上去。学校却没有专项资
金支持这件事。
当时平遥调研也是我们自己拿钱,各种日常开销都要自己拿钱。当时我去之前,我就跟学校几个主要老师讲这件事,一个是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一个是古建专家陈从周教授。陈从周教授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他说,对于这些城市来讲就是一句话叫“老城老到底,新城新到家”,新旧分开。这个建议很有智慧。
后来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也到平遥来了,过来了之后具体做了一点指导,系主任董鉴泓教授也到了,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
我到了平遥以后就发现,平遥有非常珍贵的文物遗产价值,有很重要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平遥的城墙,平遥的城墙是后周时期留下来的,像这么古老、完整的城墙中国没有几个,实在是罕见呀!当时,全国一片拆城风。当时只有4座城墙还留着:第一座是平遥,只拆了一个口子。第二个是西安拆了一半,还留了一半。第三个是荆州,因为湖北荆州的城墙本身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第四个是东北的兴城,袁崇焕明末在东北抗击金兵的城市。因此我们就说这四座古城是当时中国仅存的相对完整的古城,这些古城都可以列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当时,荆州城和西安城已经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了,进入这个级别的名录以后就能有机会把它保住。
同时,我在平遥古镇又发现了两处重要的古建筑:一个就是双林寺,双林寺里存有二千多个元、明、
清以来优秀的雕塑,这个雕塑之精良,内容之丰富,应该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如普通山门里的四大金刚,人家的四大金刚就是“风、调、雨、顺”,一般是穿上盔甲的武将装束。双林寺里的四大金刚竟穿着露脐装,肚子、胸部都裸露到外面。它们是元代的雕塑。
另外,我们常见的十八罗汉,一般是什么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然后是沉思罗汉、长眉罗汉等,双林寺里的也不是这样,他们是怒罗汉、哑罗汉、醉罗汉、睡罗汉、病罗汉,元代的雕塑非常有特色,很人性化、生活化,把人的神态用罗汉的形式表现出来,很仿真的,有活灵活现的感觉。另外,一般常见的观世音菩萨是男身女相,而他们做的是女身女相,胸部高的,屁股大的,侧身坐着,一看就是漂亮女子的形象。寻求“护身符”
最特别的是双林寺的韦陀像,看那浑身隆起的肌肉,活脱脱就是中国的男性维纳斯。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说这个是世界级瑰宝,这些罗汉像是从来没有在其它地方见到过的,是惊世骇俗的。
还有一个就是镇国寺,镇国寺是唐末的,是北汉天会七年(963年)建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第一个是南禅寺,第二个是佛光寺,第三个就是镇国寺,而年代早晚排序依次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的寺庙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镇国寺当时却不是,因为当地没人申报。我们立刻决定申报。我让学生们把镇国寺的相关材料准备好,把古城墙首先画成考古建筑图,我拿这个去报批,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谱了。若是有了这个认定称号,平遥古城就有了免于被拆的“护身符”了。
平遥的那些明清的民居,也都特别精良,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比如它的文庙大成殿。大梁上写着金大定三年(1163年)建。甚至城市当中的市楼,建的时候是清康熙二十八年,都明确写在那里。这些建筑中光明代的东西就多到几百个,还有那些像城隍庙、清虚观,一看就是元代、明代建的。但是,当时山西省留存了全国65%的古建筑,到处有精品。想要得到保护,不让它被拆迁破坏,我们还必须想方设法拿到这个“护身符”。
我们日夜奋战了一个月以后,我带着做好的材料,专门去汇报,我们把图做得很好,希望让那些领导们能看得懂并认同。我先给县里领导汇报,然后再跟省里领导汇报,然而,县里和省里领导都没有表示出较大的兴趣和支持,然后我就想办法,直接把材料送进了北京。
我一个人背着图纸,问县里借车。当时借的不是汽车,是自行车,想借自行车推我的行李,结果没借到。我就只好自己背着走,一共是7里路,路不远,但要扛着行李、图纸,当时还下着雨,很不方便。我浑身是泥浆,我走到火车站,乘夜车从平遥坐到了太原,然后到太原转火车去北京,到了北京见到了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罗哲文,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阮老师,您赶快去想办法洗个澡吧!”当时,我完全就是像叫花子一样,浑身又是泥,又是水。我把规划和图片资料给罗哲文、郑孝燮先生看了,他们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我提出请他们去一趟,当时罗哲文和郑孝燮都是重量级的专家,人也很热心,先前搞保护和考察古建筑时我和他们已经熟悉了。
郑孝燮说的“刀下留城”
我请他们去了以后,全国政协常委去了,当时的山西省省长也跟着到了平遥。郑孝燮跟山西省省长交流说,这些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地执行。我就想要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于是,当场就请他们把这个话写下来,然后请郑老签名,在我们当时的会议纪要上写上这几句话:“这个规划是高水平的”。然后,省长马上就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
我说这还不算,这个规划能不能执行,还需要钱,没有钱无法执行。那时候还没有设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当时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归他管,我后来跟他说:“平遥的古城墙应该是国保单位,肯定没问题。你能不能给点修缮文物的钱?”他说单位是有笔钱,但是这个钱是专款专用修长城的。我说你自己以前也说过,所有中国的长城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是由于各个城市都有城墙,城墙是洪武年间跟明长城是同时修的,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城墙几乎都是从洪武三年开始,各地自己修的。万里长城是中央政府修的,而这
些城墙则是各地方政府同时修的。我据理力争:
“你自己也讲过除了北方的长城还有南方长城,所有的城墙都是一个体系的。”这些平遥的城墙跟长城是同一个体系的,是万里长城的延伸部分。他说这个话有道理,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能不能多拨点款,然后他就一下子拨款8万元。
当时,在1980年代的时候,8万元不容易,是笔大数字了。
8万人民币直接拨到平遥,专款专用维修城墙,我就怕这笔款不落实,我就叫当时的同济研究生李晓江在北京盯着看这笔钱是不是真正拨出来了,拨出来以后这笔钱是不是到了平遥,到了平遥以后是不是这个钱用在城墙的修缮上,一定紧紧盯着。李晓江就做了这个重要的事情。
他盯着这笔钱汇出了,然后这个钱就批到文化部财务处,他到财务处看,看钱汇出去没有,用什么方式汇的,银行汇款还是邮政汇款还是银行转账。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叫他赶快赶到平遥去。赶到平遥以后钱还没到,我说你在那儿等着,等着过两天钱到了就去找县长。县长一开始不相信,不相信国家文物部能批这么多的钱,根本不相信有8万。后来银行的行长拿着支票的抄件就找县长去了,是手抄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县长一看高兴得不得了。
我让李晓江在平遥建立古城保护的修缮委员会,然后成立一个古城墙修缮的工程队,把建筑工程师调过来修城墙。我要他落实了再回校。李晓江在同济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北京工作,现在是中国城市规划院的院长。跟我到平遥去的这十几个学生,回忆起平遥那段经历,都还会激动、兴奋,觉得干成了件大事、有意义的事。
从“刀下留城救平遥”这件事当中我也有很深的体会,我发现,不懂技术的人在那里搞技术,是最大的缺陷。我在平遥做规划的时候感到很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技术干部。举个例子,当时平遥县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懂什么是“单行道”。我们做平遥规划时,认为平遥古城里马路还比较宽,可以用“单行道”的方式来通车,就没有必要来拆房修路了。但“单行道”这个名词平遥人都不懂。
他们更不能理解什么是修复,什么是维护。维护和修复是不一样的,当时,许多技术干部不懂。从平遥回来以后,后来还有其他的城市,比如丽江的保护、新绛的保护,还有江南古镇的保护都需要懂保护理念和技术的人去抢救我们的古城和古建筑,后来我还开办了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培训班,利用我这个同济大学老师的身份,同时我正好又兼任国家建设部城建领导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的身份,给干部们介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些专业知识。
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批初步懂得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干部,有了这些人员,才有了这些古城保护的具体工作的落实和成绩。我开玩笑说这些人全是我派到古城里去“卧底”的。当他们在古城里发现了保护工作被刻意破坏的情况,便通知我去抢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