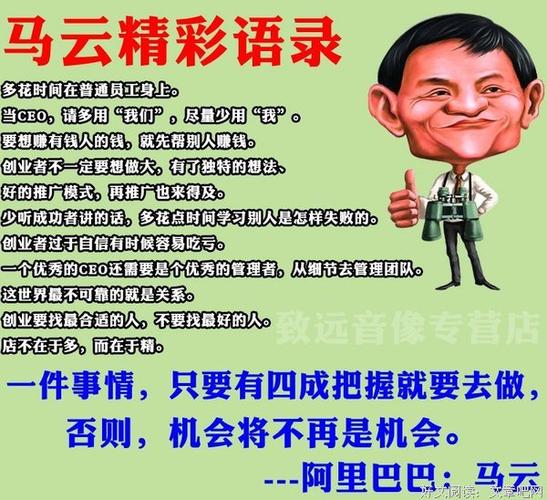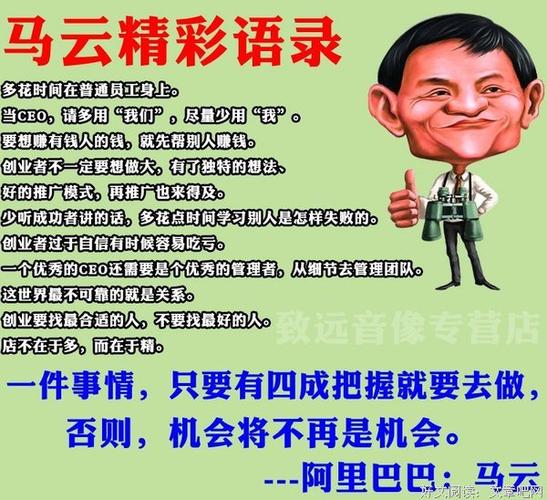
卡夫卡高考作文
一点素心
作者:黎武静来源:《羊城晚报》2013年2月3日
偶然地,被一张照片震撼。拍片现场,红墙青瓦,演员在拍片之余执一支毛笔,捧一瓶水,就这样,在墙上笔走龙蛇,行云流水。
是什么让人感动,在这短暂的瞬间?想起两个字:素心。“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15年前,年少的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只觉得漂亮,却未必懂得,但是现在突然觉得有一点懂了。
纪晓岚的老师曾撰一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想想,不过一念之间。当野心只为白云留,花开花落,山中红萼。世味有浓淡,素心无嗔喜。
济慈写诗时常写在纸片上,事后夹在书里做书签,或者随手扔在一边。1818年的春天,夜莺在他的屋外放歌。清早,他从餐桌边拖过一把椅子,坐在葡萄架下的草坪上,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写着。写完却将纸片塞到书架里了事。查尔斯将纸片拣出来,细细誊出,这就是济慈的《夜莺颂》。济慈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卡夫卡的遗嘱: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的
遗物里,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这是一个被米兰?昆德拉称为“被背叛的遗嘱”,他的朋友将这些整理出版,于是文学史上注定要留下卡夫卡的璀璨光芒。
风行水上,原来只是路过。那些不朽的传奇,在诞生的一刻,并不是为了流传。
弘一法师今宵别梦寒
梁衡
这个深秋的黄昏,当我们来到白马寺,人迹已是萧然。寺内显得清静而空旷,我们几人散漫行走其间,很自然地便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由佛教东传谈到得道高僧,其中一位女编辑和我谈起了弘一,并用她柔和的音色浅唱了几句《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此时,风掠过,白马寺塔檐上的风铃咣当作响,穿透血红的残阳,余音在紫气缭绕的寺院上空萦回。寺院的风铃与其他风铃所不同的感觉是显而易见的,既不小巧又不悦人,那种金属的音质本身就是一种感召,一种意象,尤其在这样一个深秋薄暮之际,令人听罢真有必要转过头来,把中断了几年的弘一书道研究接着做下去。
只是,按弘一之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那好,就先走进弘一吧!说真的,对于弘一,我一直认为是
个谜。我自己是没有能力进入那个已经逝去的心灵世界中去的,如今只能凭借他的遗墨,凭借他的亲朋故旧回忆甚至民间传说来复活此人。幸好,他所行未远,不至于雪泥鸿爪稍纵即逝。尤其是我的家离他圆寂的开元寺仅百步之遥,这些年又看了不少他的墨迹,便多少有些亲和的可能。不过怎么说,弘一对于生活在现实又忙乱的人来说,在精神方面,已经相隔一道厚厚的屏障了。
未出家时,我们称他李叔同,出家后则敬称弘一法师,出家前后的肉身属同一种物质,只是精神、灵魂已经异化。家世浙西望族,生于天津,年轻又有才气的李叔同,那时多么令人歆羡啊。这一点他自己也深有感受,并不失时机地在这人生舞台上充分表现。翩翩裘马,进出名场,红氍毹上,舞袖歌弦,什么都要露一手。演戏,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没有不上手的。这时的他的确是一位翩翩美少年,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底子缎带扎着裤管,眉宇间尽显英俊洒脱之气,一举手一投足,称得上潇洒倜傥,光彩照人。可是曾几何时,收拾铅华,摒却丝竹,在我脑海中印下的,却是清癯枯瘦,古貌古心,一副古之高僧薪火绵延的零余者形象了。
人生真的是一出戏。岁月的长风卷走了他青春的容颜,转瞬间留下平淡和寂寥。
李叔同的出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先后披阅了诸家之
说,有与李叔同过从甚密的夏丏尊、丰子恺,有他的高足广洽法师,更多的还有文人们从不同层面、角度的阐释,可惜没有一说能够让我感到若合符契。我只能说:此谜无解。就是让弘一本人来解,也
是无从解开人生的重重绳扣的。这么一来,我对诸说都不感兴趣,有时看到学人在争论这一话题,内心还感到腻歪。人生是能够穷尽的么?没有穷尽。再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正常的轨道可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说话间就成另一种模样了。至于无序、无规律可循,超常规的状态是经常有的。苏东坡当年说过人生如梦,梦就是无常。再说,人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形而上状态,如精神、禀赋、情怀、缘分,真正是无法规划,无从定量。也许世间什么都可能一样,但是人
和人,的确无从一样,这也就使人感到云谲波诡,无可究诘了。
李叔同终于在很突然的情况下断绝尘念出家了。说是因为缘也罢,宿命也罢,从滚滚红尘中义无反顾地遁入空门,李叔同消失了,弘一诞生了。我几次听到文人为他这种质变而嗟叹,以为文坛艺苑少了一个大才子,这损失无可弥补,又看到有人为佛门庆幸,说是得一高僧。我弄不清楚这幸与不幸的标准何在。再说,人生的转变能用幸与不幸二极如此简单地裁定么?显然是文人的偏爱和多情所致。大千世界,行当万千,彼此消长、互为涨落是很正常的。命数之间并不存
在什么衡量的标准,只是过程耳。李叔同向弘一转化,高深一点说是一种生命向度的选择。选择是相对于不选择而言的。选择可以有理有据,也可以无理无据,世事无常,什么都有可能变。通俗一点说是“换一种活法”,这没有什么不正常。你想想,在当今社会巨变的时空里,比李叔同骤变弘一更令人拍案惊奇的事还少么?只不过在当时,李叔同的转变太突兀和惹眼一些罢了。对于人生方向的选择,
我钦佩的是他对于自我的负责。生命本来无所谓意义,精神也无所谓高尚鄙俗,总是在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方显出它的成色来。弘一成为人们景仰的高僧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修炼过程,其中包含没完没了的闭关治律、禁语、静修、写经,包含几十年清汤寡味的茹素生活,包含那个时代凄风苦雨带来的重创。
晨钟暮鼓、古诗清梦,彻底地磨洗了一个人的灵魂。
弘一的伟大在于他的平常。记得孔夫子曾让弟子广开言路“盍各言尔志”,足见志向各有不同。不同道不足语怪,问题在于能够不改初衷执著而行。今日的佛门,已不再是弘一时代的清冷静寂,变得熙熙攘攘起来。本是清净地,如今游客如织,门票上扬,新时代的思维培养了与之相适应的佛门弟子和佛家行为,这已毋庸赘言。尽管如此,假使我们身边的某一位亲人或好友突然出家当了和尚,恐怕在很长一段时日里,要成为嘴边的话题反复提及。无论怎么看,出家总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