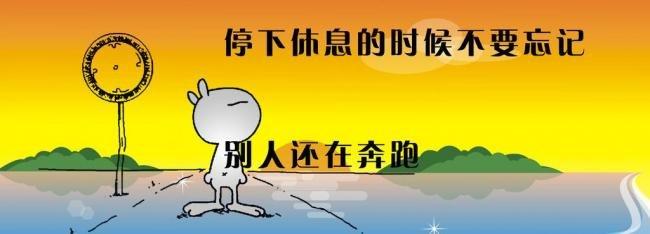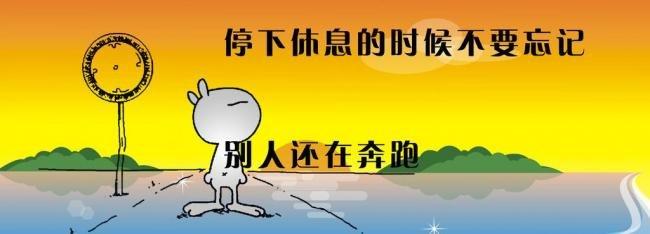
读书随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5-2)
熊彼特认为,劳动是否为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个说法对不对其实并不重要,劳动价值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它是否陈述了真理,而在于,它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分析工具或者方法。
其一,劳动量如何计量和平均,这就是一个从李嘉图开始就觉得头疼的问题,因为它假设了劳动的均一性——即所有的劳动都是同质的,这显然违背了常识。
其二,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完全竞争市场,到了寡头、垄断市场,影响因素不再是“平均”因素,则解释力就急剧下降。
其三,无法解释事实上自然因素对价值的影响,如位置、土地、资源丰裕程度等,熊彼特认为,李嘉图为了排除自然力的干扰,专门发展了地租理论,用于解决土地差异带来的产出差异问题,马克思对这一点也毫不犹豫地加以继承。
其五,劳动力价值的衡量是有问题的——这直接决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脆弱性,因为马克思是把人的潜在劳动能力当做其它普通生产资料或商品一样进行价值衡量的,即供养培育这种劳动能力所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而实际上,生活资料价值并不直接等于他所提出的劳动力
价值。
人是不能直接等同于商品和机器的。由此而引发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个重大的缺陷在于,如果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为了扩大产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会持续上升,一直到剩余价值为零。
作为分析工具和解释力而言,劳动价值论确实不如边际效用论,尽管边际效用论的立足点也一样可疑。
虽然工具简陋而漏洞百出,但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本人超绝的洞察力、卓越的观察力以及提炼能力,使他可以用经验(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弥补这种缺憾,达到一种后人难以超越的地步。
比如:马克思把李嘉图那里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转换成了他自己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然后从两种资本品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来解释工厂利润长期有下降趋势。
熊彼特认为这种观察是卓越的,尽管解释得比较牵强。在静态均衡的市场中,受到竞争的影响,厂商利润率确有长期下降趋势,只不过这种下降趋势持续地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
模式的出现而打断。
从竞争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引申出了“资本集中”概念。熊彼特也认为这是马克思卓越的观察力和提炼能力的体现,虽然他对于资本集中以及垄断出现的分析工具和推导方式也一样受制于劳动价值论而有很大的欠缺,但毫不影响他在19世纪上半叶就作出的这种伟大预见——大型企业的出现,产业垄断者的出现。
包括进一步引申出来的经济周期理论,最具价值的部分,也依然是马克思对周期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熊彼特说,不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动力学的解释如何凌乱,光是他能感受到周期性特征,就已经是极其伟大的成就了。
在马克思之前乃至同时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危机看作是一个孤立事件,仅仅是一次小概率不正常事件,除了马克思,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指出,危机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以及一系列政策管制、信用扩张等因素造成的人为后果。
要知道,那是在1847年,英国建立起来的金本位制度正在主导世界秩序,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如日中天、全球扩张,爱迪生、贝尔等一干推动技术革命的人物还才刚刚出生,大清的国门刚被打开。
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小小的暂时性的波动,谁会那么在意?马克思却指出来,这种危机将是周期性的、持续性的,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将越来越大,最终颠覆掉资本主义体制本身。
4.作为导师的马克思。作为工人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与他构建的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鸿沟。这一鸿沟一直延伸到后来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
熊彼特指出,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其实没有一个论点是可以与革命直接挂钩的。比如劳动价值论,并非只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社会主义者观点的人才会认同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封建领主经济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同样存在并且发挥作用。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所称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乃是从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角度阐述的,至于这种取代是激烈的革命,还是渐进改良,他并没有明确——他本人十分清楚,资本主义体制向社会主义体制的演变,一定是时机与条件足够成熟,瓜熟蒂落的结果。任何主观的飞跃和僭越,最终都会遭受惩罚和失败。
作为导师的马克思,其实领导和参与的,乃是一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这个运动仍然是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之内的——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与斗争。通过这种合法斗争,增促工人阶级形成自我意识、自我组织。
马克思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遵循制度演化动力学基本规律。不然他怎么会解释,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认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乃至持续到一战前后,欧洲一直都有诸多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但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而非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那些坚持马克思原版科学理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人或派别,我们有一个别称:西方马克思学说。
也许最重要的评价就是熊彼特的——要独立于我们的爱憎情感,你可以不相信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光明的来源,你可以认为它甚至是黑暗的力量,也可以认为它的一些论点是错误的,或者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但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不论正面的论证还是反面的驳斥与批判,不但不会给它以致命伤害,反而会显示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作任何社会预测,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答案是或者否,而在于论证结论的论据和方法。
这一点,我们至今未能理解。诚如敝号在前不久随笔张磊的《价值》中提到过的,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公司治理、改革转型,缺的绝不是正确答案,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何勇在二十多年前唱的“这个问题怎么这么的难啊,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我们缺乏的,其实是问题意识,是客观分析解剖事务后,提出真实问题的能力和条件。提不出好问题,要么是智商不允许,要么是环境不允许。
识别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在研究分析和理清事物来由去脉的过程。只要是做过真研究的人自然都知道,问题提对了,事情就已经解决了90%——你要知道自己真的错在哪了,你还会不知道怎么改吗?
再强大的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也只能大致指出目前所观察到的模式下可能呈现的一种或几种趋势。社会生活过程是众多变量的函数,而且大多数变量经不起任何尺度的衡量和检验。
因此任何关于社会模式运行的学说,都只能梳理出其观察视角下的几个关键变量,指出其可能呈现的趋势作用。没有谁能包打天下构建宇宙真理。
熊彼特又强调——预测病人会死亡,并不是说医生就希望病人死亡——就像他预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不是说他厌恶资本主义,预测社会主义一定到来,并不意味着他喜欢社会主义(虽然直至今日,我们一直都用虚伪的喜好来评价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他只是按照研究分析推导的结论来说话而已。
同样,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组织、这条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风险的,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厌恶这个国家、这个组织;成天说这个国家、这个组织伟光正的人,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这么认为。
熊彼特有一个名词用以说明这种乐于给观点戴帽子的思想形态——社会宗教。
熊彼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接否定——资本主义体制当然不可能持续,必将灭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演化趋势。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和运输方法,新开辟的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不断从内部革新其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的结构——注意,这种结构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由生产结构决定的市场结构。这个过程,被熊彼特称为“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
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就在于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重构。
在研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之后,反过来再看熊彼特这段著名的阐述,突然间才理解了他所指。熊彼特在解剖资本主义运作机理时,把马克思的危机经济学与黑格尔方法论分离开了,他同样运用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动力学方法——意识不断地超出自我,之后反观自我,创造世界,再回到自我——即所谓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国内大多数学人批评熊彼特把资本主义过程仅仅视为生产技术发展过程,其实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熊彼特非常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即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乃是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对旧有结构的破坏,就包含有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