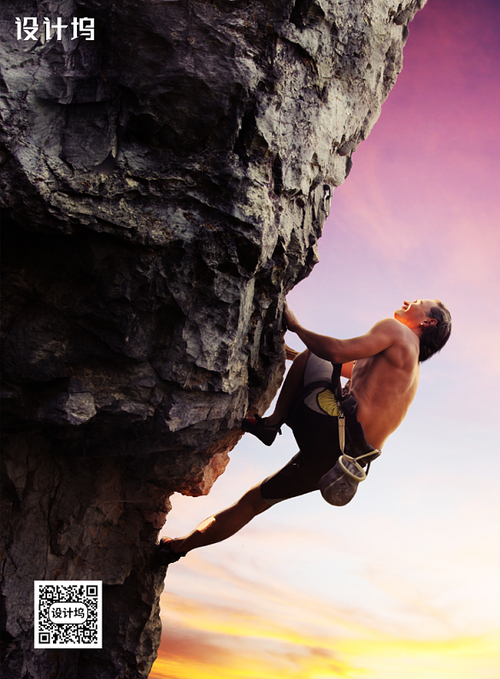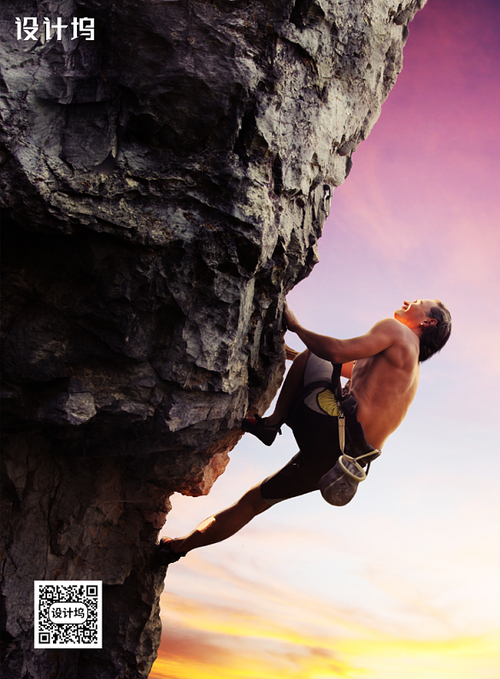
《喝火令》的摊破只是一个假设
为方便说明,先录《喝火令》范词于下。
喝火令·黄庭坚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见晚晴如旧,交疏分已深。舞时歌处动人心。
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
烟水数年魂梦,无处可追寻。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便愁云雨又难禁。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晓也星稀,晓也月西沈。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晓也雁行低度,不会寄芳音。
此词无他首可校。后段句法,若准前段,则第四句应作“星月雁行低度”,今叠用三“晓也”字,摊作三句,当是体例应然,填者须遵之。
关于《喝火令》词牌,有人倾向于用以下两种观点来衡量现实的创作。一是上下阙开头属于对仗句;二是下阙第四句遵循摊破原则。对此,我们有一些不大相同的看法。
一、上下阙开头不是对仗句
上阙开头的句子是:见晚晴如旧,交疏分已深。我们认为,这两个句子属于紧缩的转折复句,展开后应为以下样式:“(虽然)见晚,(但是)晴如旧;(虽然)交疏,(但是)分已深。”那么,这两个句子到底对仗没有呢?如果说字数相同的同类复句放在一起即算对仗,我们无话可说。众所周知,对仗应该要考虑词语的性质和句子的结构,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明确了。两个句子中,前一分句“交疏”与“见晚”可以对上,毋庸赘言。而后一分句“分已深”与“晴如旧”是否能够对上,还是有话可说的。“晴(名词)如(动词)旧(形容
词活用作名词)”是主——谓——宾结构,而“分(名词)已(副词)深(形容词)”则是主——状——谓结构,无论从词性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二者对仗关系不能成立显而易见。因此,这两个句子不是对仗关系。
下阙开头的句子是: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昨夜灯前见”的中心词是“见”,“昨夜”和“灯前”分别是“见”的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因此,“昨夜灯前见”是偏正结构。而“重题汉上襟”中,“重”是“题”的状语,“汉上”是“襟”的定语,整个句子主干由动词“题”和宾语“襟”构成动宾结构。动宾结构与偏正结构无法形成对仗关系。
二、摊破只是后人的猜想
范词附注中说:“此词无他首可校。后段句法,若准前段,则第四句应作'星月雁行低度’,今叠用三'晓也’字,摊作三句,当是体例应然,填者须遵之。”
“若准前段”,起首这个“若”字,是什么意思呢?翻阅《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对“若”字的解释有4个:①如,好像;②如果;③姓;④你。我们认为,最接近“若准前段”中“若”字的意思的是“如果”,而《现代汉
语词典》对“如果”的解释是“表示假设”,所以,“若准前段”,翻译过来,就是“假设准前段”的意思。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对“假设”的解释,共有3个:①姑且认定;②虚构;③科学研究上对客观事物的假定的说明,假设要根据事实提出,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成为理论。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范词的实际情况,即黄庭坚先生作品中“后段”的“句法”并没有“准前段”。为什么呢?第一,“准前段”只是“姑且认定”,姑且认定就是暂时认定,并不是最终结果;第二,“准前段”只是“虚构”,毋庸讳言,虚构的就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第三,“准前段”只是“科学研究上对客观事物的假定的说明”,即使这个假设是根据事实提出的,也要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能成为理论。
自宋朝黄庭坚以来,近千年的写作实践是否证明了“若准前段”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迄今为止,“此词无他首可校”。“此词无他首可校”如此掷地有声,只因为它是权威和专家们的终结性结论。这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在近千年来的《喝火令》写作实践中,没有一个作品能够达到或超过黄庭坚《喝火令》的境界,因而不能帮助证明“若准前段”这个假设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假设不能成为理论。
既然这个假设还不是理论,也就是“后段句法,若准前段”还不是理论,这就是说“若准前段”这个假设至今仍未成立。如此一来,需要以“若准前段”为条件才能产生的结果肯定不会存在,也就是说“则第四句应为'星月雁行低度’根本没有可靠抓手,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据此,下阕第四句中的所谓摊破,自然只是某些人的猜想而已。
既然这个假设还不是理论,也就说明了这个假设还在延续,当然就不能拿来指导现实的创作实践,那么,“填者须遵之”,到底要求填者“遵”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后人能够用来证明“若准前段”这个假设的只有黄庭坚自己的《喝火令》这一孤证,这显然成了自己证明自己,就算能够自圆其说,被证明的假设始终难以令人置信,反而让人生出许多疑问。比如,将“星”“月”“雁行低度”捏合成“行月雁行低度”的第一个人是谁?他是怎样知道黄庭坚是这么想的?黄庭坚当时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人看到了“星”“月”“雁行低度”等词句能够组合成“星月雁行低度”这样的句子,才提出了“若准前段”这个假设?“此词无他首可校”,是近千年没有诗人写《喝火令》,还是近千年来的诗人的创作水平不能达到或超过黄庭坚《喝火令》的水平?是权威或专家们的研究不到位,还是没完没了的厚古薄今在作怪?
综上所述,是否在上下阙开头两句对仗,是否在下阕第四句摊破,那完全是作者的自由。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喝火令》词谱并没有要求上下阙开头两句要对仗,更没有要求下阕第四句要摊破,因此,不能拿对仗和摊破作为标准乃至原则去要求和衡量后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