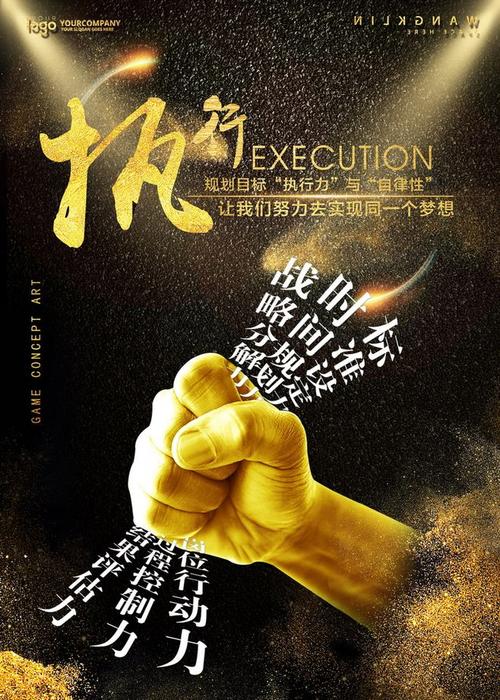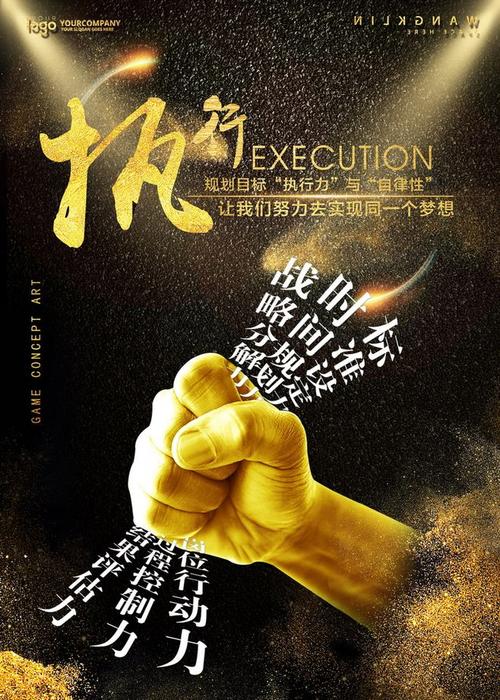
“结构分析”与中国画风格史的重构
——论方闻《心印》中的风格研究
张晓剑
艺术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或许是:确定基本的事实,如作品的断代、归属等问题;将基本事实归类或加以组织,即把基本事实构建成一个逻辑的序列,或如潘诺夫斯基所说,“使之纳入一个合理的‘有意义’的体系”(潘诺夫斯基撰,曹意强译,范景中校,《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史》,载曹意强主编《艺术史的视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第7页)。前者主要借助考证,而后者,更多解释意味——解释效力越强越说明其客观性。当然,这两者实际上相互渗透,许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循环:基本事实的澄清是属于解释的基础,反过来,解释的框架又往往成为确定基本事实的依据。方闻先生对中国画所做的风格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其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在带给我们启迪的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深层问题。
一、“视像结构”与时代风格
方闻的风格研究显然处于沃尔夫林开辟的传统之中。沃尔夫林曾在《艺术风格学》中提出了理解文艺复兴盛期和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五对范畴(有学者指出,沃尔夫林在20世纪的影响超过了之前的布克哈特和
李格尔,他的五组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工具盒‛,学者们借此更精练地理解艺术家用以获取特定效果的手段,以及风格在时间里的变化方式),艺术史由此被述为形式自律发展的历史,以致可以有一部“无名的艺术史”。方闻也试图勾勒出一部超越个体的、形式自律的中国艺术风格史。只是,沃尔夫林的风格图样得自西方艺术可靠的“代表作”,而中国画因为年代久远,面临着断代困难、真伪难辨等问题。方闻因此提出,要确定历史中的“基准作品”(‚基准作品‛的说法源于库贝勒,见方闻撰《论中国画的研究方法》,载洪再辛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第93─105页,尤其第103─104页)——这可以是无争论的传世作品,也可以是考古出土的无名作品;重构中国画的风格史,并以风格分析作为鉴定的依据。
方闻重构风格史的方法基础,是“结构分析”,及对艺术作品里形式要素的安排结构展开分析。这种方法,受到美国艺术史家夏皮罗的“风格”概念的启发。
在夏皮罗看来,风格的描述涉及艺术的三个方面,即“形式要素或母题,形式关系以及品质(包括一种我们不妨称作‘表现’的总体品质)”(夏皮罗撰,张戈译,《风格论》,载《美术译丛》1989年第2期,第5页,译文略作调整。另外见方闻撰,《论中国画的研究方法》,第104页注释12)。依此看来,中国传统画论显然只针对作品中的“形式要素”和“品质”:对不同名家笔下的山、树进行技法上的解析,或者对笔墨气韵进行鉴赏。
方闻认为,去确定和说明个人风格时,我们可以从其特殊的形式要素、母题和独特的表现性中入手,因为这些元素是体现个性的外在特征。但是,如果要给风格归类,即确定群体风格,则要从画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关系——入手。这是因为,“不管绘画中的形式要素、母题和技法怎样,在它们表现某种哲学或伦理观念之前,必先有轮廓、样式以及构图的问题”(方闻撰《山水画的结构分析》,载《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第108页)。换言之,在方闻看来,“形式之间的关系与视像构成(画面形式的含义及其组合的方式)”,最能体现“群体的特征”(方闻撰,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11页)。因此,要分析形式要素在画面上安排而成的“结构形态”,才能说明一个时代共有的风格,并据此说明风格的历史演变。(而这样的‚结构分析‛,恰是传统中国画研究最缺乏的工作。方闻因此批判了李霖灿先生以墨竹母题和按法分类来进行年代编排的传统做法,而对张大千根据手指与指甲的关系来说明敦煌壁画中画手的历史演变加以赞赏,因为后者无意中用到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见方闻撰《山水画的结构分析》,载《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第107─108页。)
之所以这样认定,乃是源于这样的预设:画面上所体现的“结构形态”,并不是艺术家本人可任意选择的,它实际上表现了特定时代里人们共有的“视像结构”,或说体现了那个时代视觉的限度。沃尔夫林说过:“每一个艺术家都在自己面前发现某些视觉的可能性,并受到这些可能性的约束。然而,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一切可能性。”(沃尔夫林撰,潘耀倡译,《艺术风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13页)方闻以“结构分析”来重构风格史,就建立在这个预设之上。基于此,同处一个时代的无名工匠与伟大画家对空间里的物象关系拥有同样的“看法”才是可以想象的。
在方闻看来,中国艺术家“再现”现实、创造错觉的进程,可以根据画面形式要素间关系的变化而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画面中的前景、中景、后景相互断裂,后来画中各序列被墨染和烟云所统一,到元初(比如赵孟頫的《鹤华秋色图》)出现连续的地面,各山水要素被更成熟的笔墨技巧融贯成一个视觉上可信的整体。(方闻撰,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21─23页)这是一段不断接近现实空间的历程。
二、探索本土视觉模式
方闻对中国绘画历史的这样一种粗线条式把握,尤其是从唐到元初的三阶段说明,犹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给我们极大的智性上的满足。其“结构分析”,不仅展示了一种相对客观的分析方法,而且给出了中国人的“视觉的历史”。
中国传统的绘画研究,多以直觉和体悟为主,用语形象而又精妙。但也因此显得偏于批评式的主观,欠缺学术研究所需的客观。方闻用西式的“风格”分析(尤其是夏皮罗的“风格”概念)来映照传统绘画研究,把原先中国画论里精妙但可能含糊成一团的说法给分出了层次,其研究实践提醒我们:在传统画论所针对的母题、做法、气韵之外,存在以“形式关系”为突破口来重构中国画风格演变的可能。把这
样一种针对视觉材料形式分析的方法用于中国画的研究,其意义是:从鉴定到艺术史写作,都要求超越主观而导向一定的客观和规范。
须知,艺术史能成为一门学科,有赖于对自身学科特性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成熟。沃尔夫林于此有重要贡献。他认为:“视觉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而揭示这些视觉层次应该被视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沃尔夫林撰,潘耀倡译,《艺术风格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3页)要解释视觉层次,就要从传记、文献回到可见的视觉材料展开形式分析,进而比较与分类。这样的形式分析抑制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任性,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正因如此,赫伯特·里德认为沃尔夫林试图使艺术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潘耀昌、陈平译《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里德(英译本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47─348页。)方闻在这点上秉承沃尔夫林的宗旨,他明确说:“风格判断与鉴赏能力作为知识的方式,不仅是维系生存和应付挑战所必须保护的,而且也是了解不同视觉语言的唯一手段”。(方闻撰,《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见《心印》
第246页。)
方闻想要以此探索中国人独一无二的视觉模式。他自己说,“我们研究‘视觉艺术语言结构’,要说明世界各文化都具有‘本土化’的特征;我们要用有系统、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来描述中国视觉艺术的视觉‘语言’、风格‘结构’,用以阐明其在风格上有它本土的特别文化思想上的‘看法’和‘内涵’表现”。(方闻
撰《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学术定位及及学科发展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第4期,第7─8页。)这是说,每种文化都会形成观看世界的特定方式,在绘画里都表现出独特的视觉模式,结构分析可作为基本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方闻的风格研究虽然在方法上西来的,但针对的问题却是“本土”的,即:中国人的视觉的历史是怎样的?方闻试图通过“结构分析”来说明,中国画在“征服幻想”的道路上拥有自身的历史,从唐到元所呈现的三阶段的“视像结构”完全是中国独有的。
三、反思:中国画与“再现”问题
方闻用以把握中国山水画史脉络的,其实是隐含着的两个观念——“再现”和“表现”:从7世纪初到13世纪晚期,是对于真实的“再现”,是“模拟形似”的不断挺进;从元代开始,在全面掌握了绘画的幻觉效果后,画家们转而借书法用笔来自我表现。中国画史因此是一个从“再现”到“表现”前后相续的过程。而为了探索中国人的视觉模式,方闻主要侧重“再现”理论以说明绘画是如何逐渐接近现实的,并据此建立起一套从唐到元初的历史叙事。但平心而论,这样的叙事显然是选择性处理的结果。我们一方面可能乐于看到方闻给出的“征服幻想”的三阶段历程,因为其高度概括性满足了我们理智上的需求,而且其纲要式的历史描述也确实呈现了中国画史重要的一个面相;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怀疑其过于概括以致丢失了某些真相。方闻自己所用的材料无疑很精到地说明了向“幻象”的一步步接近,给出了一个从唐到元的进步模式,但问题是,显然还有大量未必符合理论框架的材料被忽视了。也就是说,从唐到元初的绘画历史,用“再现”模式能够统摄吗?这样的模式固然提供了一个把握中国绘画史的框架,
但是否也模糊、掩盖中国绘画艺术以及绘画观念的精微和独特处?
在西方,基于模仿概念的“再现”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就将西方艺术的发展看做对自然的征服进程,这一直延续到印象派。
(在贡布里希看来,印象主义与当时的保守艺术家在艺术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争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完美地复制视觉印象,‘事实上,直到出现印象主义,才完全彻底地征服了自然’,以致一切皆可入画。见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536页。)这样的说法之所以在西方语境里能够成立,是因为对艺术与自然、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真实(真理)的关系在文明之初的希腊就获得了反思,而且“模仿”和“再现”后来也确实深入艺术家的意识。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时间里,西方绘画的主要目标是再现外在现实,“透视法”“明暗法”就是为视错觉的实现创造条件。
而在中国古代画论中,从姚最的“心师造化”到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再到清代松年所讲的“人之作画亦如天地以气造物”,关于艺术创作的主流观念是“师法造化”。所谓“造化”,主要指天地创造、化育的那种功能。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家要取法于“造化”本身,学习自然那化生万物的能力,可以说,他们很早就将艺术活动视为“创造”。(贡布里希对中国艺术的‚创造‛性有非常敏锐的感受。参见贡布里希撰《西方人的眼光——评苏立文的<;永恒的象征——中国山水画艺术>》,载洪再新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第373─376页。但我们要留意‚创造‛在西方语境里的基督教背
景,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艺术家的活动只是‚制造‛。)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艺术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心”的作用,这让中国人重视艺术“创造”中的精神因素,注重个人灵性的发挥(只是这种“人工”发挥应该像造化那样“自然而然”)。而中国画中的书法用笔,更为个体生命的表现提供了手段上的保证。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就已内涵了把创作行为作为个人“表现”的因子,唐代画家吴道子、张璪、王墨的创作体现了这点(参见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第23─25、198、204─205页。另见陈传席著《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37─40、50─54页),而北宋文人画,则更为明显和自觉。(在1992年出版的《超越再现》中,方闻提到,书法风格在北宋后期的士夫画里就已经产生,并说,士夫画‚预示了元代的文人画‛。)当然,宋代画家确实非常注重观察自然物象,但这样的观察不是为了简单“再现”视觉所见之外在现实,而是穷究自然内在之理,由此“再造”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世界。这种对创造性的重视,在后代更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