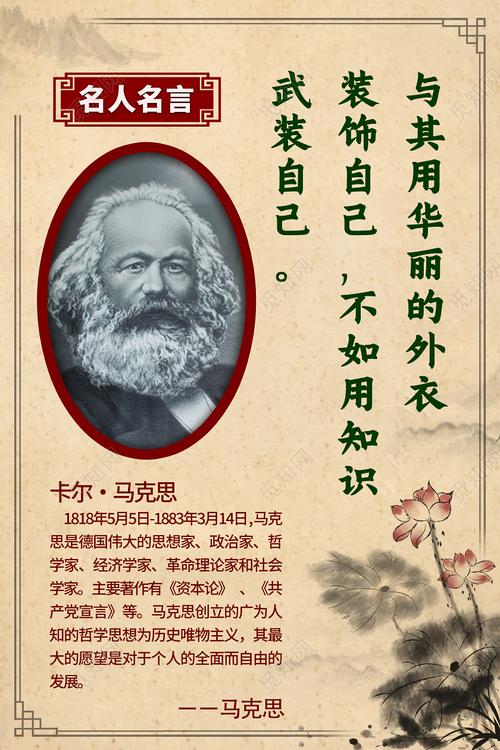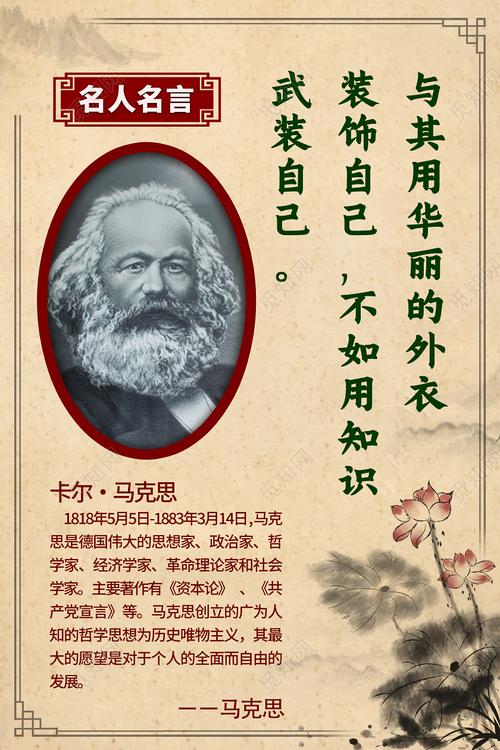
布鲁姆“诗学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的误读
胡宝平
(南京大学英语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哈罗德·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以文本互文性为基础构建起一套具有相当辩证意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互文观念使他超越了新批评的文本一元论和解构主义的意义空缺和文学史空缺等虚无主义倾向;但是将互文关系解释为斗争关系,把互文范围严格限定于两个文学文本之间,否定了文学发展特征和文本生成原因的多重性,使该理论陷入“语言的囚笼”。
关键词:诗学误读;互文性;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5)02-0091-04
Abstract:By dev elo ping his theo ry of poet ic misr eading,Har old Bloo m conceived a r emar ka bly dialectic par adigm o f literar y hist or y bad on the concept of int ertex tuality.T his concept enables him to tr anscend the N ew Cr itical co n-cept of t he tex t as an aesthetic monad and the deco nstr uctio nist idea of the abnce o f bo th meaning and lit erar y histo-r y.T o int erpret the int ertex tual r elationship mer ely as str ug g le and t o co nfine such r elatio nship str ictly w ithin t wo w
r itt en tex ts,ho w ev er,is to deny bot h litera 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 oduction o f liter ar y tex ts o f their natur e o f ov er-deter minedness,thus lea ding the theor y o f po etic mispr isio n int o the“pr ison-ho u o f lang uage”.
Key words:po etic misr eading;int ertex tuality;liter ar y histo ry
哈罗德・布鲁姆(Har o ld Bloo m)的“诗学影响”(亦称“诗学误读”)理论曾被伊格尔顿(T er r y Eag leton)誉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大胆最有创见”的文学理论(Eagleto n,1983: 186)。可如今,这套理论和论述该理论的四部曲——《影响下的焦虑》(T he A nx iety of I nf luence,1973)、《误读图释》(A M ap of M isr eading,1975)、《喀巴拉与批评》(K abbalah and Criticism,1975)和《诗歌与压抑》(P oetry and R ep r es sion, 1976),以及《抗争:建构修正的理论》(A g on:T ow ar ds a T heo-ry of R ev isionism,1982)、《打破形式》(“T he Breaking of Fo rm”,1979)等其它著作因其广博与艰深而被奉为阳春白雪,所以也逃不过曲高和寡的命运。回首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辉煌成就,文学史理论这一领域相比之下略显冷清。而布鲁姆以文本互文性为基础,提出“诗学误读”理论,来诠释“现代”(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发展史,其含金量不容低估。本文将分析布鲁姆在进行理论构建时如何为自己需要而有意“误读”后结构主义之互文性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文学史观上的得与失。
互文性是“诗学误读”理论的基础。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史呈现出一派斑驳陆离的景象,要想从中
找出一条贯穿若干世纪、牵系众多作家的线索,就必须在单个作家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进而以细的线条拧成粗的绳索。布鲁姆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以互文性为基础着手进行理论建构,而第一步就是以互文性确立自己的文本观。
互文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的一个批评概念。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和同时代的其它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其它文本进行吸收和转化的结果。在《符号学》中,她指出:“一首诗的所指总是以其它的话语为参照(或与它们相关),因此在任何一首诗的表述中可以读出大量其它的话语”(K rist eva,1969: 255)。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她又说:“不论一个文本的(语意)内容是什么,这个文本作为一种表意行为总是预设了其它话语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自一开始就处于其它文本的统辖之下”(K risteva,1974:388-9)。总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仅是一个巨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与许多其它文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确然,从后结构主义的符码“延异”观出发,一旦认定文本不是既定的存在物,而是因“延异”生成的构造体,那么互文性就成了文本的必然特性。
布鲁姆坚持与克里斯蒂娃相似的文本观,从而为描述文学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于他而言,任何诗歌都是对先前的一首诗(precur so r po em)的误释,因而是“三位一体”的:它自身作为一个文本存在,其中设定了一个先前文本的存在以及不可避免的解读环节,且解读有着双重所指——即是行为,又是结果。在《诗歌与压抑》中,他说:
诗歌不过是一些词,这些词指涉其它一些词,这其它的词又指涉另外一些词,如此类推,直至文学语言那个无比稠密的世界。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它诗歌互文的……
诗歌不是创作,而是再创作;就算强势诗是一个新的开端,亦只是再次开始。(Blo om,1976:3)
类似的陈述在四部曲中多次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所说的“诗人”不独指通常意义上的“诗体写作者”(v er-w r it-er),而是泛指所有的作者;同样,他所说的“诗歌”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还兼指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布鲁姆不厌其烦地重申他的文本观,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与此前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思潮划清界限。于新批评者而言,诗歌几乎成了超脱尘世一切事物、偏安一隅、独立自在的审美一元体——它是布鲁克斯心中“精制的瓮”,是韦姆塞特心中的“词语之象”。布鲁姆对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观颇有微词,他一再强调“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试图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理解’的不成做法”(Bloo m,1973:43),甚至忿忿地指出:“没有哪个观点比如下这一‘常识'性的东西更难消除了:诗歌文本是自足的,其意义不用对照其它诗歌文本就能确切弄清”(Bloo m,1976:2)。从否定
文本自足而代之以一种“三位一体”的文本观,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理论的矫枉过正之处,我们也可看到布鲁姆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超越形式主义”所作出的努力。然而,布鲁姆对新批评的纠偏也不彻底。他只是对新批评的文本一元观发难,而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观,他在论述中始终坚持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相似的非历史的立场和内在研究方法(这一点在下文会着重论述),此中亦足见新批评理论影响之深远。
不过,布鲁姆毕竟以互文性为基础归纳出一条文学发展规律,这终究是新批评者们无可比及的。杰弗逊(A nn Jeffer-so n)在《现代文学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新批评理论逃避文学史问题(Jeffer son and Ro bey,1982:11)是有其道理的。新批评诸理论家中,惟有韦勒克(Ren W ellek)偶有论及文学史问题,但对文学史也是持怀疑态度。在《文学史的衰落》一文中,他承认文学有历史的特征,同时指出文学史要对文学作品作价值判断,而作价值判断就要解释作品的“审美特征”,他认为文学史难以做到这一点(Wellek,1982:64-77)。单从韦勒克的文章就足以发现新批评在文学史问题上的症结所在:新批评只关注解读个体文本,关注个体文本的审美特征,它所看到的永远只是独立的点而不是连续的线和面。就此而言,在新批评之后以及整个“文学史衰落”的大气候中,布鲁姆能够以一种历史的(此处指关注发生、发展和过程)眼光透析文学,实为文学史研究和批评一大幸事。
众所周知,互文性对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不少评论者把布鲁姆与他的耶鲁同事德曼、米勒相提并论为解构主义者,正是因为他对互文性的运用。布鲁姆确实与解构主义者们有一些相同的主张,譬如说他也认为写作与阅读的背后是复杂的替换(substitut ion)、转义(tr ope/t ro ping)和防御(defen),也认为要以联系的眼光看待文本,将它放到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中去衡量,也认为作者并非意义的创作者等等。然而,正如哈特曼谈到的,布鲁姆还算不上一个解构主义者,有时甚至还是反解构主义的(Har tman, 1979:v ii-ix)。这突出表现在两点——而这两点正是布鲁姆有意“误读”互文性的地方。
其一,他赋予了互文性独特的动态意义。在他之前,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人都视互文关系为静态的、悄无声息的吸收和转化,甚至是匿名的引用(Culler,1981:108)。布鲁姆在分析过程中巧妙地引入了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形象和犹太教创世纪神话中魔鬼撒旦的形象为后起作者作比喻,从而为文本和互文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后起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姗姗来迟”(belatedness),因而注定不能是立言者,他要自强、独立,就要如撒旦一样集结力量与上帝进行殊死搏斗——“他选择了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受惩罚,去探索在惩罚之下尚可有多大作为。否则他只能懊恼,接受一个全然不同于自我的‘上帝’而彻底地无所作为”(Blo om,1973:21)。于是,他在作品中以六种修正式(rev isio nar y ra tio s)对前驱作品进行误读,从而象征性地、仪式性地杀死前驱。由此可以发现,互文性在布鲁姆诗论中表现为紧张的对峙、敌视和斗争关系,文本也不再是静态的语言符号的聚合体,而成了充满愤怒和喧嚣的战场——在这点上,布鲁姆无疑是对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发展。推及文学史,意义也不同寻常。首先,他再次证明: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史演进与社会乃至生物界的发展一样,动荡甚于平静,其中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其次,文本并不是在独自跳舞,并不是德里达所言的自由游戏。“诗学误读”论述的是“现代”文学,布鲁姆提出影响、焦虑和误读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有一个重要前提(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明,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十分明显):作者们对于新颖、独到孜孜以求,其原动力来自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诗学误读”将作者的自我意识抬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从而为“影响——焦虑——误读”这个三元模式找到了立足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恰逢其旨,可资一用。布鲁姆借鉴了弗洛伊德对家庭罗曼史、焦虑的阐释,尤其是他的人格结构模式,但对它作了修正。
在布鲁姆的诗人人格结构中,本我是前驱作者(按弗洛伊德的模式则应该是超我),自我是诗人自身,超我则是死亡(即无权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诗人)。影响不可避免,受人影响就意味着取人之有为己所用,所以就会有负债之焦虑,有己不如人的焦虑——影响因而成了“摧残性力量”,成了“灾难而不是福音”;而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性焦虑,同时又是一种强制式神经官能症的开始。这种神经官能症也可以称为对人格化超我——死亡的恐惧”(同上,58)。一面是前人的光环,一面是死亡的威胁,且二者成正比存在,后起者要成为真正的诗人(保全自我)就必须抗争前人(压抑本我、抹杀本我)。如上所述,文本之中有作者的主体意识,有作者的焦虑,还有作者的权力意志;互文关系并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还有作者的主体功能内化在当中。最后(也许正是布鲁姆的良苦用心所在),他提醒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不要将注意力仅仅放在业已形成的以结果态存在的文本,而要放到文本形成的曲曲折折中,去寻求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
其二,布鲁姆对互文性范畴作了严格的限定,使文本意义有了归属(尽管这一做法本身不无隐患)。我们知道,互文性标示的是文本之至为广泛的交涉状态,它意味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与整个文学传统以及广泛的话语域之间的关系”(Fr ow,1986:128),而且这种关系有共时的,也有历时的。从文本的互文性出发,解构主义者们象剥洋葱一样将文本一层一层地剥下去,旨在向人们展示文本意义的虚空——它是不定的,是能指的无常游戏。例如对德里达来说,语言恰如一张布满差异性“痕迹”的无限延异的巨网,无常是意义的劫数,因为“世界本身的游戏”——任何文本总是处于漫无涯际的语境关系
网中。德曼则从语言的隐喻特征出发,指出意义理解的替换、转义本质,探求文本意义犹如掉进无底深渊。总之,如米勒所言,“我们传统中诸如文本之类的任何文化表达,其意义都是不可确定的”(M iller,1954:54)。承认文本存在某个需要或可以进行解释的现实的“终极”、“中心”或“意义”是“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误区,应该被否定、推翻掉。这样一来,文本的内在统一、连贯、自足成了破灭的神话,任何以整合为目的的阅读和阐释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布鲁姆要为解构主义打破沙锅解构到底的作法纠偏,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给互文性范围划明界限。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只与另一个文本发生关系(intra tex tua lit y)——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一首“自身之外”的诗(即被误读的前驱作品)。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布鲁姆此举意义非同小可。
首先,他恢复了文本意义的重要地位,重申意义“在场”,从而避免了解构主义理论之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弊端,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人们意识深处对于整合、中心和意义的需要。不妨说这是对解构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一
重要原因,批评家博格兰(R obert de Beaug rande)称布鲁姆为“后后结构主义者”(po st-post-st rutura list)(de Beaug rande, 1988:303)。其次,将互文关系严格限制在两个文本之间无疑是肯定了文本有一个起源点和终极点,它使我们可以更方便地从历时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当然这里并不是排斥共时角度),进而可以重建文学发展史和文学传统。对于德里达、巴特等解构主义者来说,“史”的观念是他们要颠覆的对象之一,因为无涯的互文关系表明谁都不是最初的立言者,文本是能指的游戏,它是“不及物
”的,没有外在参照和指向的。德曼则以现代性与文学史之间的对立共存质疑文学史的可能性: 我们当前更为关注的是:能否相信象文学这样一个本身自我矛盾的实体具有某种历史。就目前的文学研究状况而言,这种可能性还远未有定论。一般都认为,实证主义文学史,因为把文学当作经验材料的集合,结果成了非文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对文学进行内在解释的都宣称自己是反历史或者非历史的,却常常预设了某种历史观的存在,只是批评家们未意识到而已。(de M an:
1983:162-3)
最后他指出,视文学史为文学“起伏运动的历时叙述”显得难以成立。布鲁姆以比较分析文学序列中零星的片段着手,最终让文学回归历史(文学自身的历时发展),这是他又一个超越解构主义的地方,或者说是他为修正解构主义之“彻底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尚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布鲁姆在文学史与意义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强调“一首诗的意义是另一首诗”表明了前驱文本与后起文本的影响关系,同时暗示了一种(他本人提倡的)阅读和批评文学的方法——将文学阅读、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布鲁姆曾宣称“诗学误读”是一套“实用批评理论”,说它是新的阅读方法论和迥异于前人之“文学伪史”(literar y pudo-histo ry)的“真正的文学史”,到此为止,他的说法本身尚不算太谬。
布鲁姆以互文性为工具超越了新批评的一元论,超越了解构主义的意义空缺和文学史空缺等虚无主义倾向。但是他将互文关系解释为斗争关系、对互文性范围作严格限定等“误读”行为也导致一些难以避免的悖谬之处。
不妨再回顾一下布鲁姆的推理逻辑:因为影响是必然的,所以产生焦虑心理是必然的,进而防御机制和斗争是必然的。这与他有关文本的两个说法是一致的:一是“文本不表明克服了焦虑,而就是焦虑本身”(Blo om,1973:94);另一个是“文本是血腥的战场,真正的力量在上面为不被湮没这一唯一值得一博的胜利、为使自己超凡入圣而斗争”(Blo om,1976:2)。这也就是说:互文关系中的焦虑和斗争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后起者生于一个业已形成的传统中,因而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即后起文本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互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影响之下是否必然会有焦虑和斗争?“现代”诗人是否时时刻刻都有着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末日来临感?还有,布鲁姆所说的“强势”诗人是否都一定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忘恩负义”?众所周知,互文性包含了引用他人之语和引用典故等等,现代诗人有时会很乐意地套用前人语句或某些用法且可能不作丝毫变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实即使有所变动也不一定是害怕被说成拾人牙慧,而只是上下文的需要;再如在戏仿手法(par ody)里,作者对他人的滑稽模仿大多是为了揶揄、讽刺的需要,而与焦虑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看来,互文关系必然是斗争关系这一设想就岌岌可危。
布鲁姆的重要论点——任何一首诗都是对前驱诗的有意误读,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后起文本与其亲本的先后关系;(2)后起作者对亲本的认知状况;(3)后起文本是过程态还是结果态;(4)亲本的惟一性;(5)亲本的排他性、纯粹性,即它只限于文本,而与社会、历史、作家生平等等外在因素毫无关联。在这五个问题上,他的论述有时出现抵牾之处,有时分析得不到位,同时又有些说法本身有待斟酌。
第一、一旦影响成为互文关系的主体,则被后起文本误读的文本必须是早先生成的,因为影响(influence)从“流入”(in-flux)这个意义上讲必须是以施与者事先存在为前提。然而,布鲁姆明确指出,亲本可能是“一首从未被写出的诗——即一首理应被该诗人写出来的诗歌”(Blo om,1973:6),这一点颇令人费解。面对着高高在上的前驱作者和文学经典,后起者可以有姗姗来迟感,但是具体到一个文本,若它尚未形成,来迟感与相应的焦虑就失去根基。布鲁姆的著述和耶鲁学派其他诸大家的一样,都有大量的文本分析,但他没有(估计也不能)提供一个实例为这一论断做说明。
第二、布鲁姆在实例分析中列举了大量相似或相关的意象以说明后起文本与其亲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其间却把作者放在一边,始终没有道明后起作者在创作一部作品之前是否了解亲本(或许不道明就是指两种情况都有)。其实,若了解亲本,则产生焦虑进而有意误读是可能的,但是后起作者为了与前人相区别,他或她的文本可能与亲本毫不相似。这样一来,布鲁姆认定的亲本可能实际上并不是亲本,且他的误读图式也很可能难以适用,他提出的后起作者必须经过六个修正式所代表的六个阶段或其中某些阶段就难以成立。若后起作者不了解亲本,则是否会有焦虑和误读行为都颇为可疑,我们也很难想象误读行为的假想敌是什么样子。布鲁姆习惯于在文本与作者心理之间游移,忽此忽彼,结果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点涉及文本生成过程之所在。为了揭示文本生成的复杂背景,布鲁姆从结果态的文本出发,将其分解成一些具体的概念、意象等等,进而与他认定的前驱作品的某些部分建立联系,同时指出偏离和
差异的“痕迹”,最后将这些“痕迹”串联起来,其结果就被当成文本及意义形成的过程,这无形中是将文本及意义形成的过程与结果混同。其实文本生成的过程——确切说应该是作者写作的过程,实质是作者的思维与情感活动过程;而意义形成除受文本的制约外,还与读者的接受与反应有着密切关系。客体文本间的差异何种程度上能反映作者的思维远无定数,因为文本间的差异与作者的心理本身都是变数(尤其是后者)。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布鲁姆只能在文本与作者的心理两端游移。他的分析过程更多的是拿误读图式套在具体文本上,将作者的思维简单化为求异思维,将文本生成的复杂过程压缩为单纯制造差异的过程。
第四,亲本的惟一性。正如布鲁姆所云:“诗源于对自由的幻想”(同上)。后起作者是没有多少自由可言的,他们生于一个既成的传统之中,在其熏陶中潜移默化。这也就意味着互文性的范畴至少应该包括整个文学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影响一首新作的东西完全可能源出多部前驱作品。就文学生产来说,作品的文学性与其它各种体裁、风格的作品,与整个文学发展中诸多作家的创作手段、形式、素材和方法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布鲁姆的分析象医学上通过血液检测来判定父子关
系一样明确地断定文本间的父子关系,但文学毕竟不是生理学、遗传学,而且前驱文本与后起文本之间到底是父子关系抑或更多的是师生关系?毕竟,一个人只有一个父亲,但可以有很多老师。
第五,亲本的纯粹性、排他性。在布鲁姆的论述中,互文性“降格”了,文本只是内在的与另一个文学
文本相关。其实,任何作品的“组织”(姑且借用一个新批评的术语)不只是一些概念、意象、韵律等等,还有典故、题材、人物等等,这些可能更多地来自历史和现实生活。而互文关系的最终领域是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艺术乃至风俗人情等诸多因素),作品是文化的积淀,是多重话语的结晶。因此,要把文本放到宏大的文化场中去考察。布鲁姆继承了新批评的内在研究方法,将文本尊为绝对的上帝,文学成了一块与世隔绝、自我观照的圣地,写作者因之成了超脱红尘的僧侣,心中只有先贤的经典。尽管布鲁姆亦声称“最伟大的诗人也会受到诗歌领域以外的影响”,但他关注的始终只是“诗人身上的诗人,即土生土长于诗歌领域的自我”(the poet in a poet,or the abor ig inal po-etic lf)(同上,11)。结果,他的分析象是在语言的囚笼里散步,文学的概念被缩小为文本,最终作品生成的过程被进一步简单化,文学史沦为单维的文本史。
上文在文学史理论框架内讨论了“诗学误读”对互文性的运用,指出了该理论与新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共性、它突破和超越前二者的地方以及它作为文学史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其间提及布鲁姆还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其实布鲁姆的“拿来主义”绝对有名,且拿来之后都用得得心应手。从“诗学误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响,如思想家尼采,原型批评家弗莱(N or thr op Fr ye),美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曼和哈特曼,精神分析界的后起之秀霍兰(N o rman Holland)、菲德勒(L eslie Fiedler)和兰柯(Ot to R ank)等等;可以看到犹太教传统、希腊古典神话在论证过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所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布鲁姆的诗论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反过来,“诗学误读”为我们观照原
型批评、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等也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见解。如果说布鲁姆及其诗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还只是一个鲜有论及的话题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课题了。
参考文献
[1]Bloom,Har old.T he A nxiety of I nf luence:A T heory of Poetry
[M].Oxford:Oxford U nivers ity Press,1973.
[2]Bloom,Harold.P oetry and R e p ression:Rev isionism f r om B lake to
Stev en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 s,1976.
[3]C uller,J onathan.P ursuit of S ig ns:S emiotics,L iter atur e,Decon-
str uction[M].New York:Cornell Univer sity Press,1981.
[4]De Beau grand e,Robert.Cr itical Discour :A S ur vey of L iterary
Theorists[M].New J ers ey:Ab lex Publis hing Corporation, 1988.
[5]De M an,Paul.B lindness and Insig 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 iticism[M](2nd ed.,revis ed).M inn eapolis:U-niveristy of M in nes ota Press,1983.
[6]Eagleton,T erry.L iterary T heory:A n I ntroduction[M].M in-
neapolis:University of M inn esota Press,1983.
[7]Frow,John.M arx ism and L iterary H istory[M].M as sachu tts:
Harvard U nivers ity Press,1986.
[8]Hartman,Geoffrey.Preface.Harold Bloom,et al,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M].London:Rou 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9]Jefferson,Ann.Intr od uction[A].In Ann Jefferson and David
Robey(eds.).M od ern L iterary Theory:A Comp arativ e I ntroduc-tion[C].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 td., 1982,1-15.
[10]Kr isteva,Ju lia.L a Rev olution du lang uage p oetique[M].Paris:
Seu il,1974.
[11]Kr isteva,Ju lia.S emiotike:Rec herches p our une manaly[M].
Paris:Seuil,1969.
[12]M iller,J.Hillis,T he L ing uistic M om ent:Fr om W ord sw orth to
Stev ens[M].Prin ceton:Princeton U nivers ity Press,1954. [13]Wellek,Ren .T he A ttac k on L iter ature and Other E ssay s[M].
Chapel Hill:T he U nivers ity of North Carolina Pr ess,1982.
作者简介:胡宝平,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 2004-09-29
责任编校 延 仁
扎根黄土地 热血铸辉煌
——《外语教学》走特色化办刊之路
《外语教学》系西安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外语类学术期刊,1979年创刊,1987年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1999年发行突破3000册,2000年突破4000册,2001年发行4800册,2002年以来,《外语教学》每期发行5500册,目前已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外语学术期刊之一。
《外语教学》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连续四次被评为中国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近年来,《外语教学》先后获“陕西省高等学校十佳学报”、“陕西省高校学报一等奖”、“首届全国优秀科社学报”、“第二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科社学报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殊荣。
2004年7月14日-15日,《外语教学》编辑部又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行、清华大学外语系的专家教授进行交流与座谈,受到了北大、清华专家教授的热情接待,他们充分肯定了《外语教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了该刊对全国高校外语教学与科研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对刊物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外语教学》编辑部此行的目的是学习大刊名刊的办刊经验,了解作者、读者的想法与要求。这对于刊物找准定位、提高质量、突出特色都大有启发。通过北大取经,清华问路,要达到“突出特色、繁荣学术”的更高目标,力争《外语教学》再上一个新台阶。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外语教学》将秉承自己的办刊理念,实行开放办刊,苦练内功,为社会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力争为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西外学报》记者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