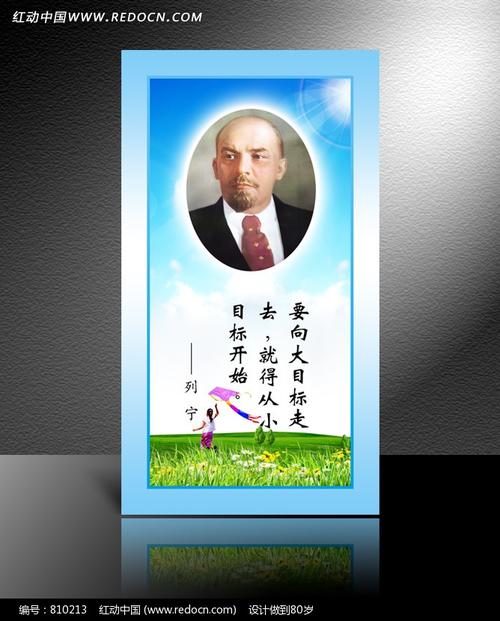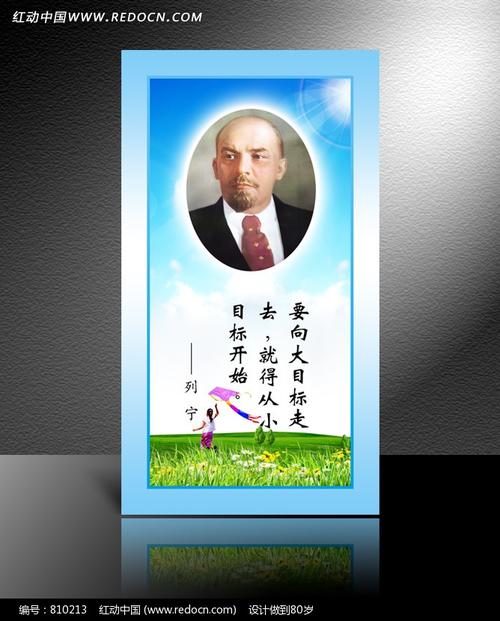
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雷平阳长诗《祭父帖》的互文性解读
摘要:雷平阳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不可或缺的诗人,行走在云南的大地上,书写着故乡的山川万物,乡愁和亲人成为其诗歌创作中独特的文化符号,其中有关父亲形象的书写更是独具匠心。长诗《祭父帖》是乡村孝子送父安葬的一首泣血之作,描写了从逝世到入葬的整个过程,回忆了父亲卑微苦难的一生。互文性又被称为文本间性,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像是宏大编织网中的一个“结”,与其他文本相互影响,彼此依赖。从这一角度对《祭父帖》进行分析可以增强文本间的相互阐释,更有助于对诗歌内涵的把握。诗人书写饱受时代沧桑的独特父亲形象,其笔下的亲情有一种彻入骨髓的感伤与悲愤,透出历史和时代之丧的力量感。
关键词:《祭父帖》;互文性诗歌;父亲形象
《祭父帖》是雷平阳创作的叙事长诗,2009年发表于《边疆文学》,后被《人民文学》转载,荣获华语传媒年度文学大奖。全诗三百余行,情感真挚热烈,一个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历经极“左”年代社会动荡苟且偷生的疾首之痛、包产到户后憧憬未来的梦呓狂欢、晚年生涯中的老年痴呆、最终归宿于黄土,时代造成了父亲的贫穷和卑贱,然而时间却无法泯灭其所
承受过的苦难,正如诗歌题记所言:“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使用互文性理论深入研究发现,《祭父帖》这一文本不仅与社会历史存在互文,而且还与诗人创作的其他文本存在动态沟通,如《奔丧途中》《与父亲书》《运往天国的石头》《少年筑墙记》《父亲的老虎》《清明节,在废墟》、《昆明的阳光》等作品。通过对文本进行互文性分析,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作品所传达的主题以及更好地把握诗人蕴藏其中的情感,使我们能够在《祭父帖》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中来解析该文本的功能,以及整个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上世纪60年代末,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她在《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一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互文性是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的互文,主要倡导人是克里斯蒂娃和其导师巴特,认为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具有互动作用,二者存在动态沟通的互文关系,在《祭父帖》中,诗人在深情回忆父亲往事的同时,也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从而形成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复现;狭义互文性是由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热奈特所主张的,任何文本都具有互文性,都是作者对其他文本碎片化的编织、组合,这种关系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方式,如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文本内部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相互派生。在本文中《祭父帖》与其
他文本所存在的狭义互文关系,是在诗人雷平阳所创作的诗歌内部来进行分析,在文中表现为文本与文本整体的互文、以及文本间细节的互文。总体而言,在诗人雷平阳描写父亲的诗歌中,《祭父帖》无论在情感还是内容上都独树一帜,一家独大,因此在本文中将其作为主文本,从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与文本、文本与文本细节的互文三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
一、文本与社会历史的互文
在《祭父帖》中,诗人在回忆父亲往事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文中对社会现状的描写向我们揭露具体的历史,社会历史被写进文本,而文本也更好的反映社会历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让上至领导阶层,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父亲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受到身心的双重摧残。文中回忆父亲卑微的一生,所经历的苦难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父亲参加“万人大会”,会后需要传达会议精神,“他”是文盲,讲话也含糊不清,万人大会上听来的文件,憋红了脸也只讲出三句半,忽而听见窗外咳嗽,吓得魂不附体。诗中在回忆父亲所经历的苦难的同时也真实再现了文革时期残酷的社会现状,万人大会是文革时期的标志性活动,其目的
或是批斗或是学习文件,学习后还须强制性的传达。在那个混沌的年代即使是父亲这样有口齿缺陷的人,也无一例外,甚至还会监督是否真正的“完成任务”,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活在透明的屋子里,说错一句话或许就会面临残忍的“批斗”,诗人向读者再现了那段让人痛心的历史,这种极富时代性的描述将文本和社会历史融合在了一起。
又如文中诗人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国家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拥有自己土地后的兴奋与狂欢,历史的一幕跃然纸上。一九八二年,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展开了,农民破天荒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地一片盎然,万物复苏,“就连水里的鱼虾、青蛙,地下的石头、耗子、深埋的白骨都跳了出来”,对一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的父亲而言,这更是一个如“范进中举”般的天大的喜讯,他和几个老哥们提着酒来到田野庆祝,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下酒菜不是别的,而是平平无奇的泥土,但这足以让他们欢呼。“泥土下酒”这是多么荒诞的一幕,但却生动地再现农民分到土地后的梦呓狂欢,同时也说明父亲卑微的命运不是偶然的,具有普遍性。那是一个贫穷、恐惧、生命被压抑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都如父亲一般背负沉重和苦难。
总而言之,在《祭父帖》中社会历史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文本中,社会历史被写进文本,而
文本也更好的反映社会历史,父亲所历经的磨难与社会历史彼此交融息息相关,时代造就父亲的卑微,而父亲种种卑微的表现也更好的反映了时代,这深刻体现了广义的互文性,任何文本它总是与社会历史分割不开,它总是受某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二、文本与文本的互文
文本间的互文是诗歌整体的互文,这种互文方式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不同文本是在同一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一首诗歌的创作是以另一首诗歌的创作为背景;一首诗歌是针对另一首诗歌中某件事延伸而创作。在雷平阳的关于父亲的诗歌创作中,《祭父帖》独挑大梁是研究的主文本,而紧随其后的有《父亲的老虎》《奔丧途中》《与父亲书》《运往天国的石头》《蓝》《清明节,在废墟》等作品,从题目不难看出,这些诗歌都是在诗人父亲离世后,诗人写作缅怀父亲的《祭父帖》一诗后所延展出来的。
其一不同文本是在同一背景下进行创作的,如在《蓝》中诗人写到“父亲死去才两月”;又如《清明节,在废墟》里所写“好像我死去多年的父亲”。这两首诗中都有明确的创作时间线索,第一首诗是父亲离世两月时所作,第二首诗是父亲去世多年而作,而《祭父帖》创作于父亲刚逝世时,显然它们的创作都是处于同一具体背景下,都是以父亲的离世为大背
景而创作。
其二一首诗歌的创作是以另一首诗歌为创作背景。《祭父帖》是围绕父亲的安葬为中心事件而进行创作,无独有偶,《少年筑墙记》同样讲述了一个少年安葬父亲的故事。 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少年薛笑非,某一天从山上放牛归来后发现父亲已经去世,在悲痛过后他决定振作起来安葬父亲,让父亲安息于黄土,但祸不单行,没有地没有棺木,无可奈何,只能在自己住的牛棚里砌了一堵墙,墙的这边是自己,墙的那边是父亲。这两首诗都是以儿子安葬父亲为故事中心,这样的创作不是巧合,是诗人在写作《祭父帖》后,又以《祭父帖》为创作背景,使用改编、重组等互文手法而创作了《少年筑墙记》。
其三针对一首诗歌中的某件事延伸而写作的另一首诗歌。如针对《祭父帖》中写到“喊一声爹,他没听见,又喊一声爹,他掉头看了一眼,掉头不理/也就是那一天,我们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诗人用生活中简短的一幕向我们告知了一件事: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针对此处诗人创作了《与父亲书》。这首诗主要写父亲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但相比前者的寥寥几笔,后者就写得更为详细具体一些。父亲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历经波折找回父亲后,“我们”在他随身衣服的小口袋里写上家人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的守护,担心再
次走丢。作为子女, “我们”只能强忍着悲伤,父亲不认识“我们”,“我们”就一次又一次与父亲相认, 虽然现实迫使接受患上老年痴呆的事实, 但在心理情感上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场噩梦,这件事犹如股椎心之痛。《祭父帖》中短短的几句话告知父亲患上老年痴呆,诗人便延伸开来创作了另一首以此为主要事件的诗歌,互文关系显而易见。
三、文本与文本细节的互文
1、父亲形象的互文
《祭父帖》里出现了一个患老年痴呆的父亲,而《与父亲书》中同样也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父亲,这种互文方式是极为明显的。但除老年痴呆的父亲形象外,《祭父帖》里还有因时代风云变幻而时刻胆战心,惊恐惧不安的父亲形象,贫穷、卑微、战战兢兢。《祭父帖》里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懂当时的社会为什么动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自知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没有资格去学习“万人大会”的文件,更无力去做“万人大会精神”的传达者。尽管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父亲还是时时恐惧如惊弓之鸟般的状态,每日提心吊胆的活着,随时做好挨批斗的准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屋外一声咳嗽,吓得脸色大变”,自导自演了一场荒诞的“家庭审判戏”。“找了一根结实的绳索, 叫我们把他绑起来,爬上饭桌,
接受历史的审判/他赖在上面, 命令我们用污水泼他,朝他脸上吐痰”。因为害怕噩梦的到来,因此在噩梦还没到来时就让自己提前处于噩梦中,像自己做错事必须接受惩罚似的“折磨”自己,仿佛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心安,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时代是这幕戏的总“导演”。政治氛围给普通小人物带来的恐惧已经深入到灵魂深处和潜意识,表面行为的荒诞暗示了内心深处藏有无止境的恐惧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