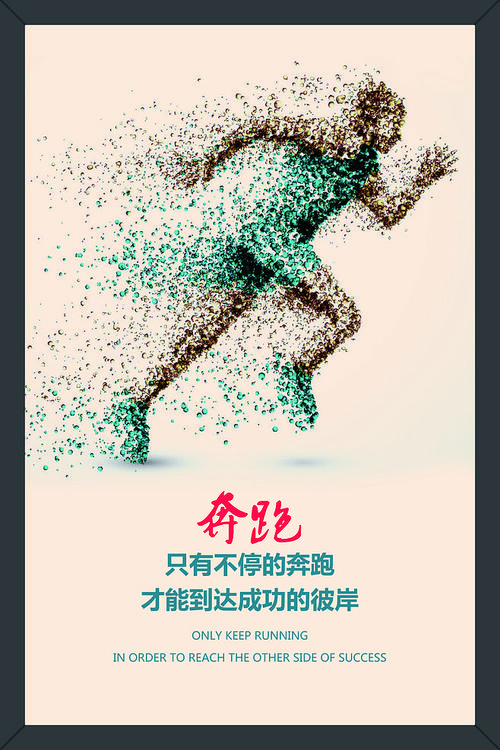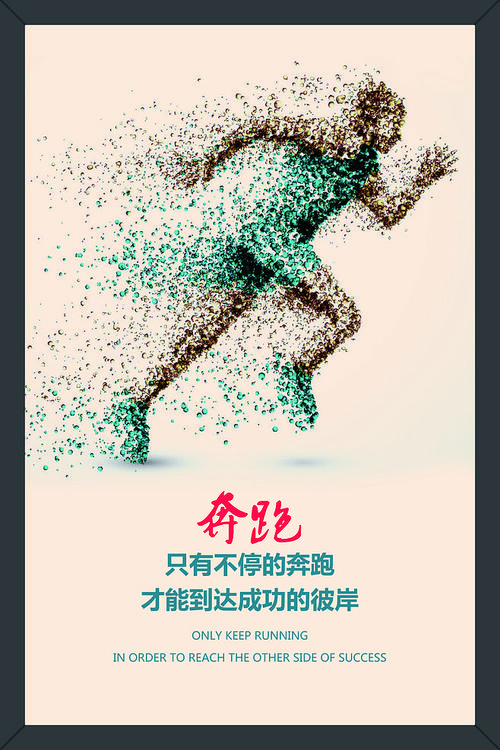
解读《斯通与骑士伙伴》的后殖民互文性
摘要:《斯通与骑士伙伴》是奈保尔唯一一部与第三世界毫无关联的小说。这部小说与英美经典文本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同时具备了“模仿”与“改写”的双重含义,模仿是对语言与文体的延续,改写则成为颠覆英美文学传统的有效手段。奈保尔“戏仿者”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在小说的互文性中得到确定。
关键词:《斯通与骑士伙伴》后殖民互文性模仿改写
一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都被文学研究者们视为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亚、非、南美等地社会生活为题材,以“边缘人”的视角冷静的记述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与欧美中心世界的碰撞与交融,如小说类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抵达之谜》《模仿者》等,又如非小说类作品《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等。在奈保尔众多充满异域特色的作品中,1963年出版的小说《斯通与骑士伙伴》显得非常特别。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小说中,奈保尔的主人公们都身处英国以外的第三世界或者来自第三世界,研究者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奈保尔本人的影子,而这部小说却是唯一一部完全以英国为背
景的作品,其中的所有人物亦均是英国白人,他们的身份和经历与奈保尔本人更是相去甚远,研究者们似乎很难给这部小说贴上后殖民的标签。
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外发表的《斯通与骑士伙伴》的相关研究文章并不多,最早可追溯至Walter Allen于1964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又见伦敦》。Anthony Boxill 的《中的春天概念》一文探讨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春天意象和主人公心理变化的关联。Gillian Dooley发表的论文《奈保尔“失实的”伦敦小说:》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文本分析对该小说的“失实性”做出了论证。在我国,与它之前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和之后的《模仿者》(1967)相比,《斯通和骑士伙伴》显然没有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通过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所做的相关搜索可窥一斑:在摘要检索中搜索奈保尔上述三部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模仿者》分别显示48条结果和43条结果,而《斯通与骑士伙伴》则没有任何搜索结果。我国研究者仅在介绍奈保尔写作生涯时对该小说有所提及,且都是一带而过式的,甚至在研究奈保尔的专著中出现了对该小说的错误描述。[10]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反复解读奈保尔那些有关第三世界作品的政治性、历史性以及后殖民文化属性,强调特殊身世与经历赋予他的独特书写视角,分析其小说中众多人物所具有的文化无根性,却忽视了这本“小书”所暴露出的
奈保尔本人的后殖民文化身份。
《斯通与骑士伙伴》讲述了斯通先生暮年的一段人生经历。小说初始时,六十二岁的斯通先生还是个孤独的单身汉,住在伦敦南部的一幢宅子里,由一名同样上了年纪、邋里邋遢的女管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斯通先生是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供职于一家名叫伊斯卡尔的公司,退休指日可待。在一次
朋友的聚会上,斯通先生结识了小他十来岁的寡妇斯普林格太太,两人很快相爱结婚,但婚姻生活并没有消除斯通先生的孤独感,反而使他感到距离亲人更远了。退休意味着衰老甚至死亡,这让斯通先生惶恐不已,在此压力下他设计了一个拜访退休员工的计划,这个被称作“骑士伙伴”的计划被公司采纳并付诸行动,斯通先生藉此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但事实上真正从计划中获益的是他的年轻搭档,而斯通先生在短暂的荣耀后依然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小说篇幅尽管不长,却涉及了衰老、死亡、人性、婚姻、家庭关系、工作、友谊等诸多主题,叙事充满奈保尔惯有的不动声色和辛辣讽刺的风格。而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奈保尔这部“白人”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文本互文现象,互文性成为这本小说的一大特征。
“互文性”概念最先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互文性理论具有极强的包
容性与概括性,许多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从广义来讲,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不论作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文本有很多方法来提及另一个文本,例如戏仿、拼贴、呼应、典故、直接引用以及平行结构。保罗・瑟洛克斯在其第一部研究奈保尔的专著中盛赞他“也许是现在唯一一位未受他人影响的作家”。[2]但这一褒奖放在任何作家身上都显得过于武断,包括奈保尔。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的奈保尔,研读英美经典文学作品是他的必修课,在创作初期写作题材和写作风格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这些来自西方的经典必定成为作家参考模仿的对象,这就解释了为何奈保尔会在早期
创作出《斯通与骑士伙伴》这样一部完全由英国白人构成的小说。在一次访谈中奈保尔曾直言自己在创作《斯通与骑士伙伴》期间尚处于“非常摇摆不定”[3]的阶段,在作家本人的漂泊经历不能为他提供充足的参考素材时,向英美宗主国的文学传统提取灵感并模仿其中经典形象与桥段是作家的必然选择,因此文学作品间的互文性成为解读该书一个重要通道,而奈保尔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又使得这种互文性具备了“改写”的第二重涵义。
一、模仿――语言文体的互文
奈保尔的小说语言一贯以冷峻、直接著称,其中不乏幽默的反讽,读者经常能够从他的小说中读到可与王尔德媲美的机智诙谐,在这本《斯通与骑士伙伴》中,奈保尔更是
以各种方式多次向王尔德致敬,实现与西方经典文本的互文。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斯通先生的侄女格温曾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表演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
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她表演了剧中的一段,其间还一人分饰数个角色,用头部的忽然晃动来表示角色的转换。她没有一处忘词,也没在表演中失去镇静。在压低了嗓子说“在手提包里”这句台词时,因为把声音压得太低,以至于“手”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喉咙间发出的干吼。[4](P50)除了这样直接的借用,书中一些幽默辛辣的人物刻画也可以被看做是对王尔德式悖论(paradox)的互文与效仿。在描述公司老板哈里时,奈保尔是这样写的:“老哈里――不熟悉他的人是这么称呼他的,而那些能和他说
得上话,并以此为荣的人则称他为哈里爵士――是个让人敬畏的人物。”[4](P77)众所周知,通常人们会用较为亲昵的叫法(“老哈里”)来称呼自己熟悉的人,而用带有头衔的叫法(“哈里爵士”)来尊称不熟悉的人,奈保尔的这段描写显然与常识相悖,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描述却恰好反映出老哈里爱慕虚荣的个性,这样的行文风格不能不让人想起王尔德对萧伯纳的讥讽式评价:“他在世上绝无敌人,也绝无朋友喜欢他。”[5]同样,奈保尔笔下的寡妇格蕾丝与《不可儿戏》中那位丧夫之后“足足年轻了二十岁”“头发因为悲伤而变成了金色”[6]的哈伯里太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