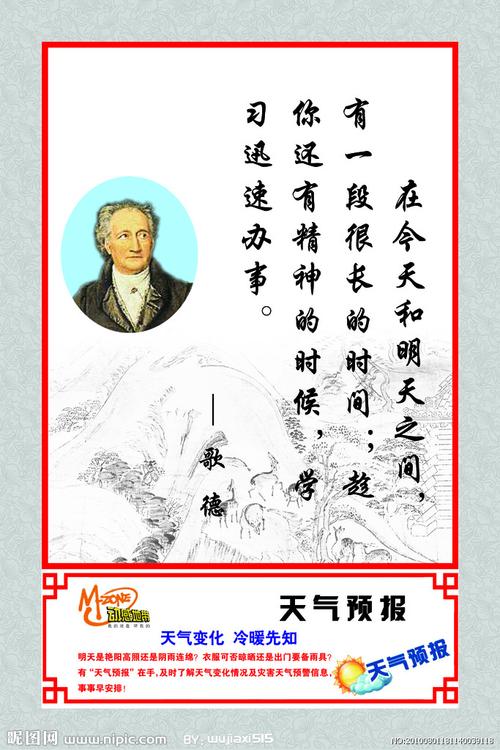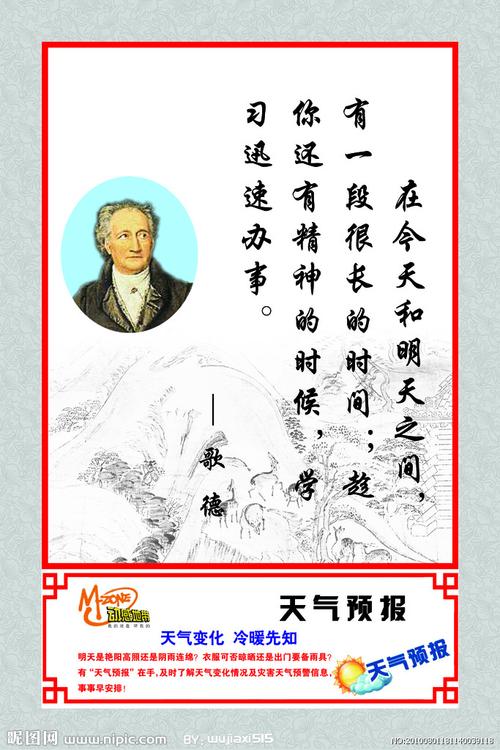
2012年11月2012年 第6期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Nov.2012
No.6,2012
《波比》:一部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书写*
黄 洁
内容提要:《波比》是澳大利亚女作家德鲁希拉·莫杰斯卡基于自己母亲的生平经历创作的一部人生书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重点阐释了三组关系,即“母亲”与“女儿”之间、“父亲语言”与“母亲语言”之间以及形式创新与女权主义政治任务之间的关系。本文试从分析这三组关系入手,揭示这一作品实质上是一部借着为母亲作传来反思在女权运动热潮消退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澳大利亚社会中激进女权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关键词:《波比》 莫杰斯卡 后激进女权主义 人生书写
中图分类号:I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6-0015-08
《波比》(Poppy)是澳大利亚文学史家、作家德鲁希拉·莫杰斯卡(Drusilla Modj-eska)于1990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莫杰斯卡1946年出生于英国,1971年经由巴布亚新几内亚来到澳大利亚,从此在这片新大陆上定居、工作和生活。她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从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奠定其在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突出地位的著作是由其博士论文改编的《流放于祖国:澳大利亚妇女作家1925—1945》(Exiles at Home:AustralianWomen Writers 1925—1945,1981)。这部以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妇女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集中体现了其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这部著作中,她
考察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男权统治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并揭示了为对抗国际、国内乃至家庭等领域的父权制的胁迫,女作家们互相扶持、互为精神支柱的姐妹情谊。批评家伯德认为该著作标志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关注妇女在文学中的形象转向挖掘妇女作家作品和重写澳大利亚文学史。(Bird:205)费里尔则认为它“将会揭开澳大利亚妇女文学创作的完整历史”。(Ferrier:77)
《波比》是莫杰斯卡在八十年代后期转向文学创作后取得的第一个丰硕成果。此后,她还相继创作了《果园》(The Orchard,
* 本文在资料收集阶段得到澳中理事会的资助得以赴悉尼大学调研,在此深表感谢。
·
·
1994)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午餐》(Stravin-
sky’s Lunch,2001)。这些作品游离于小说与非小说体裁之间,探讨不同年代、不同阶级的女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种种困境,其中既蕴含厚重的历史感,又不乏细腻的心理分析。与《流放于祖国》中展现的激进锋芒不同,这些作品常常表现出对两性关系的重新思考、
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形式创新的探索等。《波比》曾获得赫伯·托马斯文学奖(Herb Thomas Lit-erary
Award)、全国图书理事会班卓奖(NBC Banj
o Awards)、1991年年度有声读物奖(Talking Book of the Year Award)以及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奖(Douglas Stew-art
Prize)等重要奖项。该作品的面世不仅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还对其学术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该书标志着莫杰斯卡在澳大利亚身份的变化:从女权主义学者变为出类拔萃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Scarp
aro:125)《波比》出版后,莫杰斯卡放弃了大学的教席,
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除了在业余时间从事编辑工作外,
她还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在其公开领域的活动中,最能体现其公共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的,当属她对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大论争的积极参与。她在澳大利亚和其前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上,以及澳大利亚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和解的问题上,都不吝抒发自己的见解。
《波比》是一本献给母亲的书。在书末的致谢中,莫杰斯卡提到起初她想写一本单纯的传记,打算以忠于证据为第一准则。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我发现自己无法自拔地被梦境、想象和虚构吸引。作为结果,《波比》是事实和虚构、传记和小说的混合体。仅仅忠于事实似乎
否认了真实本为虚构的这一悖论,也拒绝了本书迫切需要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放弃了事实以及历史和传记的严肃的欢愉,将背离我创作的初衷。(317
)围绕母亲生平的种种疑问是创作这本书的出发点,但本书又不仅仅是母亲一个人的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拉拉吉(书中的主
要叙述者)
①发现,她书写母亲的人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将一个普通的女人从在历史上缺场的窘境中解救出来,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波比的过程就必然包含将拉拉吉作为叙述的主体来加以考虑的过程。这里的悖论,
《波比》中众多的结构和文本悖论之一,
就在于“为了通过认识她的母亲来认识她自己,莫杰斯卡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母亲来供她认识……既然‘波比’是一种创造,那么可以说莫杰斯卡也在进化或创造她自己;
创作这本书的行为本身就是作者自我不断创造的一部分”。(Lord:66
)通过追寻具有代表性的母女两代人建构自我的不同轨迹,
莫杰斯卡还试图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某些共同命运和普遍真理。
一、“母亲”与“女儿”:爱与恨的漩涡
妇女作家作品中的一大永恒主题———母女关系,同样是《波比》中重点探讨的一组关系。无论对于波比还是对于拉拉吉,母亲都似乎是她们早期痛苦的根源。波比的母亲齐娜出身于靠钢铁业发家的暴发户家庭,从小养成骄奢放纵的恶习。她宠溺
·
·2012年 外国文学 第6期
①
拉拉吉和德鲁希拉是波比最喜欢的书———罗伯逊(E.Arnot Robertson)的《普通家庭》(Ordinary
Fami-lies)
中的姐妹。拉拉吉是书中的叙述者,她聪明、勇敢、精力充沛,而德鲁希拉则是个俗气的、不讨人喜欢的角
色。在写作中,
现实中的德鲁希拉把书中虚构的自我命名为拉拉吉,一方面是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被取错了名
字,
因此想通过为自己重新命名来清算旧账,另一方面,“lalag
e”一词本身意味着“安静的谈话、静静述说的河流”等,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个非常恰当的叙述者的名字。
两个儿子,却对大女儿波比极为冷淡,甚至不惜以在精神上折磨她来发泄对丈夫的忿恨和对生活的不满。在拼贴波比的童年意象时,拉拉吉发现,波比的保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波比拥有的不是一个坏母亲,而是一个分裂的“母亲”:一边是自我放纵、顾影自怜的齐娜,被渴望着却不可得;
另一边是自我抹煞、触手可及的保姆、仆人式的母亲。“她是在这个夹缝中学会沉默的吗?没有卑躬屈膝,而是沉默着观察、
收集信息,等待她的机会,等待保姆向她许诺而齐娜却禁止的未来?分裂的母亲。她是否为了治愈这个分裂而分裂了她自己呢?”(32
)对于年幼的拉拉吉而言,她拥有的也是一个分裂的母亲:一边是使家中永远井井有条、充满欢歌笑语的“家中的天使”,另一边则是毫无征兆地某天突然精神崩溃的可怜女人。波比的患病打破了家中原本的秩序与平静,也使拉拉吉和她的妹妹们被迫离开她们熟悉的家园。拉拉吉被送到了寄宿学校,那里的封闭和压抑使她深感孤独和痛苦,
这也使她在成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无法原谅母亲。成年后的拉拉吉对于母亲的恐惧也是非理性的。“当我三十出头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害怕会患上波比的那种精神崩溃,
就好像这种事情是我们遗传的一部分一样。这种我们将遵循我们母亲设下的模式的恐惧似乎牢牢植根于女性心理的深处。”(77
)然而,排斥和恐惧不可能是母女关系的全部内容。波比最终找到了和女儿们和谐相处的方式。她学会了放手,从而使女儿们也使自己获得了全新的生活。她还做到了和自己的母亲和平共处。在齐娜最后的岁月里,波比承担起照料她的大部分责任,虽然后者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未曾改变骄奢、
刻薄的个性。年轻一代女儿的代表拉拉吉则认识到,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母亲,她就无法了解她自己,只能不断重复以前的失败。她意识到,
自己和同性密友以及恋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重复每个人最初与母亲之间展开的原始竞争:“对爱的欲
望将我们拖回最初的那一刻,然后我们被举到镜子前,她说,看,这就是你,在那个倒影中,她的和我们的,我们看到了未来。摇摆;波动。对分离的欲望;对回归的欲望。我抛弃了乔斯①,就像我在很多年前抛弃了波比,
在其他人身上寻找她的影子,在不被承认的过去寻找没有希望的未来。”(102
)根据拉康对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的阐释,婴儿最初认同在镜中抱着自己的母亲,渴望与之合而为一,当他/她发现父亲而非自己才是母亲欲望的对象时,无奈之下只好认同父亲代表的语言文化法则,从而进入象征秩序,希望以此来填补欲望的空缺。对以语言为代表的父权的服从使个体获得了掌控世界的能力,
暂时平息了其欲望叫嚣,但这却是以母亲的缺场为代价的。
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则指出女性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并不需要以割裂与母亲之间的联系为代价。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她指出同一意指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形式—
——符号和象征缺一不可。只具有符号性或只具有象征性的系统是不具备示意功能的。而意指能力的获得依赖于说话主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之间的联系。在主体尚未形成的这一阶段,婴儿没有把自己当成主体,也没有把母亲当成不同于自己的客体。婴儿会以一些特殊的表情和动作向母亲示意,这些表情和动作具有特定的意义。通过研究这
·
·黄 洁 《波比》:一部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书写
①
乔斯是拉拉吉的一位同性密友,文中暗示两人
之间存在着某种超越友谊的深刻情感联系。
一时期婴儿的行为特征,克里斯蒂娃得出语言的习得最初是发生在身体间的,然后才是主体间的。语言的产生与前俄狄浦斯阶段密不可分。(Schmitz:74—75)从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波比的一生是在追求与母亲的重新团聚,追求恢复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和孩子间的永恒纽带。她深陷符号学意义上的分裂/沉默、对母亲渴望、被父亲抛弃的状态中,她不得不冲出泥沼,发现自己的声音。而拉拉吉则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妇女一样,通过接受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长大,自然而然地重视公众的、世界性的、外在的现实而对内在的现实不屑一顾。对于拉拉吉而言,她需要学会的是对符号系统的重视,学会接受符号和象征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Hopkins:53)
波比对自我的追寻由其逃离社会强加在女性头上的种种要求的欲望来界定。她的斗争是对战后英国社
会的中产阶级妇女被强加的角色身份的反抗。这些角色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常常被生物学话语所掩盖。波比的前半生都活在别人的期待和注目下。当她在众多的社会角色,尤其是“母亲”的角色上,竭力达到社会普遍要求的努力遭遇严酷的现实时,心理平衡就被打破了。“因为母亲占据了政府政策、精神治疗策略、大众社会学和日常思考的中心舞台,她只能认为自己辜负了我们”。(86)然而,精神崩溃恰好成为一个转机,使她开始正视自我的不完美和有时的无能为力。从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的幻想破灭后,她开始安排自己接受再教育。新获得的人生智慧使得她顺利度过了被丈夫抛弃的痛苦时光。她随后开展的极富开创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她对与神父情人之间艰难爱情的长期坚守以及对印度佛教的信奉,都标志着她脱离了传统社会期待的束缚,开始了全
新的生活。
波比的奋斗经历给了拉拉吉重要的人生启示。在尝试了解波比的人生之前,拉拉吉对于自己从事的正统的学术工作及其背后的理性组织原则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在英国待上一年后,当她返回之前的工作岗位,却发现自己对在学术机构被解码的庞大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再感兴趣。她认识到,自己以往一向得心应手的研究写作的方式实际上割裂了文字和用它们来写作或阅读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她尝试说服她的同事在教学中关注“再现的母性纽带”,通过研究“妇女运用写作的方式、她们的作家身份来凸显女性的主体性”,但她的提议却遭到了冷遇。一位同事回答,“我们不想社会性别沦为女性忏悔,或仅仅是心理分析”,另一位同事回答,“我对消化分解的修辞不感兴趣”。(152)拉拉吉
的同事们将对再现的物质纽带的关注视为现代的异端,“因此《波比》戏剧性地展现了女权主义内部的争论和焦虑,以及拒绝向女性前辈学习的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Trigg:141)
二、“父亲语言”与“母亲语言”:
知识女性的突围
莫杰斯卡曾表示,20世纪80年代末,众多历史学家、批评理论家和小说作家都对历史、传记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她无法抗拒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传记?(Glendin-ning,et al.:32)在这层意义上,《波比》还承载了作者对传记这一文学样式本身的探索。
在创作之初,拉拉吉倾向于将传记写作与历史写作相认同,认为两者都是建立在证据和可供佐证的事实的基础上的。作为一名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拉拉·
·
2012年 外国文学 第6期
吉深信她可以通过借鉴传统的历史写作的方式,写出母亲的人生故事。她收集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
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校对后,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艰辛创作。她并不满足于给出一个纵向的、孤立的人生故事,而是倾向于将波比一生中的重要事件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从而将母亲的故事从私人领域引向公共领域。“我曾试图把波比的生命附着在历史的运动和我所了解的辩论与阐释上,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够治愈一代代传下来的伤口”。(12)在她看来,将波比的个人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是赋予波比的生命以意义的重要手段。她试图诱导波比进入宏大叙事的话语框架,但波比却坚持个人历史是游离于传统历史叙事之外的。当拉拉吉询问她对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时,她的回答是一连串日常家庭的琐碎细节。拉拉吉认为,母亲对历史的概念持敌视的态度,“可能是她对理查德和我的敌意的移植,因为这是我们共享的东西,历史,我敢说我们曾用它来把她排除在外”。(67)波比则表示,她对历史的反感是基于她对这套话语的冷漠和非人性化的清醒认识。她认识到历史话语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等个体弱势生命和边缘群体极度缺乏尊重。“进步”或“历史”这类抽象概念常被政客们挪用,成为他们逃避责任、粉饰太平的有效工具。
拉拉吉本以为自己可以像找到杂线团里的每一根线是来自哪件织物那样,对每个事实、每件证物进行背景还原,从而将围绕波比故事的空隙填满。但她很快就发现,这一解决方案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对文件的欺骗性的权威和声音的自我迷惑力保持警惕。有时我为证据的不足而感到无力,有时又因为同一原因而充满释放感:如果没有证据,我又该如何写呢?我发现
我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被记忆所辜负,被争先抢后、互相矛盾的故事所捉弄。情感可以作为证据吗?
记忆呢?故事呢?”(67)写作中面临的困境使拉拉吉认识到,仅仅以历史书写的方式来撰写母亲的人生故事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开始更多地求助于小说的写作模式,并从而发现这样做可以使以往写作中遇到的困难迎刃而解。“因为缺乏信息,所以我不得不把它编造出来。一旦我开始编造,就感到无比的自由。”(Rivers:320)
拉拉吉作为历史学家和女儿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了她必然走上探索自己语言的艰辛道路。作为一位深谙历史书写方法论和模式的历史学家,她认为将个体生命楔入历史运动的洪流中的这类叙事是一个可操作的领域。而作为书写母亲人生故事的女儿,她又试图为这个拒绝秩序,坚持活在当下,活在未被记录、没有系统性的每一天的个体描绘出生动的人生画卷。这两种身份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张力:
她的故事,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礼物……我本以为我拥有宏大的设计,两条河流将汇入同一部作品:一本传记。但当它遭遇日常细节时……没有什么是连贯一致的,那里有巨大的缺口和沉寂。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接近证据,却发现一旦我走出公共领域来到幽暗的私人水道,证据变得不像我的教育告诉我的那么坚实可靠……我所持有的历史学家的声音将压倒女儿声音的自信开始动摇。(Glendinning,et al.:33)
这就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为了再现被湮没的个体的日常经历,拉拉吉从公开的话语———“父亲语言”(fathertongue)(以历史话语为代表,这也是她在长期的教育中习得和内化的)转向“母亲语言”(mother tongue)———“谈话式的、无所·
·
黄 洁 《波比》:一部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