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
来源:凤凰⽹读书凤凰⽹读书
鲁迅与梁实秋两位⽂学⼤家,曾在同⼀个时代引领⼀时之⽂学风潮,但是⼀场将近10年的论战,使两⼈成为
最为⼈所知的死对头,造就了民国⽂坛有名的⼀段公案。两⼈从⽂学观点到政治⽴场,笔战升温,直⾄梁被
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狗”,可谓是硝烟弥漫。但这场论争的导⽕索,竟然是⼀场翻译风波。
1929年9⽉,梁实秋在《新⽉》杂志发表了⼀篇题为《论鲁迅先⽣的“硬译” 》的⽂章,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
其是“硬译” 、“死译”,说这“稀奇古怪的句法,读了等于不读”,于是⽩话中⽂诞⽣未久,便遭遇了这次翻译理
论的交锋。
论鲁迅先⽣的“硬译”
⽂/梁实秋
梁实秋夫妇
西滢先⽣说:“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
懂愈糟。”这话不错。不过“令⼈看不懂”这⽑病就不算⼩了。我私⼈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个条件就是要令⼈
看得懂,译出来⽽令⼈看不懂,那不是⽩费读者的时⼒么?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太不忠实,把精
华译成了糟粕,但是⼀部书断断不会从头⾄尾的完全曲译,⼀页上就是发现⼏处曲译的地⽅,究竟还有没有
曲译的地⽅,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穷的,⽽你读
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定是从头⾄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精⼒。况且犯曲译
的⽑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病,⽽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
的,然⽽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说:“他们⾮但字⽐句次,⽽且⼀字不可增,⼀字不可先,⼀字不可后,名⽈翻译,⽽‘
译犹不译’,这种⽅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先⽣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概是周作⼈先⽣的创造了
。
死译的例⼦多得很,我现在单举出鲁迅先⽣的翻译来作个例⼦,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的⼩说和杂感的
⽂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没有⼈能说鲁迅先⽣的⽂笔不济,但是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鲁迅先⽣前些年翻
译的⽂字,例如厨川⽩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
。今年六⽉⼗五⼤江书铺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今年⼗⽉⽔沫书店出版的《卢那卡尔斯基:⽂
艺与批评》,这两部书都是鲁迅先⽣的近译,我现在随便捡⼏句极端难懂的句⼦写在下⾯,让⼤家知道⽂笔
矫健如鲁迅先⽣者却不能免于“死译”: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可能的材料,⽽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配
着即被组织在它⾥⾯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定的社会底兴味这⼀层意义上,
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艺术论》第七页)
“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组织化之际,则直接和观念形态,以及产⽣观念形态⽣活上的事实,或把持着这些观念形
态的社会底集团相连系的事,是颇为容易的。和这相反,问题倘触到成着艺术的最为特⾊底物质的那感情的
组织化,那就极其困难了。”(《艺术论》第⼗⼆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感
底性质的漠然的满⾜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的深奥,有着兴味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
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彻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常的⼤的教训。”(《⽂艺与批
评》第⼀九⼋页)
够了。上⾯⼏句话虽然是从译⽂中间抽出来的,也许因为没有上下⽂的缘故,意思不能⼗分明了。但是专就
⽂字⽽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真感觉⽂字的艰深。读这样的书,就
如同看地图⼀般,要伸着⼿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
鲁迅先⽣⾃⼰不是不知道他的译笔是“蹩扭”的。他在《⽂艺与批判》和《译者后记》⾥说:“从译本看来,卢
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不够,和中国⽂本来的缺点,译完⼀看,晦
涩,甚⽽⾄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折下来呢,⼜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
译之外,只有‘束⼿’这⼀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看
下去⽽已。”我们硬着头⽪看下去了,但是⽆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鲁迅先⽣说“中国⽂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艰涩”的两个缘故之⼀,照这样说,中国⽂若不改良,翻译的书
总不能免去五⼗分的“晦涩”了。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
地⽅。假如两种⽂中的⽂法句法词法完全⼀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件⼯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有“本来的
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要义,因为“硬着头⽪”不是
⼀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假如“硬译”⽽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
那真是⼀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是有“缺点”吗?
(1929年9⽉10⽇《新⽉》第⼆卷第六、七号合刊)
《新⽉》杂志书影
之后,鲁迅开始在《萌芽⽉刊》上发⽂回击,从此开始了两个⼈旷⽇持久的翻译⼤论战。
“硬译”与“⽂学的阶级性”
⽂/鲁迅
1
听说《新⽉》⽉刊团体⾥的⼈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也在两
个年青朋友的⼿⾥见过第⼆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翻,是争“⾔论⾃由”的⽂字和⼩说居多。近尾巴处,
则有梁实秋先⽣的⼀篇《论鲁迅先⽣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
段译⽂,以及在《⽂艺与批评》的后记⾥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不够,和中国⽂本来的缺点,译完⼀看,
晦涩,甚⽽⾄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失了原来的语⽓,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
外,只有束⼿这⼀条路了,所余的惟⼀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看下去⽽已”这些话,细⼼地在字旁加
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
道:“我们‘硬着头⽪看下去’了,但是⽆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社的声明中,虽说并⽆什么组织,在论⽂⾥,也似乎痛恶⽆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
有组织的,⾄少,关于政治的论⽂,这⼀本⾥都互相“照应”;关于⽂艺,则这⼀篇是登在上⾯的同⼀批评家所
作的《⽂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篇⾥有⼀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本这类的书能被我
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字,……简直读起来⽐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个中国⼈,⽤中国⼈
所能看得懂的⽂字,写⼀篇⽂章告诉我们⽆产⽂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烦,
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认是⼀切中国⼈的代表,这些书既为⾃⼰所不懂,也就是为⼀切中国⼈所不懂
,应该在中国断绝其⽣命,于是出⽰⽈“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着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梁先⽣⾃以为“硬着
头⽪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个问题。以硬⾃居了,⽽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社的
⼀种特⾊。第⼆,梁先⽣虽⾃来代表⼀切中国⼈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个问题。这问题
从《⽂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章⾥,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
。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据《韦⽩斯特⼤字典》,Proletary的意
思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
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只会⽣孩⼦的阶级!〔⾄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须来争这“体⾯”,⼤约略有
常识者,总不⾄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产者都看作罗马⼈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
者必不和埃及的“炼⾦术”混同,对于“梁”先⽣所作的⽂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桥”竟会动笔
⼀样。连“翻翻字典”〔《韦⽩斯特⼤字典》!〕也还是“⽆所得”,⼀切中国⼈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2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的⽂字⾥,有两处都⽤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
味了。⾃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类则决不只⼀⼈,⽤“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看起来较有⼒量,
⼜不⾄于⼀⼈双肩负责。然⽽,当“思想不能统⼀”时,“⾔论应该⾃由”时,正如梁先⽣的批评资本制度⼀般,
也有⼀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
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所得”的读者存在,⽽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存,和“死译”
还有⼀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社的“他们”之⼀,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样的。
那⼀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部书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
给你⼀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穷的,⽽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可以加上夹圈,但
我却从来不⼲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于使⼈⽓闷,憎恶
,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有新⽉社的⼈们的译着在:徐志摩先⽣的诗,沈从⽂凌叔华先⽣的⼩说
,陈西滢〔即陈源〕先⽣的闲话,梁实秋先⽣的批评,潘光旦先⽣的优⽣学,还有⽩璧德先⽣的⼈⽂主义。
所以,梁先⽣后⽂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般,要伸着⼿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
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样,要伸着⼿指来找寻“句
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于还须伸着⼿指〔其实
这恐怕梁先⽣⾃⼰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是只⽤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
同⼀之劳,照例⼦也就和“死译”
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程式⽆关,会打算盘的⾃以为数学家,看起
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为学者,便与⼀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梁先⽣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的缘故,意思不能⼗分明了”。在
《⽂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章中,也⽤了类似⼿段,举出两⾸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的⽆产⽂学
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本《新⽉》
⽉刊⾥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页上,举出⼀段⽂字来——
“⼩鸡有⽿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鸡长⽿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鸡⿊鸡?”枝⼉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鸡才知道。”
“婉⼉姊说⼩鸡会变⼤鸡,这些⼩鸡也会变⼤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了,象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么⼤吧?”
也够了,“⽂字”是懂得的,也⽆须伸出⼿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段看,是既不“爽快”,⽽
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还有⼀个诘问:“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于这个地⽅。假如两种⽂中的⽂
法句法词法完全⼀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件⼯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要
义,因为‘硬着头⽪’不是⼀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精悍的语⽓’。假如‘硬译’⽽还能保存‘
原来的精悍的语⽓’,那真是⼀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
相同的外国⽂,或者希望“两种⽂中的⽂法句法词法完全⼀样”。我但以为⽂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
,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且也是⼀种⼯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作没有什么
区别么?⽇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起古⽂来,更宜于翻译⽽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
⽓,开初⾃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些⼈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
⼰有了。中国的⽂法,⽐⽇本的古⽂还要不完备,然⽽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
《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话⽂⼜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
有些“⽂法句法词法”是⽣造的,⼀经习⽤,便不必伸出⼿指,就懂得了。现在⼜来了“外国⽂”,许多句⼦,即
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教之化为⼏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
,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指”,“
硬着头⽪”,于有些⼈⾃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
有若⼲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们”的苦乐以及⽆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有本不必求助于⽆产⽂学理论,⽽仍然很不了了的地⽅,例如他说:“鲁迅先⽣前些年翻译的⽂学
,例如厨川⽩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
些常识的⼈就知道:“中国⽂和外国⽂是不同的”,但同是⼀个外国⽂,因为作者各⼈的做法,⽽“风格”和“句法
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种外国⽂,易解的程度就都⼀式。我的
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样,是按板规逐句,甚⽽⾄于逐字译的,然⽽梁实秋先⽣居然以为还能看懂
者,乃是原⽂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
⽐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专读《古⽂观⽌》的学者们,看起来⼜何尝不⽐“天书”还难呢?
3
但是,这回的“⽐天书还难”的⽆产⽂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不⼩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
好象滑稽,然⽽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说:“我现在批评所谓⽆产⽂学理论,也
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点材料⽽已。”这就是说:因此⽽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括⼀切“天书”译者在内,故⽈“们”〕也只能负⼀部分的责任,⼀部分是要作者⾃⼰的
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和托
罗兹基的半部《⽂学与⾰命》,则确有英⽂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译⽂定该⾮常易解。梁先⽣对于
伟⼤的⽆产⽂学的产⽣,曾经显⽰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和勇⽓,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下⼦,寻
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不求⽈胡涂,知其有⽽不求⽈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开
起⼝来,却很容易咽进冷⽓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结论是并⽆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净的是吴
稚晖先⽣的“什么马克思⽜克斯”以及什么先⽣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
太平。但梁先⽣却中了⼀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产者
。不过这“⽆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觉。是⼏个过于富有同情⼼⽽⼜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
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
世界的思想。况且“本⽆其物”的东西,是⽆从⾃觉,⽆从激发的,会⾃觉,能激发,⾜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
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说⽣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被宗教家烧死,
或者⼤受保守者攻击呢,然⽽现在⼈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物确也在进化的
缘故。承认其有⽽掩饰为⽆,⾮有绝技是不⾏的。
但梁先⽣⾃有消除⽃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明”
,“⼀个⽆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苦苦诚诚实实的⼯作⼀⽣,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
是正当的⽣活⽃争的⼿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年,但当不⾄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明,都以资产为基
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明,⽽繁盛时俱⾮在资产社会,他⼤
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于⽆产者应该“⾟⾟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法,则是
中国有钱的⽼太爷⾼兴时候,教导穷⼯⼈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级去的“
⽆产者”也还多。然⽽这是还没有⼈“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个⼀
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所说,“他们是⼀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
常轨的⼀跃⽽夺取政权财权,⼀跃⽽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苦苦诚诚实实⼯作⼀⽣,多少必定可以得
到相当的资产”的“⽆产者”呢?⾃然还有的。然⽽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的忠告,将为⽆产者
所呕吐了,将只好和⽼太爷去互相赞赏⽽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以为是不⾜虑的。因为“这种⾰命的现象不能是长久的,经过⾃然进化之后,优胜
劣败的定律⼜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过⼈的⼈占优越的地位,⽆产者仍是⽆产者”。但⽆产阶级⼤概也知道“
反⽂明的势⼒早晚要被⽂明的势⼒所征服”,所以“要建⽴所谓‘⽆产阶级⽂化’,……这⾥⾯包括⽂艺学术”。
⾃此以后,这才⼊了⽂艺批评的本题。
4
梁先⽣⾸先以为⽆产者⽂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学上⾯”
,因为⼀个资本家和⼀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但还有相同的地⽅,“他们的⼈性〔这两字原有套圈〕并没
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不是恋爱的⽅式”〕,“⽂学就是表现这最
基本的⼈性的艺术”。
这些话是⽭盾⽽空虚的。既然⽂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以竭⼒爬上去为“有出息”
,那么,爬上是⼈⽣的真谛,富翁乃⼈类的⾄尊,⽂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何必如此“富于同情⼼”
,⼀并包括“劣败”的⽆产者?况且“⼈性”的“本⾝”,⼜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
⼒,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这⼒和度数,是须⽤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物质⽽显⽰化合⼒和
硬度的单单“本⾝”,⽆此妙法;但⼀⽤物质,这现象即⼜因物质⽽不同。
⽂学不借⼈,也⽆以表⽰“性”,⼀⽤⼈,⽽且还在阶级社会⾥,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需加以“束缚”
,实乃出于必然。⾃然,“喜怒哀乐,⼈之情也”
,然⽽穷⼈决⽆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受的酸⾟,饥区的灾民,⼤约
总不去种兰花,象阔⼈的⽼太爷⼀样,贾府上的焦⼤,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
⽆产⽂学,然⽽“⼀切东西呀!”“⼀切⼈呀!”“可喜的事来了,⼈喜了!”也不是表现“⼈性”的“本⾝”的⽂学。倘
以表现最普通的⼈性的⽂学为⾄⾼,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殖——的⽂学,或者
除去“运动”,表现⽣物性的⽂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所以以表现⼈性为限,那么,⽆产者
就因为是⽆产阶级,所以要做⽆产⽂学。
其次,梁先⽣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关。托尔斯泰出⾝贵族,⽽同情于贫民,然⽽并不主张阶级⽃争;马
克思并⾮⽆产阶级中的⼈物;终⾝穷苦的约翰逊博⼠,志⾏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学,当看作品本⾝
,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分。这些例⼦,也全不⾜以证明⽂学的⽆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贵族
,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不主张阶级⽃争。马克思原先诚⾮⽆产阶级的任务,但也并⽆⽂学作
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定是不⽤⽅式的恋爱本⾝。⾄于约翰逊博⼠终⾝穷苦,⽽志⾏吐
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苦苦诚诚
实实的⼯作⼀⽣,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
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的专利品,⼤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学⽆缘”,但鉴赏⼒之有
⽆却和阶级⽆⼲,因为“鉴赏⼒也是天⽣的⼀种福⽓”,就是,虽在⽆产阶级⾥,也会有这“天⽣的⼀种福⽓”的
⼈。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种“福⽓”的⼈,虽穷得不能受教育,⾄于⼀字不识,也可以鉴赏《新⽉》⽉
刊,来作“⼈性”和⽂艺“本⾝”原⽆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也知道天⽣这⼀种福⽓的⽆产者⼀定不多,所以另
定⼀种东西〔⽂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通俗⼩说之类”,因为“⼀般劳⼯劳农需要
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学确因阶级⽽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之⾼低
⽽定的,这种⼒量的修养和经济⽆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所以⽂学家要⾃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
族所雇⽤,也不该受⽆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产⽂学理论中
,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阶级的⽂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却该受⽆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
⽂章,不过说,⽂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学家虽⾃以为“⾃由”,⾃以为超了阶级,⽽⽆意识底地,也
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配,那些创作,并⾮别阶级的⽂化罢了。例如梁先⽣的这篇⽂章,原意是在取消
⽂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明的祖宗,指穷⼈为劣败的渣滓,只要⼀瞥,就知道是资产家
的⽃争的“武器”,——不,“⽂章”了。⽆产⽂学理论家以主张“全⼈类”“超阶级”的⽂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
西,这⾥就给了⼀个极分明的例证。⾄于成仿吾先⽣似的“他们⼀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知道安慰他们去”,说
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产⽂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样地对于⽆产
⽂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其次,梁先⽣最痛恨的是⽆产⽂学理论家以⽂艺为⽃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利⽤⽂
学来达到另外的⽬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字便是⽂学”。我以为这是⾃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
,都不过说凡⽂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字便是⽂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有许多
诗歌⼩说,填进⼝号和标语去,⾃以为就是⽆产⽂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产⽓,不⽤⼝号和
标语,便⽆从表⽰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产⽂学。今年,有名的“⽆产⽂学底批评家”钱杏村先⽣在《
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众能解的⽂学,⾜见⼝号标语之未可厚⾮,来给那些“⾰
命⽂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样,是有意的或⽆意的曲解。
卢那卡尔斯基所谓⼤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本⼦那样的⽂体,⼯农⼀看便会了然
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旗章,⽽他的诗中并不⽤标语和
⼝号,便可明⽩了。
最后,梁先⽣要看货⾊。这不错,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译诗算是在⽰众,是不对的。《新⽉》上就曾
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是诗。就我所见的⽽论,卢那卡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
的《溃灭》,格拉特柯夫的《⽔门汀》,在中国这⼗⼀年中,就并⽆可以和这些相⽐的作品。这是指“新⽉社”
⼀流的蒙资产⽂明的余荫,⽽且衷⼼在拥护它的作家⽽⾔。于号称⽆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
绩。但钱杏村先⽣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学的本领当然幼稚⽽单纯,向他们⽴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
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
有富翁那么肥胖⼀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刚刚放下锄斧柄⼦的⼈,⼤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
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莫⾮克服了⾃⼰的⼩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
么?不会的。俄国的⽼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号⽽
⽆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艺为阶级⽃争的武器”,⽽在“借阶级⽃争为⽂艺的武器”,在“⽆产
者⽂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的⼈,试看去年的新书⼴告,⼏乎没有⼀本不是⾰命⽂学,批评
家⼜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学坐在“阶级⽃争”的掩护之下,于是⽂学⾃⼰倒不必着⼒,因⽽于⽂学
和⽃争两⽅⾯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前的⼀时现象,当然毫不⾜作⽆产⽂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
⽆产阶级⾰命家⼀定要把他的宣传⽂学唤做⽆产⽂学,那总算是⼀种新兴的⽂学,总算是⽂学国⼟⾥的新收
获,⽤不着⾼呼打倒资产的⽂学来争夺⽂学的领域,因为⽂学的领域太⼤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
但这好象“中⽇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未丰的⽆产者看来,是⼀种欺骗。
愿意这样的“⽆产⽂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产
者”⼀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产⽂学。⽆产者⽂学
是为了以⾃⼰们之⼒,来解放本阶级以及⼀切阶级⽽⽃争的⼀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的地位。就拿⽂
艺批评界来⽐⽅罢,假如在“⼈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处租来暂⽤〕⾥,向南⾯摆两把虎⽪交椅
,请梁实秋钱杏村两位先⽣并排坐下,⼀个右执“新⽉”,⼀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5
到这⾥,⼜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的问题:⽆产⽂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
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和⼏个以⽆产⽂学批评家⾃居的⼈,和⼀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
⽩⼀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的攻击是多极了,每⼀种刊物上,⼤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作者的⼝吻,则粗
粗⼀看,打抵好象⾰命⽂学家。但我看了⼏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既不中腠理,⼦弹所击之处
,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今还未判定,忽说⼩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
封建余孽”,⽽且⼜等于猩猩〔见《创造⽉刊》上的《东京通信》〕;有⼀回则骂到⽛齿的颜⾊。在这样的社
会⾥,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
出⽛齿⾊黄,即有害于⽆产阶级⾰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家有些
胡涂。对于敌⼈,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本解剖学,有⼀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
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命者,以为窃⽕给⼈,虽遭天帝之虐待
不悔,其博⼤坚韧正相同。但我从别国⾥窃得⽕来,本意却在煮⾃⼰的⾁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在咬
嚼者那⼀⾯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躯:出发点全是个⼈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市民性的奢华,
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来,反⽽刺进解剖者的⼼脏⾥去的“报复”。梁先⽣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
这样的⼈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和光。
这样,⾸先开⼿的就是《⽂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命⽂学家,便在所编的《⽂
艺⽣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没落,⽽可惜别⼈着了先鞭。翻⼀本书便会浮起,做⾰命⽂学家真太
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种⼩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
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两样了
,在《拓荒者》和《现代⼩说》上,都说是“⽅向转换”
。我看见⽇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冈铁兵上,算是⼀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
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连想也不肯想的⽼病。译⼀本关于⽆产⽂学的书,是不⾜以证明⽅向的,倘有曲
译,倒反⾜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产⽂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
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信并⽆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
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个原因。⾃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
,也不“硬”或“死”
的⽂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世间纸张还多,每⼀⽂社的⼈数却少,志⼤⼒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
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之苦。上海的《申报》上,⾄于称
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
曾往⽇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谈到⽇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原⽂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
……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的,如果⽇本⼈将欧洲⼈那⼀国的
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
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不过梁先⽣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只嫣然⼀笑,扫荡⽆余,真
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是从俄⽂直接译过许多⽂艺理论和⼩说的,于我个⼈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
⼀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翻译者,陆续翻出好书来,不仅骂⼀声“混蛋”就算尽了⾰命⽂学家的责任。
然⽽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是不译的,称⼈为“阿狗阿猫”的伟⼈也不译,学过俄⽂的蒋先⽣原是最为
适宜,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本《⼀周间》,⽽⽇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谈达尔⽂,⼤谈
尼采,到欧战时候,则⼤骂了他们⼀通,但达尔⽂的着作的译本,⾄今只有⼀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
德⽂的学者及⽂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笑骂,仍从⽇⽂来重
译,或者取⼀本原⽂,⽐照了⽇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来填⼀填彻底
的⾼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象蒋先⽣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6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居了,⽽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社的⼀种特⾊”这些话,到这⾥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句
,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者则骂之,讥⼈者则讥之。
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之道,还治其⼈之⾝”,虽然也是⼀种“报复”,⽽⾮为了⾃⼰。到⼆卷六七号合本的
⼴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
乎理性的学说”
。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还⽛”,和开初仍然⼀贯。然⽽从这条⼤路⾛下去,⼀定要遇到“以暴⼒抗
暴⼒”,这和新⽉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回,新⽉社的“⾃由⾔论”遭了压迫,照⽼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上所显现
的反应,却是⼀篇《告压迫⾔论⾃由者》,先引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
⾃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番替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量相类,或⼒量较⼩的⼈的,倘给有⼒者
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掩住⾃⼰的脸,叫⼀声“⼩⼼你⾃⼰的眼睛!”
〔发表于⼀九三零年三⽉〕
及后,两⼈的论战升温,则不仅仅是关于中外⽂学见解 和翻译理论的较量,⽽是引⼊了⼤于⽂学外的其他因
素。如今事情已过去近⼀个世纪,当年关于翻译的分歧,仍然有参考价值。
近期活动
-End-
甲申同⽂翻译TIIT
更多精彩内容进⼊ [新国风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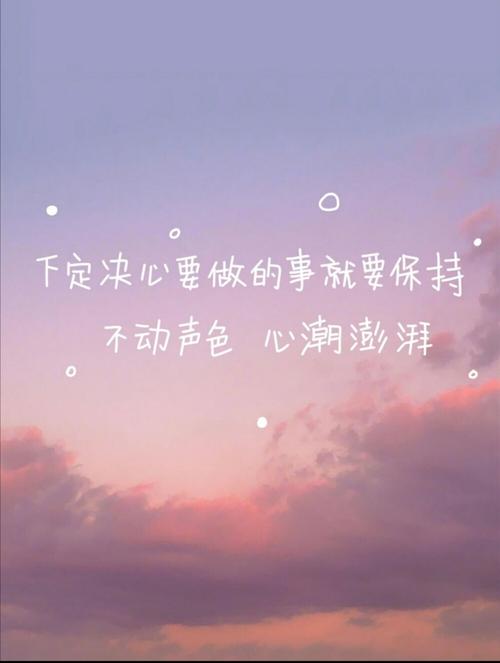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2023-05-25 18:50:26,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8501182817853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强译、硬译,稀奇古怪.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