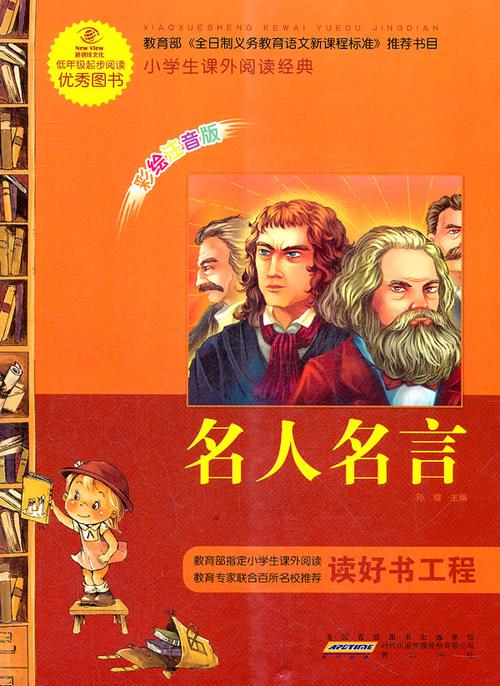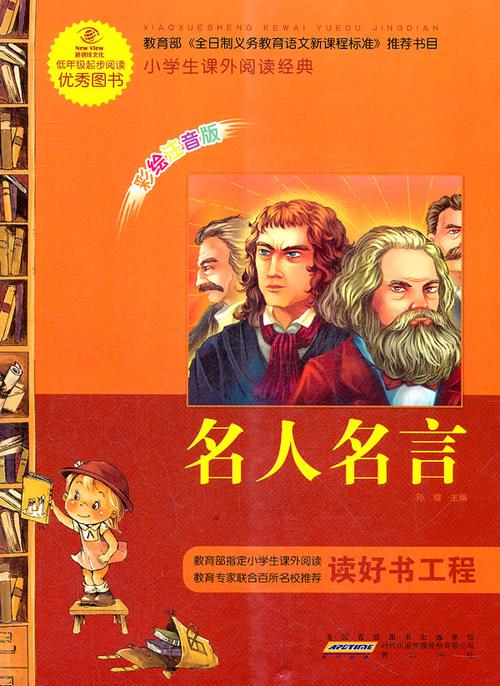
2023年5月22日发(作者:南瓜子的营养价值)陈凯歌导演风格解读
陈凯歌导演说过的一句话:电影,是很多人在黑暗中聚会,去共同分享一个梦想。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造梦者,陈凯歌始终顶着一颗有很多文学和思想成分的巨大头颅,将他的文化思辩、忧患意识、才华激情,统统浇铸进电影这门在一些人看来容量有限的艺术当中。在他的光影世界里,电影不再是单纯的再现生活的手段,而是一种揭示和评价生活的工具。借助这种工具,他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感受,以一种批判的目光来审视人的生存状态,追溯这种状态背后所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并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我们常常可以在他寓意复杂和精心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体会到他那种尖锐的批判锋芒。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表达强烈的人文意味和美学追求,并调动多种电影手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重而犀利、平和而激越的电影风格。
综观陈凯歌所有的电影,无论是具有寓意象征的《黄土地》、《边走边唱》,具有较强反思的《大阅兵》、《孩子王》,还是影象华丽的《霸王别姬》、《无极》,其影片都有着他思想的反映。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反思,一直是陈凯歌电影的灵魂。他一贯的艺术目标就是在史诗格局中注入文化反思,达到超验的理性和哲学的意味。他的创作活动也有一条连贯的主线,就是透过电影阐述中国文化历史的变迁和沉浮。这种居高临下的创作态度固然有雕琢之气,但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感性。当这种感性经历了岁月的打磨,逐渐转变成一种风格,与作品水乳交融,我们便不难从芒芒片海中一眼识别那些打着陈氏烙印的人文电影。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光影面纱,一窥其风格的四种外化表现。
一、借助寓言故事 表达象征意味
作为中国新电影语言的奠基者之一,陈凯歌总是试图在寓言式的历史景观与情节的呈现中实现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扣问。他把那些他爱之深,恨之切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幻化成一则则色彩斑斓,浓烈而忧伤的东方寓言搬上荧幕。当这些纯正而超载的东方寓言像一幅幅巨大的画框惊现于人们眼前时,它身负的底蕴与内涵便随着光影的释放从容流泻。
从他的第一部石破天惊之作《黄土地》开始,陈凯歌就踏上了一条寓言叙事之路。影片中的“黄土地”,沟壑连绵,山形地貌大起大落,看上去既温暖又冷漠,既贫瘠又深广,传达出一种特别沉重和压抑的感觉。导演抓住了这种感觉,没有把它当作单纯的故事背景来处理,而是让它成为了整个民族人格化的象征体。生生不息的黄土地,默默耕作的身影,显示
出一种巨大的韧性和耐力,也映
衬着心灵的闭塞,保守与无奈。电影从一个启蒙者的目光看出了这片古老土地上人民的愚昧。在黄土高原上搜集民歌的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唤醒了当地少女翠巧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但她却难以抵抗自己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她所面对的是养育了她的人,是那种平静和温暖中的愚昧,最终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死的代价。戛然而止的歌声中,“黄土地”被赋予了复杂的情感,它象征了那种沉淀在民族文化深处的保守性格和无法挣脱天命的悲剧感。影片结尾,翠巧的弟弟在求雨的人流中逆向奔跑的情景,又似乎在暗示着那长期被压抑在古老黄土之下的年轻生命力必定有它被唤醒并喷薄而出的一天。影片通过人与土地这种自氏族社会以来就存在的古老又最永恒的关系的展示,表现了陕北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也表达了创作者对民族特性、农民命运的思考。
如果说《黄土地》是一则民俗的寓言,那么《边走边唱》就是一个关于谎言的寓言。老神神终其一生,七十年,千根弦,换来的却是一张白纸。他成为了历史谎言的蒙难者与牺牲品,但他仍试图延续这历史的链条:将谎言传递给石头。《边走边唱》以寓言的方式透过独特的视觉世界和意蕴深厚的自然景观突现了两个顽强的生命。对光明的渴望在这里成为了谎言,人物的理想和现实的真实隔着一段飘渺的距离。影片讲述了生活在谎言中的顽强和生命。盲人歌手用琴声和音乐构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然而这个未来却是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上的。导演陈凯歌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生命渴望和民间故事来阐述关于世界真相的问题。
毋庸质疑,在这两部电影中,寓言精神已经不可磨灭的成为他电影的一部分。但他的寓言故事并没有一般通俗民间文学里的寓言特点,是类似口头文学传播的下里巴人,而是带有贵族式的阳春白雪。有人认为,他因此脱离了中国观众的传统文化心理和长期以来的欣赏习惯,而与观众拉开了距离。
二、将历史宏观与个人命运的微观相融合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似乎是一道必须去正视又令人晕眩的深谷。在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语境中交织着对老中国切肤的怨恨和依恋。他们一面满怀欣喜地宣告,这古旧的舞台正坍塌并沉没于世纪之交明亮的地平线上,一面又为失去在这舞台上曾出演过的,全部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戏梦人生而惋惜。1993年为陈凯歌捧回金棕榈的《霸王别姬》就是其历史叙事这一文化命题中富于深意的例证。
陈凯歌的作品从来充
满对历史与命运的思考,深沉厚重,作者气质明显。在《霸王
别姬》中,他更是完成了一次个人创作主题上的思辩,将历史宏观和个人命运的微观近乎完美得融合一处。可以说,李碧华的小说为陈凯歌提供了一段涉渡的浮木。凭借李碧华的故事,陈凯歌颇不自甘地将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情感,将对似已沉沦的旧中国文化的苦恋固化成一处“瑰丽莫名”的东方景观。它以京剧舞台的造型出现,在锣鼓喧天,斑斓绚丽之间生出一份清幽寂寥,它让一出韵味悠长的历史剧目把一段迂回曲折戏梦人生唱响。
那段为陈凯歌们欲罢不能的历史在影片中仅成为了悠长故事的标点与节拍器。它们像背景一样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和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和宿命的苦涩。诸如日寇纵马弛入北京之日,正是程蝶衣一赠佩剑之时。他带着和袁四爷周旋后的一脸残妆来到段小楼面前,看到的却是大家为菊仙道喜的热闹场面。他迎着众人的目光拂袖而去后,侵略者的马队又阻断了段小楼追赶的脚步;而解放军进入北京,却成了程蝶衣二赠佩剑的背景。面对狂喜的腰鼓队和布衣风尘仆仆的队伍,陈凯歌安排了小楼,蝶衣与张公公的重逢。两人分坐在张公公的身边,在为一座石阶所充任的观众席上,目击着这一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缕缕飘过的烟雾,遮断了画面的纵深感,将这幅三人全景呈现为一幅扁平的画面。仿佛在这一历史剧变的时刻,旧日的历史不仅永远失去了它延伸的可能,而且被挤压为极薄且平的一页:昔日显赫一时的公公与永恒的戏子,此时已一同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间不值一文的点缀。
这出跨越了老中国,新世界的人生故事负载着对老中国死亡环舞的既恨,且怨,且沉迷的复杂情感。1937,1949,1966,如翩然翻飞的斑斓戏衣,连缀起一个奇异且绚烂,酷烈且动人的东方。在这出动人的东方镜象中,导演延续了他对历史和传统的思考,阐释了人生理想与现实存在这对永恒的矛盾。在浩荡的历史洪流与社会变迁中,个人理想再强烈也是微茫的。程蝶衣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企图根据理想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在舞台和现实中,都陶醉于这样的戏剧情境之中,从而使他的人生笼罩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梦幻气氛。在强悍的历史舞台上,微小的个人即使想独舞也不可能,生活的浪潮最终淹没了他倔强的身姿。就如贝特鲁奇所说,个人只是历史的人质。
其实陈凯歌的这一观念早在《黄土地》中就初见端倪。欲挣脱封建束缚的翠巧在根深蒂固的民俗面前是那
么悲戚而无能为力。黄河边上须臾不见的小舟其实是被历史的旋涡所吞没,戏台上拔剑自刎的
蝶衣其实也是被历史的暴力所谋杀,它们都将成为人类悠长的记忆碎片中永恒的剪影。
当然陈凯歌对于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反思会随着个人经历变化而改变。从《孩子王》里对教育缺失问题的反思,到《边走边唱》的理想和谎言的辨证思考,再到《霸王别姬》里情感背叛的社会困境忏悔,陈凯歌用不同的方式对**伤痕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和探索。如果说《孩子王》和《边走边唱》还是具有个体性质的反思,那么到了《霸王别姬》已经是戏梦人生的社会悲剧了。他对**的反思从教育,文化,人性等各个角度进行思考,期间都穿插着他对**时代的激情和叛逆的情绪反映。这种反映又是他个人经验的一种自我反省,传达了他对青春时期的人生经历的成熟理性。
三 表现三大电影主题:生、死、爱
主题是一部影片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通常也能反映电影导演本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思想。而这种思想即主题,往往贯穿或者重复于同一位导演的影片中。众所周知,电影主题有三大永恒的母题:生、死、爱。导演陈凯歌以往的作品,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选择的都是压抑,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死去的沉重主题。在这类主题的创作中,陈凯歌始终袒露着士大夫式的忧愤,他的哲学表达和电影文本在这个领域亦成为了文化苦旅的代名。
〈一〉生死道场 历史见证
陈凯歌是个沉湎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生建构的导演,就拿他的开山之作《黄土地》来说,就是个很见沉默者伟力的作品。影片让民族的压抑心态得到了集中的宣泄与爆发。翠巧的“小舟从此逝”是向生而死,憨憨的逆向奔跑是死气沉沉的大背景中的一点生气。生与死成为一种符号,在历史的镜象中跃动着民族的精魂与戾气。当热烈的安塞腰鼓队从地平线下面慢慢升起来,当大块大块贫瘠而夹带血性的黄土地向镜头摇来,我们似乎可以瞥见黄土文化的精灵在旋舞。
另外一部充满生死戏剧冲突的就是《霸王别姬》。影片通过中国文化沉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及其艺人的生活,通过他们之间生与死,爱与恨的感情冲突,更通过几十年的时事风云,投射出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片中的程蝶衣在认可了自己的性别改写后,固执遵循着对虞姬的贞烈和“从一而终”的实践。他永远在任何时代,任何观众面前歌着,舞着,扮演着虞姬。如果国民党伤兵不闯上舞台,如果京剧改革不剥夺他出演的权利,他无疑会舞下去,歌下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菊仙
奉行的是夫唱妇随,贫贱不移,她在生活中努力扮演着一个良家妇女。她的至高理想是平安地守着一个家,一个男人,度一
份庸常而温馨的日子。可以说,他们都在扮演着自己所规定的理想女性。当他们的角色被历史剥夺时,剩下的便只有赴死这条路了。蝶衣拔剑自刎像虞姬一样死在“霸王”面前,不过是为了完满对角色的诠释。菊仙亦然,当她一次次被程蝶衣,师傅最后是段小楼本人指认为一个“花满楼的姑娘”,一个被社会所不耻的妓女时,她便身着大红的嫁衣悬梁自尽于她“堂正”的婚床之前。这里的生与死成了他们出戏入戏的标志,他们在“戏”里而生,也因“戏”的结束而死。导演借助这种戏梦一样的生死剖析了历史和传统对人的制约和影响。
尽管同为哲学题材,同样表现生死主题,两片在手法上还是不尽相同的。论界一般认为《霸王别姬》集商业性、情节化、明星效应和视听包装于一身,是陈氏人文电影的改弦易辙之举。但细细品味,它的文化内涵非但不减,甚至更浓,可以说它是陈氏电影中一部“通俗中见斑斓,曲高而和众”的佳作。而他这一类型电影也多数是颇具艺术价值的作品,能够抓住人性的本质,触动观众的心灵。这与他本身的深刻与敏锐不无关系,同时他的阅历和思想也帮助他锻造了这一段属于他的辉煌。
〈二〉命运无常 爱生万相
当然陈凯歌的作品中也不乏以表现爱为主题的情调电影,如《致命温柔》、《和你在一起》以及《无极》都属于此类。它们以表现故事氛围为中心,力求制造一种感觉与情调。
导演陈凯歌在处理这类影片时,经常把不确定的命运因素融入其中。命运无常,在无常的命途中爱却能生出千万种可能与感觉。《致命温柔》散发的就是一种另类的爱与死亡的味道。这部花费近3000万美元的大制作是陈凯歌对于当代人的情感和生死问题的一次探索。女主人公爱丽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与一个陌生的男子相爱,但这种激情的遭遇换来的却是内心的恐惧。奇妙危险的关系,扑朔迷离的爱情,以及对于心灵世界隐秘的探索,陈凯歌试图通过此片来一次文化反思的突围。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较大差异和导演本人对好莱坞制作模式的陌生,导致影片最终没能营造出故事的氛围,更谈不上表现情调主题。
撤离好莱坞之后,陈凯歌受到中国电影朴素风格的影响,拍摄了一部艾略特式的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和你在一起》。影片讲述了一个敏感而沉默的13岁男孩刘小春被望子成龙的老父送往北京深造音乐的经历。这段经历把他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
口,让他面临着情感与前途的选择。一边是父爱重如山,一边是机会千载难逢,陈凯歌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来揭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但他梦想的轨迹却
难以与普通人契合,影片最终在一些稀疏的喝彩声中沉寂。在这部以爱为名的成长寓言中,陈凯歌的问题不在于哲学思考和文化反思,而在于如何让他的电影从曲高和寡走向雅俗共赏。
同样是诠释爱,在《无极》中陈凯歌把他那无法忘怀的理性精神依附到了一个个血肉之躯身上。让人们在驰骋于充满想象力的电影时,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沉重与关怀。这部模糊了时代背景的电影,叙述了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之间在一个所谓的东方无极世界中的爱恨情仇的情感故事。在那个架空的年代里,王妃倾城和奴隶昆仑,大将军光明以及北宫爵无欢,刺客鬼狼上演了一出关于承诺与背叛,家国与爱情的传奇。陈凯歌借想象的翅膀赋予了这些人物理性的因素。电影可以说,用一种戏剧化的人物命运阐释了“自由,爱情,命运”的宏大命题:爱情的极限是放弃,速度的极限是自由,生命的极限是无极。奔放的想象力与严峻理性的结合,使这部感情层次上的浪漫史诗,既有武侠梦幻的辉煌壮丽,又兼具有关命运本身的亦庄亦谐的深沉思考。但陈凯歌对于情调主题的表现显然没有哲学主题那么游刃有余,因此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也遭到了较多的非议。
事实上,无论是表现生死的沉重主题,还是表现爱恨的情调主题,都是陈凯歌借电影之名进行的一次文化思辩。可以说,他的成就也就在于他高度的人文精神,对人的本体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
四 用感性的电影语言来承载理性的思考
崇尚造型,影象表意,在广阔的西北高原和黄河背景上展开诗化的电影叙事,是第五代导演革新电影语言的标志。而理性精神和电影诗情的综合,正是陈凯歌的特点,是他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的鲜明印记。他惯用镜头进行哲理性思辩,不重视讲故事而注重影象表意系统,在艺术上精雕细琢,刻意求工,往往理念胜于情感,思维大于形象。可以说,用感性的电影语言来承载理性的思考,已经成为他电影创作的自觉选择。他试图以诗化的电影语言来创作独特的视觉风格,使观众在视觉的愉悦中进一步挖掘影片的内涵。但这种拍摄风格,对于电影这种大众化艺术形式而言,未免给人曲高和寡之感。
(一)高度舞台化的场景设计
陈凯歌导演一向喜欢用感性的具体场景来完成他原本理性的,抽象的思考,我们已经习惯从陈凯歌电影的某个场景里找寻他复杂的电影语言。他习惯追求古典主义含义
,追求细节的完美和严谨,他的场景设计常常带有舞台化的夸张与美感,充满了象征意义。
如《黄土地》里那场著名的求雨场景。场面非常压抑,无数瘦弱的老农向画面尽头缓缓
奔去,传达出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而在安塞腰鼓那个场景里,镜头的情绪却饱满了许多。漫山遍野,上百名青年农民在兴高采烈地打着腰鼓,尽情释放着欢乐情绪和使不完的力气,好象一切都在瞬间变得生机盎然。这两个场景都象征着力量,但前面一个表现不知所措的盲目的力量,后者则意味着生命本身积极进取的力量。影片显然想通过这两个场景的对比说明,这两者都集中了中华民族性格的成分,是这片黄土地上生成的民族文化的必然两面。
陈凯歌这种带有隐寓意味的象征场景同样出现在了他的佳作《霸王别姬》里。关师傅死在了一个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戏班子情景之中,死在为孩子示范《林冲夜奔》中“八百万禁军教头”的英武造型之时。关师傅的死名副其实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世界的沉沦。此后,便是蝶衣,小楼与张公公的巧遇,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年。解放军进驻北京,以蝶衣,小楼,及张公公同在的画面宣告了既往历史失去了的绵延,被压缩为一个平面。这样舞台化的场景设计使三人的重逢宛如一张见证历史的老照片,风云变幻的苍凉气息在一瞬间被定格。这些有着油画般质地的场景与影片史诗般的格局相当吻合,许多场面令人震撼。
如果说《霸王别姬》让我们看到了陈凯歌对场景的铺张与渲染,那《无极》便把他的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梦幻宏大的场面,不输以视觉称奇的好莱钨大片,同时,东方意境之美又构成了这些视觉奇观的骨架。陈凯歌试图借影象给观众呈现一场磅礴大气,瑰丽雄美的视觉盛宴。翻开《无极》这幅重彩之下的神秘东方魔幻画卷,你会发现有两种风格交汇其中,一种是东方泼墨山水画的浑然大气,一种是西方油画的深刻厚重,前者的空灵和后者的华丽在画卷中完美的融为一体。与《英雄》中的大片用色,力求用几种基础色调展开情节不同,《无极》的着色委实厚重,每个镜头都有种反复描画的感觉,展示了东方特有的神秘。
比如它的开场就很华丽绝伦。让人想起宫崎骏的动画。海棠树下落缨缤纷,天边飘浮着镶有金边的云彩,小女孩赤脚奔跑在尸横遍野的古战场上,小小的蜂鸟扑扇着翅膀在花间觅食。寥寥几个镜头既带出了战场的荒凉也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年幼的倾城是于一无所有中作出选择。之后由黑暗之中升起的“镜花水月”,也是这部电影
场景设计中攫住观众的第一笔惊诧。一个发丝飞扬,衣袂飘飘的满神在“镜花水月”中出现,她轻盈地立于枯木之上,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让小倾城做出生命的选择,然后飘然而逝,宛如一场不真实的梦。这样的
场景,会让人想起一句佛语:诸法无我,一切众生都只是随缘而起的幻像,人生在世,谁也不能超脱欲望的迷阵。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设计可以让你感觉到象征主义的神秘暗语。比如,那“魔幻王城”用一圈圈的圆形设计,让你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走出命运的迷宫,脱不掉生命的不息轮回;而“海棠精舍”那个场景则集中了体现了创作者的爱情理想,那里宁静,自然,洗尽铅华,海棠的飘飘落落让你真真切切地想盛开着相爱,让你期待着海棠花落尽,你爱的人就会回来。而“绝杀之地”那个场景中的鸟笼,更让人觉得,当你自以为把别人关在笼里时,自己不过是被关在了一个更大的笼子里,内心的不自由才是永远的禁锢。这些场景设计很像舞台,有种仪式感,但过于形式主义,把画面拍得姹紫嫣红有时反而会削弱故事的张力。
〈二〉高度角色化的人物造型
众所周知,电影离不开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电影创作的基本任务。但由于创作者的艺术功力有高下之分,对人物的艺术处理有轻重之分,人物形象的塑造便形成了三种基本形态:脸谱形象,性格形象,典型形象。其中典型形象是形象塑造的最高级形态,它不仅作为个性鲜活的形象而吸引人,还能使人从它身上找到某种思想启示。陈凯歌就善于塑造这类典型形象,他总是把思想寄寓于人物的个性之中,让观众去寻找个性后面的“微言大义”,甚至不惜在人物造型上砸下重金来完成角色的塑造。也因为他对人物造型角色化的处理,才使中国电影长廊多了如许光辉夺目,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看罢《霸王别姬》,观众一定无法忘怀那个风华绝代的“戏疯子”程蝶衣。他沉浸在虞姬的角色扮演中不可自拨,因此许多重要的场景中,他均以虞姬的造型亮相。无论是遭受张公公的强暴,袁四爷介入,菊仙投奔,与国民党伤军冲突,京剧改革,甚至“**”场景,他均穿着那身他挚爱的斑斓戏衣。如此角色化的人物造型除了完满“霸王与虞姬”的镜像外还倾注了陈凯歌对蝶衣这个角色个人化的认同。当然这个认同无疑不是针对“女性”命运的,更不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命运而言的,而是建立在程蝶衣作为一个“不疯魔不成活”,具有超越的艺术使命感的艺术家之上的。
同样《无极》里充满魔幻色彩的人物造型也是依造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而
设定的。通过这些造型,我们可以更好地解读人物。先来看这个数字技术成就的“命运女神”,她是电影中一个始终在飞的人,乾坤圈束住发丝向上飘扬。她的形象有一种神秘的飘逸之美,象征着陈凯歌眼中无法参透的命运迷宫;再来看这些华
衣之下隐藏的悲喜灵魂。立于城墙上的倾城,一席五彩薄纱衣裙,眉间点点忧郁之情,修长白净的脖颈上一丝红线牵动起脆弱的命运。风吹起衣襟撩拨着心中无限的无奈。此时的倾城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妃,貌似天仙却苍白如烟。之后,她穿上白色的千羽衣,像一只折翼的飞鸟一样困在金丝笼中,满身华羽却伤痕累累。这时候的她已成为折翼天使的象征,用消瘦的肩膀背负着红颜祸水的罪名,扛起命运的使然。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造型,刻画出倾城在命运与灵魂之间的矛盾。
《无极》中若干个男人形象也各有不同——身穿鲜花盔甲的光明威严庄重,粗布麻衣包裹下的昆仑单纯多情,满脸鬼画符的鬼狼则永远阴暗诡异。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谢霆锋扮演的北宫爵无欢。就霆锋本人而言,他身上有一种流动的可塑性,所以导演大胆地把这个性格小生打造成了深邃多变、凶狠毒辣的谋反佞臣。他们为他设计了多款造型,用服饰的繁复来表现无欢内心的复杂。阴险的北宫爵身着银白色的盔甲,造型繁杂,眉目间隐藏杀机;而身着一身白衫的翩翩少年形象则和人们熟悉的“花无缺”相似,忧郁外型下满脸的明朗英俊。同时无欢的造型里也运用了很多鸟的标志。鸟的含义就是飞,就是完结,没有什么根。这种“无根之美”传达了导演对角色的理解——这个看似权倾朝野的佞臣无欢其实不过是个被命运无端摆布的人物。
导演陈凯歌显然想借助这些视觉芭蕾,让观众品味到影片背后更丰富的意韵和更抽象的思想。但他过分依靠影象系统而淡化情节的作法恐怕是不可取的。对任何一部电影而言,故事都是第一位的,再华丽的影象也无法弥补故事的单薄。
作为一个有着敏感的电影触觉的导演,陈凯歌从未放弃将他的人生哲学和文化思辩注入电影中。他总是试图把自己对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生命与理想的反思以压倒一切的方式体现出来,透露出知识分子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尽管他这种居高临下的精英之气与肆无忌惮的话语知觉,
难免与普通观众拉开距离。但回望整个电影界,又有几人还像他这样沉湎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他的创作态度固然有雕琢之嫌,但也有股超然之气。不管怎样,陈凯歌依然走在路上,我们依然期待他为我们奉上
厚重的电影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