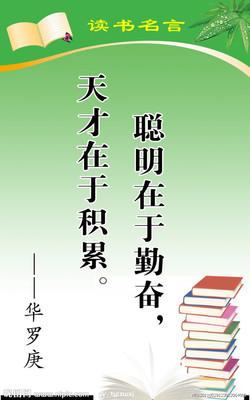2023年4月12日发(作者:创意台灯)摘要 永陵十二神将为永陵地宫中室棺床东西两侧半身圆雕。关于十二神将的真实面目有很多说法。本文通过对于王建父子的思想分析,宗教与世俗中的“十二”,唐五代时期绘画中的十二神,十二神将之为十二生肖神几方面的分析来重新解读永陵十二神将的身份问题。
关键词 永陵 王建 五代 十二神将
引 言
蜀永陵是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地处成都,它的发现纯属偶然。1940年秋,当时的天成铁路局在挖建防空洞时发现砖墙。1942年9月15日由冯汉骥先生主持了永陵的发掘工作。永陵因为规模宏大的陵墓建筑和墓内出土的珍贵文物,而成为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唯一一座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陵墓。
永陵棺床用红砂岩修造,采用须弥座式。棺床四周用高浮雕、半圆雕、减底平雕等手法刻伎乐、龙鸾凤,荷花纹、云气纹等图案。棺床东西两侧各置神像6尊,均为半身雕像,股以下部分埋入地下,像高约50—65厘米,最宽处的约51厘米。十二神像身穿铠甲,或戴冠、或着盔,面朝墓门,双手伸入须弥座底部,作抬扶棺床状。
外公生日祝福语
陵墓中安置十二神的习俗,大多数学者持与道教有关的观点。冯先生认为这组作护持状的十二神将石像与道教的“十二天将”有关,即东一至东六为“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一”;西一至西六为“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认为其起源于阴阳术数家的六壬式法。把“十二天将”置于墓中是为驱除凶恶,守卫墓冢,保护墓主尸体及灵魂。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是道教中的“随斗十二神”,即“征明、河魁、从魁、传送、胜先、小吉、太一、天罡、太冲、功曹、大吉、神后。”置“随斗十二神”于墓中是为了“使无忧患,利护生人”,保护墓主及子孙。并以历代墓内出土的买地券上面多有“随斗十二神”的一些神名为依据。部分学者以王建棺床为须弥座(佛座)式为依据,认为十二神将与佛教文化有关,而将十二神将认为是与佛教有关的十二力士像。还有学者认为十二神将是按王建生前十二宿卫制度设置的。也有学者认为十二神将与“十二生肖”有关。⑴关于这十二神将的真实身份,本文将从以下的论述中进一步剖析。
一、王建父子的思想分析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县)人。他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双亲早丧。王建少时曾以屠牛、贩私盐为业,后入忠武军为卒。王建从军卒到队将再到都头,后因拥众奔蜀,与晋晖等为神策军宿卫。光启二年,唐僖宗幸兴元,让王建为清道使,背负玉玺随行。行至
当泽驿时,“李昌符焚栈道,栈道几断,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寝,即觉,涕泣,解御衣赐之。”⑵王建由此得到僖宗重视,但是,僖宗的所作所为在王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更是深的多。
王建即皇帝位后,“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中书门下事,唐袭为枢密使,郑骞为御使中丞,张格、王锴皆为翰林学士,周博雅为成都尹。蜀侍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浚之子也。建渭之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宾等百余人,并见信用。”⑶由此可见,王建是以唐帝尤其是僖宗作为自己的榜样的。
唐王朝崇道重佛的观念影响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平民出身又做了皇帝的王建自然也不能获免它的影响。王建曾赐号道士杜光庭为“天师”,并命其为太子之师。王建曾命创建龙华禅院,请贯休做主持,并赐号“禅月大师”。王建在成都重建、新建了众多的寺观,这都是与王建自身崇道敬佛的思想以及以唐帝为榜样的心理分不开的。
综合来看蜀国内的宗教形势,应是道教占了上风的,这与著名道士杜光庭的努力分不开的。“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曰:‘臣观两街之众,道听途说,一时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远,且困于风尘,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曰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之为天师。”⑷又“元膺……年十七,为皇太子……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⑸虽然王元膺为卫兵所杀,郑王宗衍(即王衍)为太子,并最终做了皇帝。但是,从王衍所做之事来看,他尊崇道教比王建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也是受了杜光庭影响的。王衍为帝后,“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⑹“常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⑺又“
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⑻由此可见,王蜀以李唐为榜样是很明显的。永陵是在王建生前便建造完毕的,但是并不排除王衍继位后的一些后期工程。因此,王建父子,特别是王建的思想对于解读十二神将至关重要。即十二神将与道教文化将有莫大的联系。
二、宗教与世俗中的“十二”
永陵除地宫外,在当时还有大规模的地面陵庙建筑。不仅在永陵地宫的棺床是须弥座式,并且在永陵陵区内还置有寺院,那么永陵是否是以佛教为依据建造的呢?宋真宗奉道教是极为有名的,在他的永定陵建有永定禅院。所以,陵区建寺院只不过是承继前制罢了,此前的北魏永固陵便建有佛堂。至于须弥座式的棺床在严格意义上与佛教的须弥座还有不同,其图案、形制皆有其独特的特点。另外,早期道教造像多有受佛教造像的影响,一些天尊像也是刻于须弥座或莲花宝座之上。因此依据持十二神将为十二力士之说是难以立足的。
我们再从佛教与“十二神将”有关的文化谈起。佛教有十二神将之说,他们的身份是药师佛的侍卫。据《药师经》讲,药师佛曾发过十二大愿,要满足众生一切愿望,拔除众生一切苦。药王殿的药师佛除了胁持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外,旁侍十二神将。“这十二员大将全部都顶盔擐甲手持武器,按十二地支瓠子的做法
生肖配合昼夜十二时辰轮流值班。十二生肖往往在头盔上显现”。⑼药师十二神将,又称十二神明王。具体神名为“招杜罗神将(子神),昆伽罗神将(丑神),宫昆罗神将(寅神),伐折罗神将(卯神),迷企罗神将(辰神),宴底罗神将(巳神),摩尼罗神将(午神),珊底罗神将(未神),因达罗神将(亥神)”,另一种说法是以宫昆罗神将配子,以伐折罗神将配丑,依次类推。即以寅为首,还是以子为首的问题。由此可推知,佛教十二神将与十二地支的结合有后加上去的嫌疑。莫高窟初唐第220窟药师经变中,十二神将“身穿甲胄,头戴宝冠,宝冠饰以动物肖像,现在可视的有蛇、兔、虎邮箱登录
等动物,这是以十二生肖对应十二神将。”⑽这是造像中的例子。
党员个人思想汇报
郭沫若先生的《释干支》列举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的十二生肖,其中引《大集经虚空盼净目品》列举印度的十二生肖名单为“鼠、牛、狮子、兔、龙、毒蛇、马、羊、猕猴、鸡、犬、猪。”北凉时期所译的《大集经》卷二十三讲在佛经所说的四大洲之外的大海中各有神仙,每方山中有三神窟,每神窟中有一神兽。现简列于
下:南海琉璃山(山名“潮”),三窟为“种种色”窟(居住毒蛇),“无死”窟(居住马),“善住”窟(居住羊);西海玻璃山,三窟为“上色”窟(居住猕猴),“誓愿”窟(居住鸡),“法麻”窟(居住犬);北海银山(山名“菩萨月”),三窟为“金刚”窟(居住猪),“香功德”窟(居住鼠),“高功德”窟(居住牛);东海金山(山名“功德相”),三窟为“明星”窟(居住狮子),“净道”窟(居住兔子),“喜乐”窟(居住龙)。《大集经》中十二生肖的方位分布同中国古代十二生辰是一致的。隋代智者大师《摩河止观》讲“魔事”,说到《大集经》十二生肖及三十六神兽,神兽名单与六朝式盘的三十六基本相同。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中“论三十六禽”认为三十六禽十二属即是十二生肖,加上二十四“配禽”组成。由此可知,无论是药师佛十二神将,还是十二窟神,虽是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十二神将,但是在传入汉地逐渐被中国文化同化,可以与十二生肖即十二地支一体而论。佛教的护法神中亦有欲界“十二天主”之说。欲界为三界之一,欲界十二天按曼陀罗之配位为“大自在天、帝释天、尖天、梵天、日天、毗沙门天、焰魔天、地天、月天、风天、水天、罗刹天。”欲界十二天主的形象一般为头戴五梁冠,身穿袍服,足蹬云履,双手执圭的帝王形象。所以永陵十二神将与“十二天主”的形象最没有吻合之处的。
随着佛经的翻译,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也在隋唐时期进入中国。当时所翻译黄道十二宫名并不一致。就现在所知,隋代耶连提耶舍所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出现的黄道十二宫名最早。其次为唐代不空于758年译出的《文殊师利普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简称《宿曜经》),此外还有金俱吒于806年译出的《七曜禳灾法》等。⑾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到宋代才逐渐同一。1059年刊行的《蟹谱》引《释典》曰:“十二星宫有巨蟹焉”。这说明黄道十二宫在北宋已经是广为流传。那么,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正是十二星宫广为传播的时期,如此一来,十二神将会不会是十二宫神的人格化呢?1971年河北宣化发现的葬于1116年的辽代古墓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墓室穹隆圆顶上的彩色星图,内圈为黄道十二宫,其外一圈为中国的二十八星宿,最外一圈为头顶动白醋泡黑豆
物形象的十二生肖神像。黄道十二宫神虽然已经融入中国风格,如双子宫,画为两人拱手模样,左为男子,戴软巾,紫色长袍短襦,右为女子,高发髻蓝襦红袍。又如室女宫,画为女子站立,一红襦蓝袍,一蓝襦红袍,皆双手拱于胸前
。摩羯宫,画为龙首鱼身兽,并带有翅膀。另外如敦煌莫高窟第61洞的黄道十二宫中的双子宫,也是画为两人,只不过是幼童模样而已。这一切都说明十二宫还没有完全人格化为十二位神君的模样。而辽墓中与之相对的十二生肖神像已经是完全成熟的神像。十二宫神像的形象在明代宝宁寺水陆画中已经完全成熟,并明显的受十二生肖神像的影响。可以推知,在前蜀不可能塑造十二神将来指代十二宫神。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中的十二神将有数组,但是他们要么是原始宗教的遗留,要么是神仙家的创说,多数早于道教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在道教发展进程中进一步人格化罢了。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些神将时不能脱离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十二”是一个成数。《左传哀公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又《周礼春官冯相氏》曰:“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可见“十二”是与中国古人观天文,制历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十二”真是“天之大数”。中国向有地分九州之说,但是古人为了天地相应,便又制造出十二洲之说。《尚书舜典》:“肇十有二洲,封十有二山,浚川。”姓有有十二之说,《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二人,为十二姓。”又有《后汉书荀爽传》:“故天子娶十二女,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十二”做为成数,可见影响中国文化之深。所以汉代星占术所谓分野之说,天星对应州国,在天称“十二分星”,在地称“十二分野”,是顺理成章的。此后,“十二”在道教文化中也成了重要内容。
冯先生认为十二神将为道教的“十二天将”,即“天一,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我认为是有所不妥的。首先在道教经典的神仙组合中,这种组合的提法几乎是没有的。它是起源与阴阳术数家的六壬式法,并只限于术数范围内。虽然道教收录了许多术数书籍,但是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却并不存在这样的组合。
“十二天将”起自天文星象,司马迁在其《史记天官书》中说:“天官十有二”,并列其名字如上。后世多以“十二天将”作为星象占卜的代名词,最早时代现不可考。有托名诸葛亮著的《奇门遁甲》应是后人伪作。唐代王希明的《太乙金镜式经》宋代杨惟德的《六壬神定经释天官二十九》中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天官与方位对应的星占法。可知六壬算法在五代时期
已广为流传。那么为什么永陵中的十二神将不会是“十二天将”呢?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曰:“天乙在紫微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斗战,知人之吉凶者也。”可知天乙(即天一)之神是极为尊贵的,道教星辰神谱系中有太乙、太一,应是天乙神的别名。勾陈是为“天乙大将军”,又变为道教四御之一,称为勾陈大帝。《星经》曰:“勾陈六星在五帝下,为后宫,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军将军,又主三公。”所以勾陈也指后宫。《晋书.天文志》曰:“勾陈六星,皆在紫宫中。……勾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圣御君灵,执万神图。”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组合早于道教,称为“四象”,又称“四灵”。四象应是与二十八星宿同时出现的,其最初只是表天文意义。《书传》曰:“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又《史论天官书》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索引》引《尔雅》:“大辰,房,心,尾也”。1987年在河南濮阳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早期墓,幕中即有蚌壳摆塑成的龙虎形象。随着五行五方五色之说的流行,四象按方位着色,分别成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汉瓦当上多有造型生动的四象形象,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漆画青龙白虎二十星宿图,以及后世许多墓室壁画中的四象形象,只是把四象作为天的象征和避凶趋吉的符号。四象在汉时开始神化,如《后汉书王梁传》:“《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李贤注云:“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和体。”《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帝览嬉》:“北方玄武之所生……镇北方,生风雨。”道教吸收四象最初为护法神。如《抱朴子杂应》描述太上老君形象时说:“左有二十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四象神的人格化也是在汉代,如汉代藏纬书《河图》中曰:“北方黑帝,体为玄武,其人尖面兑头,深目厚耳。”限于篇幅,对于其另外六神将的来历身份不一一介绍,总而言之,“十二天官”的地位尊贵,作为尊崇道教的皇帝王建,并有杜光庭这样的道教大师在旁,是不会不了解道教的,所以不可能让“十二天官”来为他抬棺床的。
对于把永陵十二神将认为是“随斗十二神”,即“征明、河魁、从魁、传送、胜先、小吉、太一、天罡、太冲、功曹、大吉、神后”的说法也不可信。杨惟德《六壬神定经释月将等二十三》
曰:“正月将征明,《金膺经》曰:‘建寅之月,阳气始达,征召万物而明理之,故曰征明。’二月天魁,《金膺经》曰:‘建卯之月,万物皆迷,各求根本,以类含聚,故曰天魁’。三月将从魁,《金膺经》曰:‘建辰之月,万物皆长,枝蕊花叶,从根本而出,故曰从魁。……天之运转,含宿之所至,以立神名。天之十二神,运移无穷;地之十二辰,以静而待之。或有相生,或有相克,吉凶之本,不可不知。上克下,忧他人;下克上,忧己身;上克下,忧妇人;下克上,忧男子;王气所胜,忧县官;相气所胜,忧财物;死气所胜,忧死丧;囚气所胜,忧囚系;体气所胜,忧疾病,余皆仿此例。十二月将除二月将天魁被称为河魁,六月将胜光被称为胜先,七月将太乙被称为太一,五月将与六月将顺序颠倒外,与“随斗十二神”基本相同的。可以说“随斗十二神”即是“十二月将”。“随斗十二神”是和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天神,其地位也相当高,也不可能出现在永陵墓中为抬棺神将。另外,“随斗十二神”与十二地支相配,唐墓室常配十二生肖神,而不会选用“随斗十二神”。至于历代墓内出土的买地券上面,多有“随斗十二神”一些神名,这可能是与“十二月将”配十二地支纪月份有关,也可能是与配十二分野纪区域有关,更有可能是与趋吉避凶有关,此文不细论。综合来说,并无一墓中出现全部“随斗十二神”的记录,因此,永陵十二神将也并非“随斗十二神”。
十二地支是一组与“十二”有关的中国极为古老的时间概念。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结合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最深处,这注定了它的被神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泰简《曰书》中的《盗者》和八十年代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泰简《曰书》中的《亡盗》都发现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的名单。虽然和现在的十二生肖稍有出入,但大致相同。十二月神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被考古界定为楚帛书的近于正方的十二月神图。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所记月名可相互考释,每面画三个神物,多作身首肢体拼含形状。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曰“以四兽验之,十二辰之禽效之”。十二辰之禽即指十二生肖。大概在此时,阴阳术数家们便把十二生肖与人生肖联系了起来,此风盛于南北朝时。南朝人沈炯曾写过一首《十二属》,即说十二生肖之诗。唐代《事始》:“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名兽属之,”韩愈《毛颖传》:“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柳宗元《三戒》:“鼠,子神”;明代于慎行《毂山笔尘》:“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属也。”隋
唐时,十二支已经完全人格神化,并被吸入道教神系。十二生肖并被制作生肖佣为死者陪葬,所以十二神将有可能是十二支神。但是生肖佣要麽为人身兽首,要麽为怀抱生肖,而十二神将并无生肖标志呢?这问题将在第四节中具体讨论。
在中国与数字有关的神系里,四象、十二地支、二十八星宿、三十六禽、六十甲子皆是既与动物形象联系又与天文联系的神仙组合。但是,除了十二地支,在这里面还暗含了两组与“十二”有关的组合。这两个组合都与岁星有关。《山海经海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有十二。”又《山海经大荒西经》:“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即讲岁星的轨道周期。木星沿轨道饶行一周需要11.86年。古人先是以岁星纪年,如《左传襄公三十年》“岁在降娄”、“岁在诹訾”。但后来发现岁星纪年的欠精确性,于是另造一理想天体即太岁,用假想中太岁所处十二辰的位置来纪年,即太岁纪年。战国时期,人们并不用地支纪年,而另备一套十二年名,称岁阴。十天干也配了岁阳。但是这些年名并没有被用多久,便被干支纪年取代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循环相配,共得六十对,用此纪年,称为“六十甲子”。道教提出“本命”论,即凡本人的出生年六十甲子干支之年,称本命元辰、本命年。道教认为六十甲子即六十星宿,后来人格化为六十尊元辰星宿神。道教称太岁为岁神,又名岁星、顺星。《月令广义岁令二》:“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凡吉事勿冲之,凶事勿犯之,凡修造方向等事尤慎避。又如生产,最忌向太岁方坐,又忌于太岁方倾秽水埋私胞之类。”《协纪辩方》卷三引《神枢经》:“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岁成功。……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选宅舍,筑垒墙垣,并须回避。”古时人们习惯上只重视岁阴(即十二地支),故有“太岁”十二年一循环之说。地支有方位,“太岁”因而也有方位,所以由此民间产生许多禁忌,以太岁所在方为凶,忌兴土木或迁徙房室等。《土风录》云:“术家以太岁为大将军,动土迁徙者必避其方。”太岁神的奉祀在南北朝已经兴盛。据杜佑《通典》载,北魏道武帝(386-409年在位)时,已立“神岁十二”(即十二位太岁神)专祀。所以以十二太岁神为十二神将也不大可能。
同是六十太岁神中的六丁六甲的地位似乎要比其他太岁神有些不同。十天干中,甲居奇数位,属阳;丁居偶数位,属阴。六十甲子中,与甲配合的地支,均为居奇数位而属
阳的地支;与丁所配合的地支,均居偶数而属阴。六甲神称阳神玉男,六丁神称阴神玉女。道教典籍说,六丁甲是为天帝所役使的十二神将;道士可用符《*》召请以供驱使。《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畅性聪惠,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噩梦,从官六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卡筮。”注曰:“六丁,谓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则丁卯为神;甲寅旬中,则丁巳为神之类也。”唐韩愈《调张籍》诗曰:“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所以唐时六丁六甲已经人格神化。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扶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这座紫府观北宋时称为醴泉观,像没亦醴泉旧制。“所以永陵十二神将也不可能是六丁六甲神像。
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即“义儿军”的出现。《新五代史》曾为此专门列有《义儿传》,这在中国纪传体史书中亦为一大奇事。史载王建有义儿一百二十人,他们皆因战功被赐姓王。有的学者认为前蜀政权本质上是一个政权,政权的核心成员也以为主。有如此多的义儿,便认为十二神将可能为当时象征,这些石刻武士是按王建生前十二宿卫制度设置的。⑿这种说法也有欠妥之处。
首先从十二神将的造型来看,既具有写实主义的风格,又极具浪漫主义情调。特别是西一的面目,两只下齿裸露,明显是神将的模样,并非具体形象。结合王建像的塑造风格,如是其义儿军的象征,应以具体形象综合多人形象而塑造。另外,古稀之年的王建为立储之事大费脑筋,永平五年(915)宫廷大火时,任诸军都指挥使的王建义子王宗侃等人率兵救火,王建却紧闭宫门,任后宫珍宝付之一炬。可见,王建与义子们的关系并不能简单视之。
称王蜀政权为政权,并不确切。王建本人虽属,但是却非常重贤纳才。《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称:“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赋,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放其僭号,所用皆康名臣也族……”前蜀是最为承袭唐代典章制度及文化风韵的,所以以十二神将,为象征之说也难以确定。
三、唐五代时期绘画与雕刻中的十二神像
本节重点谈唐五代时期绘画与雕刻中的十二神像形象,但是为了追溯其根源,艺术创作时期将不止以唐为上限,内容也不以十二神为限,为比较起见,其他组合一并论及。
出土的艺术品中除上节谈到的楚帛画十二神图为最早,汉墓还出土了许多十二生肖砖,开启了以十二生肖形象制造明器的先例。1978年发
掘的河常见的近义词
南省洛阳市金谷圆村东墓,是新莽地皇年间的墓葬。墓后室东壁,西壁,北壁三面上方之拱眼壁上,共绘有十二幅神百家讲坛岳飞
怪像。东壁南起第一幅画一人面鸟身怪像,顶戴冠,额下系绶带,饰羽翎的鸟尾向上跷卷,作昂首展翅将奋进壮,周围饰有朱红色的流云纹。《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东方句芒,鸟身人面”,所以所以发掘者称之为“句芒像”。第二幅画一人面虎身怪像,顶戴冠,肩胛处生羽翼。虎颈、背、尾翼皆涂朱黄色,服、爪敷白色,《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西方蓐收”有“人面、虎爪、白毛”之特征,蓐收既是金神,又是司日之神。发掘者称此幅为“蓐收像”。……类似形象曾见于洛阳烧沟及二九五区出土的西汉晚期彩绘陶壶上。1922年《杭州府志》引《杭俗遗风记》,每年立春时节至那杭州西湖边的吴山迎奉春神句芒,是一项古老的风俗,“吴山有太岁庙,大殿中供至德帝君,两旁列供六十花甲子值年太岁,殿左供本年甲子太岁一位,殿右供句芒之神”。“句芒”等这些依托《山海经》的老神砥随着新的神砥的出现,出现了分化,其在墓中的地位,很快便被“十二辰”取代。
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是1979年至1981年发掘的北齐武帝元年时的墓。墓室四壁上栏按子午方位画兽形十二辰,其上绘有天象的墓室顶部。兽形生效前后有神兽围护,造型准确简练。娄睿墓是迄今为十二生肖形诸墓较早的发现。隋唐以来,墓室多置十二生肖俑,如十二生肖出现较早的湖南长沙威嘉出土的初唐时期的唐墓,此风沿袭至宋代。其中也有以雕刻形象出现的。如1987年发掘的福建尤溪县团结乡麻洋的宋墓,其墓东西两壁共绘有十二个头戴动物属相冠的人物,以代表十二生肖。十二生肖着士人服,执笏,旁黑书地支字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剑阁鹤鸣山“一群奇观”龛中的十二神将浮雕。这组浮雕雕刻于晚唐时期,剑阁在唐代置普安郡,故石窟题额为“一郡奇观”。龛内主雕已于1947年被剜盗走,所以十二生肖神将的身份也并未确定。神将应是护法神,左右各刻六人,身高在93到97 厘米之间。头部簇拥煊赫,面容肃穆。其右壁雕神将六位,鬼魔两个,神将皆蓄发,着披肩,着履,其中五位戴铁盔.前两位着战裙,穿软底快靴,右面的一位手执方锏,盔上有尖顶,似为指挥形象,其双脚踏在一男鬼肩上。后面四人,其中一人手执法器,最后一位长发蓬松,胡髭上翘,双眼圆瞪,似为唐时北方少数民族模样。左壁雕神将六位,魔鬼两个,与右壁相互呼应。龛窟内正面左右各有一尊道教神仙造像,手捧戒尺,宽大的两袖下垂,与下肢浑然一
体.整个窟龛浮雕左右对称,造型朴拙含蓄,艺术手法简括洗练。十二神将的形象与永陵十二神将颇有暗合之处。杜光庭曾到剑阁,应该见到过这组雕像,剑阁处于王建治内,甚至不排除王建见过这组雕像的可能性。这组雕像的身份也不确定,并不能给予我们分析永陵十二神将更多的帮助,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永陵十二神将与道教有莫大的关系。
在记录北宋御府藏画的《宣和画谱》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一些记录,即“道释”画像在唐以前是佛教画像多于道教画像。前期的“道释”画像多为单像,如陆探徽“托塔李天王图一、北门天王图一、天王图一”。南梁的张僧繇多画组合道释像,他不仅画了“佛十弟子图一、十六罗汉像之一、十高僧像图一”,还画了“九曜像之一、镇星像一”、“五星二十八宿像一”。而与“十二”有关的图画有唐代阎立本的“十二真君像一”和“十二神符一”,记唐张素卿曾画《十二真君像》,如此而已,这些真君像明显不会是神将模样。《宣和画谱》中我们常见到九曜、五星、二十八星宿、镇星(岁星)、辰星(二十八星宿之一心宿)、寿星、六甲神、六丁六甲神,而没有十二支神。虽然寿星是十二星辰之一,在十二支为辰,但是在神仙体系中寿星是独立的,他的地位远比十二支神要高。唐代周肪曾画“六丁六甲神像四”,六丁六甲神共为十二神,但是我们并未见其画像是否为十二男性神将,所以只能以文献为准,认为六丁神为女神模样,见第二节。《宣和画谱》的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十二支神的地位要比九曜五星等神的地位要小,因为与这些神同样被画上画面的多为佛、菩萨、天帝、真君、天王等,虽然十二支与六十甲子及其中的六丁、六甲记时间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是在道教神仙体系中他们是并行存在的,并存在严格的等级区别。
《益州名画录》是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区域的画像和壁画创作的记录,黄休复把唐肃宗乾元初年(758)至宋太祖乾德(963--967)近二百年间四川画家,自孙位至邱文晓五十八位的小传及手笔留寺者二十七处、写真二十二处记录下来,使我们更能清楚的了解十世纪前后成都地区的绘画,特别是壁画情况,在黄休复罗列的这些画家的画作中,与“十二”有关的有神格赵公佑的“药师院师堂内四天王并十二神”,范琼的“圣兴寺大殿东北二方天王药师,十二神”,妙格张素卿的“十二溪女”,“又于简州开元观画容成子、董仲舒、严君华、李阿、马自然、葛玄、长寿仙、黄初平、葛永贵、窦子明、左慈、苏眈,十二仙人像“,能格李寿仪模写张素卿“十
二仙君一堂”,皆非十二神将形象。六十甲子等神像也多有画幅。可见,十二生肖神形象并非出现在绘画及壁画中,而出现在墓室壁画中是有其等级原因的。后世如白云观十二生肖壁不在此论。
四、十二神将之为十二生肖神
上节谈到汉墓时墓中所有十二生肖砖,至北齐娄睿墓出土增形十二壁画,而隋唐时便多以十二生肖俑做为明器了。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群之中的十号墓为北魏墓,其中的的生肖俑为现在知道的最早者。唐宋时期十二生肖俑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格,如《大汉原陵密葬经明器神煞篇》载:“天子山陵用明器神煞法……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中的明器……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⒀较早的如前面提到的初唐时期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十二生肖俑在河南洛阳、河北邢台、陕西西安、陕西铜川、皆有出土,时间有盛唐、中唐和晚唐。十二生肖俑的形象多为彩绘人身兽首形象。武汉出土的墓室中的十二生肖俑是人身怀抱动物。即其统一特点是十二生肖俑皆有十二生肖为标志,或兽首人身,或人身怀抱生肖,或头盔上有生肖形象。
吴汉月墓位于杭州市郊施家山南坡。墓室四壁上皆浮雕一条由宝相花组成的带装花边,中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底部为十二生肖像。后室顶盖阴面还刻有二十八星宿图。此墓篮球场
是五代吴越墓的代表。十二生肖神像皆为人形手托生肖兽像。福建莲花峰1965年发掘的五代时期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墓亦有人形兽首的十二生肖俑。《五代史闽世家》称闽国家统治者既笃信佛教又好道教之说,刘华墓志铭亦云刘华生前“留心佛殿,赏观道书”。宋代李傅《五代会要》称:“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十二时即指十二生肖俑。
如果说十二神将为十二生肖神,那么就要解决第二节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十二生肖并无生肖标志呢?我们首先从永陵出土的一件稀世之形—谥宝(即帝王在阴宅使用的印玺)谈起。古代帝王印玺的纽通常都雕刻为龙形,而王建谥宝纽却雕成了兔头龙身的一个奇特形象。王建生于公元847年即丁卯年,而其登基亦是其六十岁时的丁卯年,并据宋人记载,王建称帝paint过去式
前,蜀中流传“兔子上金床”的歌谣。可见,王建与兔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其谥宝雕成兔头龙身。那么既然王建把自己与兔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王建永陵中自然不会出现带生肖头像的俑或石像,所以十二神将并无生肖标志。
古人以十二生肖置于墓中。最初只有纪星、纪时之功用,后来渐成为永享富贵的一
种愿望。十二生肖指代十二时,自己时时可以保持自己的所得。作为帝王的王建更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下去,所以选十二生肖神来为自己抬棺床是不无深意的。十二生肖不仅纪时,还表达方位,亦可深化十二分野的象征。可以解释为王建想统一天下,千秋万代保持王代江山的意愿。
十二神将左右各位六位,排列却是:“一 —— 二—— 二 —— 一”的位置,虽然隐含有建筑结构的原理在内,却也另含有十二生肖的方位及生克关系在内的。另外,十二神将还有一个特点,即东一、东二、东五、西一、西三、西五戴盔,东二、东四、东六、西二、西四、西六为戴冠。即奇术为阳,偶数为阴。我们前面谈到这十二神像将不可能为六丁六甲神的原因,十二生肖即十二地支也是暗含阴阳关系的,其相互之间的配合也不是简单的“子、丑、寅、卯……”的顺序排列。
十二神将与二十四伎乐形成呼应关系,一阴一阳,一刚一柔。有学者认为二十四伎乐为前蜀宫廷乐队的形式,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左右应分开来看,右边为宫廷音乐,同时也为道乐,左边为军队音乐,即二十四伎乐本身亦有阴阳刚柔之属,但就整体而言而非单个而论。十二神将与二十四伎乐,相合为三十六禽神,即十二生肖加二十四配禽。上海博物馆藏六朝晚期铜式,地盘最外一圈刻三十六禽,每面九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称:“禽虫之类,名数甚多,今解三十六者,盖与六甲之数,《式经》所用也”。
永陵的选址也是风水学的一个典型,永陵整体都体现了王建的思想。永陵处于成都城的西北方,距离当时的大西门(即乾正门)外不到一公里,为一处高于城内的台地,西北方属于“乾”地,居君位。永陵址是经当时著名文士,曾任“成都尹”的周庠(字博雅)精心选择后,经群臣议定(王建是参与决定的)一块风水宝地,北宋路振《九国志周博雅传》载:“建薨,葬永陵,博雅议山陵事”。周庠不仅参与选址,还是王建葬事的主持者之一。所以说永陵从选址到建筑再到内部建筑及随葬物品应是出于统一考虑的。从侧面也说明王建对自己的身后事是极为重视的,并在细节方面也是极为重视的。
1990年出土的据永陵数百米的前蜀后妃墓,可与永陵相比较分析一些问题。据推测这座后妃墓应是王建皇后周氏的陵墓。我认为这是对的。首先,此墓处于永陵西南,是为“坤”位,以配“乾”位。玉册也是证明其级别较为尊贵,应为皇后的位置,棺床及神将皆类永陵。此墓室除了墓主石雕像之外,另有四只石雕像,棺床虽也为须弥座式,但束腰部分无
伎乐,仅饰花卉。这四位半身圆雕的神将是什么身份呢?四尊神将长发披肩,头戴冠,身着甲,表现出威严的神态。是不是《五代会要》中的“四神”呢?四神的具体解释是那四位呢?又是一连串的问题。早期墓室中多出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而随着其人格化过程中地位提高,不会出现为抬棺力士的形象。那么,另外一组护法神,“四值功曹”,即“年值功曹、月值功曹、日值功曹、时值功曹,最有可能担当此任”。“功曹”本为汉代州郡的长官的帮手,有功曹和功曹史,为考查功劳,掌管功劳薄之职。北齐以后称功曹参军。到唐在府的称功曹参军,在州的则称司力参军。道教的记录功劳的官也称功曹,即四值功曹。他们除了记功劳外,还是守护神将。并且年、月、日、时之组合,亦有使江山万年之意,功曹护棺,亦有升仙之望。所以后妃墓中的四位神将可认为是四值功曹。
结 论
王建虽是一介武人,但是早年追随唐帝的记忆使他难以忘怀,以唐王朝为梦想,以唐帝为榜样的情结。蜀地富强安定的环境不仅使众多的文人学士避难于此,并使唐朝宗教领袖、艺术大师也汇集于此。川蜀本就人杰地灵,这不仅是王蜀的文化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道光芒,也使他它凝结在这座帝王墓——永陵中。
唐代四川地区的石刻艺术达到非常高的标准,如广元千佛崖、夹江千佛崖、乐山大佛等等,永陵的雕刻雕刻更充分的展现出精致流畅、自由豪迈的风格。
永陵使二神将的身份本就已有数说,但是并不能完全取信于世。本文从多角度来解读十二神将的身份问题,但鉴于资料有限,也难以确下定论。就目前所得资料来讲,我认为十二神像将最有可能是十二元辰神,即十二生肖神。如果有新的资料证明宋以前六丁六甲神将为十二男神形象,则又另论。
注释:
⑴成都永陵博物馆编:《走进永陵》 天地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192—192页
⑵[宋] 欧阳修撰 徐元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第513页
⑶.同上 第516页
⑷.[宋]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63页
⑸.同2 第157页
⑹.同2 第518页
⑺.同2 第519页
⑻.同2 第519页
⑼.白话文:《汉代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52页
⑽.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⑾见夏鼎:《从重化陵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⑿.见1 第192页
⒀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
的十二生肖佣》《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参考书目:
《走近永陵》,成都永陵博物馆编,天地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成都永陵博物馆》,张西平编著 巴蜀书社,1999年5月第一版
《生肖与中国文化》吴裕成著 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 [宋]徐无党注 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一版
《中国道教诸神》马书田著 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道教神仙信仰》张兴发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益州名画录.》[宋] 黄休复 人民美术出版社(合订本)1964年5月第1版
《道教美术史话》王宜峨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
《宣和画谱》岳二泽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宋人画评》云告泽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宋辽金画家史料》陈高华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3 月第1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上海书厦出版社 2002年8 月第1版
《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6月第1版
《中国道教音乐简史》胡军著 华龄出版社 2000年8月第1版
《云笈七 》[宋]张军房编 李永晟点校 中华书局 2003年2月第1版
《佛教手册》宽忍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中国古代算命术》洪丕漠 姜玉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12月第2版
《中华杂经集成》吴龙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1版
《三命通会》赵金生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1版
《金函玉镜奇门遁甲秘籍全书》传诸葛亮等著 青海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赵尚志
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宗教》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2年4月第1版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墓室壁画》 宿白 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9年5月第1版
《中国历代艺术雕塑编》 刘玉山 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1版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