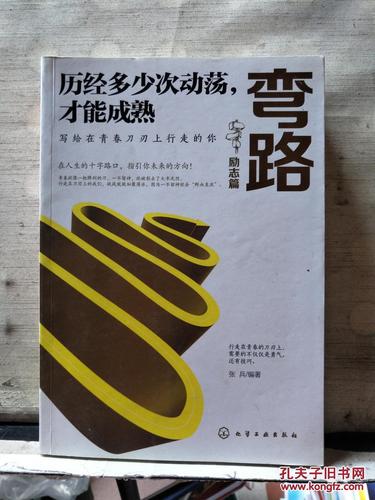
从十驾斋说到钱大昕及其《全集》
虞万里
荀子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钱大昕十驾斋之名盖取意于
此。《年谱》不载是斋名取自何年,唯于乾隆三十三年下云:“始买城中孩儿桥弄宅,名其
堂曰潜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书扁。”时钱氏四十一岁。自后编著之诗文集、金石文跋尾等
均题此名。《清史稿吴凌云传》谓凌云“尝假馆钱大昕孱守斋,尽读所藏书”,又见故宫
博物院所藏钱氏关于吴彩鸾书《切韵》跋记一则,下署“甲寅三月八日竹汀居士书于孱守斋”。
此甲寅乃1794年,时钱氏已六十六岁。至晚年所定稿之《养新录》却冠以“十驾斋”之名,
自序云:“今年逾七十,学不加进,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书名取其先大父依张子厚
《咏芭蕉》句榜于读书堂之“养新”二字,合己斋名而成。是“十驾斋”当晚年所名。由此
可见,钱氏书斋名字依次有潜研堂,孱守斋,十驾斋,或为同一室之异名,或为不同斋室之
名。观钱氏等身之著作及学术所臻之境,固是潜心专研之结果,谓乃“驽马十驾”所得所至,
似谦虚太过,然细察其行事、思想及治学方法,却颇耐人寻味。
钱氏周岁即能认字,三岁能诵堂上扁联,五岁受经书,十岁学为八股文。十三岁应童子
试,为林上梓所勉。十五复应童子试,为内阁学士刘藻所激赏,谓“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
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旋与王鸣盛订交,并为王之父虚亭先生相中,许以婚姻。其后
科试、岁试,多在一等。十九岁读李延寿《南北史》,撮故事为《南北史隽》一册。二十二
岁入紫阳书院肄业,王艮斋先生阅其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已,诧为“此天下才也”。
巡抚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钱氏下笔千言,致院中名宿莫不敛手敬之。如此经
历,宜其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幼慧”之誉,“神童”之目。钱氏有诗记幼时之娱乐云:“人
日元宵兴不孤,小时了了记欢娱。烧灯巧解藏头谜,对局偷拈谒选图。”(《初春怀乡杂咏》)
用“小时了了”之典,是冲和老境对儿时实况的一种谦虚的追忆。
清初以讫乾嘉,学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学,提倡实事求是,陵唐追汉,于音韵、训诂、
名物制度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一些学者也就此自视甚高,如戴东原、段玉裁、王鸣盛、
汪中等。唯钱大昕,其功力、学识堪称一流,造诣、成就与惠栋、戴震相侔而自成一派,治
学范围之广又实过之,但其平心静气、谨慎谦雅之风范,却戛戛独标一帜圣诞节的来源 ,与众不同。
戴震曾云:“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是戴氏俨然以第一人自居。检《戴震全
书》,提及钱氏者仅两处,一是钱氏与其论及怀疑《古文尚书》乃王肃私为之,一是序段玉
裁《六书音均表》时连及钱氏曾为段氏序《诗经韵谱》。而钱氏,自一见戴震,即对其推崇
备至,目为天下奇才,致书与之讨论学问,且向秦惠田推荐戴氏。及戴震殁,键盘手 又为作传,表
揭其学术成就。钱与友朋书云:“予少与海内士大夫游,所见习于数者,无如戴东原氏。东
原殁,其学无传。”(《赠谈阶平序》)崇敬思慕之情益于言表。
王鸣盛是钱氏的同乡,少时即订交,同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同中进士。钱
大昕曾说:“予与西沚总角交,予又妻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
疑义,质难无虚日。”(《西沚先生墓志》)两人年齿相近,经历相仿,志趣相投。王作《十
七史商榷》,钱著《廿二史考异》,两书与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同为乾嘉年间史学名著。
尤应补上一笔的是,两人都极其聪颖。“相传宫詹少时,一日在塾检阅历书,适光禄至,因
谓曰:‘吾与若偕读,能先默诵者为胜。’宫詹允之。光禄甫读一遍,已能背诵,宫詹读三
遍而始能之,于是同塾之人咸优光禄而绌宫詹。及翌日,请再试之,宫詹一字不误,光禄则
间有讹舛,以是知二人固无分轩轾也”。(《清稗类钞异禀类》)但两人的性格却是一傲
慢,一恭谦。惠栋为吴派经学大师,江藩《汉学师承记》谓王、钱于惠氏皆执经问难,以师
1
礼事之。惠长于王二十五岁,而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称“亡友惠定
宇、戴东原”,其序《古经解钩沉》也称“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县戴
东原也”。而钱氏序惠栋《古文尚书考》云:“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余弱
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謬以余为可与道古者。匆匆四十余
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钱、王两人是否真的入室执礼姑且不
论,但两人对这位师长的态度却泾渭判然。对于历史上之学者,王鸣盛多肆意指责,如:“陆
德明、张守节皆无知之辈,谬妄殊甚”(《商榷》卷五一),“李延寿也者,于经非但不见
门庭,并尚未窥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庸且妄也”(卷六二),他如讥杜元
凯剽窃,蔡九峰妄谬,前哲时贤,多遭其指斥。而钱大昕认为李延寿《南北史》“事增文省”,
虽有不当,但亦为史家所难。(《跋南北史》)《潜研堂集》有《答王西庄书》云:“得手
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诋诃前哲为
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
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切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辩,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
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
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
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此谓“所撰”,以迮鹤寿《蛾术编凡
例》观之,似指《蛾术编》一书。透过挚友间的诚意规劝,可以看出王鸣盛俾倪前贤的傲气
和钱氏平允谦和的冲渊之气。钱大昕薄责于人的态度还可从下举事例中得窥一端。
吴缜初登第,上书欧阳修,求预史局。修以其轻佻,不许。后吴遂作《新唐书纠谬》以
诋毁之。钱氏认为吴“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在历数其未达于“地
理”、“官制”、“小学”之后云:“《新史》舛谬固多,廷珍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
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跋新唐书纠谬》)又其《跋资治通鉴》云:
“胡身之于舆地之学深矣,然亦不能无误……予尝有《通鉴注辩正》二卷,于地理纠举颇多,
非敢排诋前贤,聊附争友之义尔。”《跋通鉴释文》云:“自胡景参(按,三省又字景参)之
注行,而史氏《释文》学者久束之高阁……景参以地理名家,而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
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后人知二书之不可偏废云。”鲍廷博刻
熊氏《后汉书年表》,请其覆校并求序。钱氏云:“以予粗涉史学,属覆校焉。予弟晦之尤
熟于范史,因与参考商略,正其传写之讹脱者。”略点表中之讹后云:“此或千虑之失,弟
元文未可轻改,聊效光伯《规过》之义以谂来学云。”钱大昕信从颜师古攘叔父《汉书决疑》
为己有之说,但他作《汉书正误序》,没有肆意谩骂,仅云“夫孟坚书义蕴宏深,自汉讫隋,
名其学者数十家,小颜集其成而诸家尽废,学者因有‘孟坚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读之,亦
有未尽然者”,“裴注《史记》,所引《汉书音义》盖出于蔡谟本,而小颜多袭为己说;且
其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史称师古多资取其义,而绝不齿及一字,则攘善之失,更难掩
也”。他对时人专在前人书中寻摘一些流传抄刻之误,所谓“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
墨,夸曜凡庸”,及“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
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者,皆深致不满,亦仅说“予所不能效也”(《廿
二史考异序》),而不是痛斥谩骂。在平实的批评中,蕴含着纠谬、求真、不掠人美、诚意
规过的真情,躬自履行着实事求是的治学道路,体现出一种为学与为人之精神,足以端人心、
纯学风。
钱大昕之所以能在为学与为人上达到此种境界,是与其家庭教育、自身经历、学术专攻
等分不开的。他的祖父“生而颖敏,好读书”,因“家贫”,只能“以课徒自给”,但“亲
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辍”,“于四部书靡不研究”,主张“读
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经句读,字之边旁,
2
音之平仄,无少讹混”。(《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年逾八十,尚读书不辍。或云:
“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读书便俗。”(《记先大父逸事》)其父亲“少承
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不屑屑记闻章句,习举子业,涤烦去滥,壹以先正为师”。因
“家故无负郭田”,“岁时伏腊,四顾壁立,恒相对愀然”,故“弱冠后,亦出授徒,束修
所入,悉以奉菽水”。(《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先考小山府君行述》)钱氏五
岁,综观四部书、能辨四声清浊的祖父即“亲授以经书,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详悉指
示,俾记忆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虽然家无负
郭田,父亲仍然贷钱为其购书。大昕本生而颖悟,故可想见其在十五岁时已具备良好的经史
和小学基础。钱大昕一身殚心史学,自十八岁读《资治通鉴》及不全本二十一史,萌发尚论
千古之志。二十二岁从王艮斋游,史学益进。观览史书,自然熟于史鉴,进而于历史人物之
骄谦勤惰、功名成败、高官厚禄、道德文章有透彻的理世界文化遗产手抄报 解。加之家庭影响,形成了他一生冲
和谦退、以博学立言为宗旨的人身哲学。其《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云:“今海内文人学士,
穷年累月,肆力于铅椠,孰不欲托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谓可以两言决之,曰:‘多
读书而已矣,善读书而已矣。’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快一
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夫惊而舌挢,识者笑且齿冷,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多
读书,善读书,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既已胸罗万卷,也不率尔为文,恃才
傲物。他认为:“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文箴》)虽数十年间勤
于著述,却始终恪守著作中“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
的准则,今见《考异》中引当代学者及门弟子之说,皆标举姓名。他自戒云“窃人之言,以
为己词,欺世啖名,为识者嗤”(《文箴》),并深以“郭象、何法盛之事”为耻。古人有失,
援据匡之;今人有善,表而出之。他序臧琳《经义杂识》云:“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
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先生之书,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其辞,轻诋先
哲,斯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书,而益重其人也。”《经义杂识》是一
部质量相当高的学术著作,钱氏不但肯定其书之价值,更从臧氏著述的立意予以褒扬。倘若
稍读一些钱氏的著作,便可体味到这既是对臧著的褒扬,也是他一生躬自实践的信条。
钱大昕一生学问,可谓博大精深,足以自是,但他却信奉“博而孱守,默而湛思”(《文
箴》)。其治学态度,即是在他著作中出现过数十次,并且也体现得最充分的“实事求是”。
其等身著作,是天资与勤奋的结晶,而他却以“潜研”、“孱守”、“十驾”名其斋,谦然
若使人不解者。但是,当我们清晰地了解了他的行历、思想及治学方法后,就可深切地把握
他一贯的人生哲学——“怀孔之璧,守老之黑”。(《圆砚铭》)
综论钱氏之学问成就,大致可分为:经学,主要是小学;史学,主要是职官、舆地、谱
牒之学,元蒙史学以及金石学,避讳学,天文历法学等等。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
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之,综合之。以上各门学问,当今学者均有专论,以探讨钱氏在
各领域中之成就与得失,无须赘论。兹就笔者曾稍涉足或初有观想者略述一二。
一、古声纽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提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
(后人概括为“古无舌上音”)二说,并以大量例证来证成其说。又著《声类》四卷,以
一千五百余条例证来发明正转、变转之理。清代研讨声韵而先于钱氏者有顾、江,同时
者有戴、段,但诸家所论多偏重韵,唯钱氏独求古声。此说一出,学者翕然风从。清末
以还探求古声纽者:如黄侃论证“照穿神审禅古读端透定”,曾运乾论证“喻三归匣,
喻四归定”,及其他论证古声纽文章者,皆循钱氏之方法。今有符定一等人据此而反证
古有轻唇音、古有舌上音,而学界大多还是信从钱说。笔者曾研讨三礼汉读、异文中之
古声类,深感谐声、异文所反映之古声类有古今之变,亦有方音之异。钱氏对方音也是
有认识的,他与段玉裁书云:“声音之变,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遍于天下,久之遂失
其最初之音。”又云:“但古人一音异读,多由南北方言,清浊讹变。”(《答问》十
3
二)如果钱氏能本着这种思想,对所辑集的古音资料再作一种微观的方音研究,则古声
类的真实面貌必然会进一步得到呈现。
二、避讳学钱大昕倡导经史无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使弥漫在历史文献中的避讳史料凸
现出来。钱氏抓住这个现象,深入研究,解决了大量历史文献中由避讳而引起的问题。
这些考订分散在《考异》《金石文跋尾》和《养新录》等著作中。与钱氏同时的周广业
于嘉庆二年著成《经史避名汇考》,就避讳史料的搜辑而言,古今独步,无人能出其右。
但因钱氏于廿二史逐史考证校勘,故其所论证的避讳史料亦有出周书之外者。陈垣先生
著《史讳举例》,当今奉为避讳学之圭元宵节的图片大全 臬。笔者因欲撰《避讳研究》与《避讳词典》,
曾广泛搜辑资料,发现《史讳举例》乃取材于《日知录》《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札记》及自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元典章校补》等书,而稍作伦次排比,
归纳为例。顾、钱、王、赵书中有关避讳论述以《考异》为最多,故可以说《举例》主
要是归纳钱氏《考异》中避讳论述而成。
三、版本一般谈清代版本学者,恒数顾、黄诸人,鲜及钱氏。今读钱氏著作,知黄丕烈在
考证宋元善本时,多请其参证定夺。由于钱氏精于小学、目录、校勘、舆地、职官、谱
牒、避讳,熟于史事,故其鉴定版本,往往能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别白精审,既能定其
刊刻时代,又能考明其源流。何元锡所编录之《竹汀先生日记钞》记载了卢文弨、黄丕
烈、顾千里、周锡瓒、袁廷檮、江声、李锐、吴骞等向钱氏请教并与之讨论宋元版本之
事实。如能将此书与《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金石文跋尾》等著作中有关版
本的论述辑集并加以研究,不仅可以确定钱氏在清代版本学中的地位,同时对理清清代
版本学史暨学者间之关系亦有裨益。
四、金石岑仲勉先生撰《贞石证史》,为本世纪很有影响的以碑刻证史的专著。岑先生以
为,“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其弊在于“过信石刻”,“偏
责史失”,“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落如晨星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八本四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三十万字,以“辨别小学,考证史事为主”(《郑
堂读书记》卷三四)。自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人多推为首倡,奉为科条。其实,
《跋尾》之作,已无其名而有其实。
学术在发展,钱氏当初詮釋解决之问题,今天来看不免会有修正或需重新论证者,但就
当时而言,他追求实事求是,为学为人已达到了较完美的境地。乾嘉时期学者对他称誉良多,
即如轻视汉学,与惠派经学家唇枪舌剑地论战的袁枚,亦称赞钱氏为人,并向其请教官制问
题。段玉裁以精于经学、音韵与《说文》著称,且自以断识精审,于其著作中动辄骂人。钱
氏在《竹汀日记》中对段注《说文》武断增删,“自信太过”表示过不满,在《与段若膺书》
中对其《古文尚书撰要》《六书音均表》皆提出过尖锐意见,而段氏在《潜研堂文集序》中
自称“后学”(段仅比钱少六岁),对其著作推崇备至,认为古人能以文集传且久而著者,
数十家而已,钱集“好玩单机游戏 传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
钱大昕一生著作丰富,其生前已刊行部分,嘉庆九年逝世后又续有刊行。道光二十年
(1840),钱师光将乾嘉年间所刊者汇集重修,成《潜研堂全书》十七种印行于世。光绪十
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增补《声类》等五种,题为《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重印行世。
此虽题为《全书》,但专著、遗文仍漏略不少。今人陈垣、顾荻、刘渭平、朱瑞熙诸先生于
钱氏佚文均有辑集,张荫麟、顾吉辰、朱瑞熙先生对钱氏著作之存佚均曾作考录。光绪以还,
钱氏之各种专著,以抄本、刻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不同版本流行于世。陈文和先
生《钱大昕著述考》对钱氏著作及不同版本进行著录考订,搜辑颇勤,基本勾勒出钱氏著作
的存佚流传情况。偶有失录者如:上图藏有清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抄本《洪文惠公年谱》一
卷及嘉庆四年黄廷鉴抄本《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一卷,《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尚有1958
年商务排印本,前者又有1994年岳麓书社《二十五史三编》本;《潜研堂答问》又有光绪
4
辛巳重刊巾箱本;《王深宁年谱》又有《四明丛书四明文献集》本;《疑年录》又有小双
寂庵《疑年录汇编》本;《十驾斋养新录》又有1983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等等。陈文和先生
在诸家辑佚的基础上,进一步参校搜辑,将佚文佚诗编为《潜研堂文集补编》,并与《全书》
及新辑专著十三种汇编成《嘉定钱大昕全集》,共十册,约四百万字,1997年由江苏古籍
出版社出版。由于钱氏在当时已俨然一代宗师,求文者多,著述亦勤,编纂文集时未能搜全,
后人两次辑印,亦只是略增专著,而无散篇。时推世移,像《元史纪传稿》这种巨著已难觅
得,遗文散篇更不易遍搜,尽管笔者近来仍新发现钱文之一鳞半爪,但这已无碍新编《全集》
之辉光,新编《全集》可谓钱氏逝世后近二百年来最完善之版本。此书的出版,将使钱氏之
学术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也应了段玉裁“传而能久,久而愈著”的预言。
乾嘉考据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已成过去,今方学术所凭借的出土资料已非清人所能梦
见,利用的方法也与他们有所不同,但乾嘉学者“无徵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仍
然应成为现代学人的座右铭。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固然是一笔丰富的文
化遗产,但笔者认为,这位学术巨子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博而孱守,默而
湛思”的风范,“实事求是”、“无绿豆芽的做法 徵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更值得
我们现代学人去体味,去思考。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虞万里于榆枋斋
5
本文发布于:2023-03-21 14:10:41,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937904215386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十驾.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十驾.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