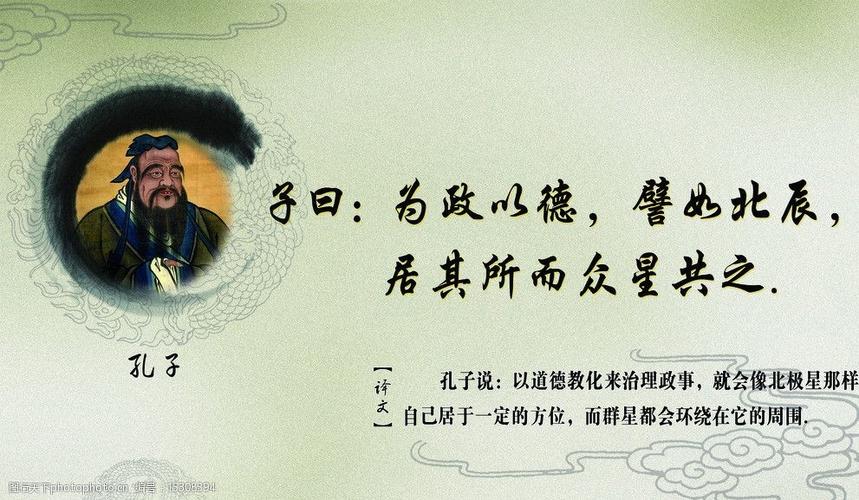
2021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
得失范文
新时期以来,新疆不少作家加入了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涌现出像冉红、汪海涛
这样产生过全国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新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民族采取“大杂
居、小聚居”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背景的影响下,新疆汉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
呈现出一个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的特别现象,就是在作品中书写少数民族儿童,体现
独特的地域民族特色。塑造少数民族儿童形象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形象塑造,有一
定的艺术难度,但作家们愿意进行这样的尝试,目的是以此寄寓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艺
术想象。分析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的表现类型及艺术得失,有益于发现
跨民族的创作文化心理,同时不失为一个深入观照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新视角。
一、“理想型”的道德偶像代言人
一位新疆作家毫不讳言地说:“身在新疆你必须写少数民族,这是你作为一个新
疆作家不同于内地作家的标签;我们写少数民族从来都是正面书写,这关系到你的政
治立场,绝不能马虎。”这一番“大实话”委实道破了新疆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环
境,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政治环境仍不宽松的上世纪80年代。配合着这一时期“儿童
文学是教育儿童的”的“教育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新疆汉族作家努力尝试树立起
少数民族儿童的道德模范典型,包括唐栋的《到后山去》、肖嗣文的《带泪的清
晨》、汪海涛的《骑白马的哈兰》、马焰的《你不相信依沙木爷爷吗?》、姚梅的
《“皮大王”捐款记》以及90年代于文胜的叙事诗《海孜勒罕》等。无论是《到后
山去》中狠心杀了心爱的小黑羊为解放军炖羊肉的维吾尔族牧羊少女米尔古丽,还是
《带泪的清晨》中故意放枪惊走小鹿的哈萨克族少年阿依达尔,抑或是《骑白马的哈
兰》中佯装受伤、帮同学赛马夺冠重拾信心的哈萨克小男孩哈兰,还有《你不相信
依沙木爷爷吗?》中敢于质疑权威、用科学拆穿迷信把戏的维吾尔族小男孩乌苏尔,
为少年儿童基金会捐钱的四个维吾尔族淘气包,以及在额尔齐斯河岸摆渡智斗杀人犯
的哈萨克英雄少年海孜勒罕……他们都是善良天使的化身,有着纯净的心灵与无畏的
胆色,他们基本都来自乡村,有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与大自然天然亲近的本色,
才会与马、羊、鹿为伴,将其视为自己的伙伴和心爱之物。作者将理想化的不含一点
杂质的人性理想寄托在这些幼小的童心之上,通过他们去完成成人世界业已忘却的善
举,也透过他们去释放道德感召的力量。
作者在塑造这些理想化的道德偶像时,不愿让儿童直接充作图解政治的宣传工
具,因而十分注意刻画少年儿童的细腻心理从而避免功利性地直奔主题。例如少女米
尔古丽在杀心爱小羊之前矛盾的心理斗争,她泪水汪汪地拍着小黑羊:“啊,我心上
的宝贝,不是我对你无情,因为只有你才能替我偿还这份心愿。原谅我吧,小宝
贝……”之后她丢下匕首扑倒在小黑羊身上大哭。似乎只有舍弃珍惜之物才能表达最
深切的感情---这明显是成人的逻辑思维,但是作者却刻画得非常动人,当米尔古丽抱
着热腾腾的清炖羊羔肉瓦罐往公路跑时,发现军车竟已离开,她“只觉得心里空荡荡
地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两腿一软,扑通跌坐在山路上……”这时的米尔古丽是错过了
报恩?是白宰了小羊?是失望?是伤心?那复杂的心情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宰羊,是
穆斯林的最高礼节,为尊贵的客人宰羊,没有什么舍不得,这是维吾尔、哈萨克等少
数民族的传统,明白了这种文化背景,就可以理解小姑娘宰羊并不是成人逻辑的强
加,而是民族传统使然;相反,小姑娘依依不舍与小黑羊说话告别才真正体现了儿童
思维。最后作者安排又驶来几辆军车、小姑娘破涕为笑“小黑羊还热得烫手呢”的结
局,进行了米尔古丽的心灵补偿,也让少年儿童读者体验了一次圆满的心灵旅行和人
格洗礼。同样,哈萨克少年阿依达尔保护小鹿不受伤害,既有儿童与动物的天然亲近
和善良愿望,更浸润着游牧民族哈萨克人对自然之子的深厚感情,他们把四蹄类动物
看作神灵、看作天赐的礼物和最亲密的伙伴,这种宗教感情与汉族儿童爱护小动物的
感情有着本质区别。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一个维吾尔族小学生从一群迷信的乡亲们中间站出来说“权
威并不等于真理,只有科学才是真理”(《你不相信依沙木爷爷吗?》),当四个淘
气的维吾尔族小男孩说出“我们眼巴巴地盼着你们能为我们少年儿童多买些球、多修
几个体育场,使我们放学后不再过那种寂寞的日子,不再玩那种无聊的把戏……”
(《“皮大王”捐款记》),当一个哈萨克小女孩认为爸爸不关心南方灾情质问他
“算什么国家干部和党员”(于文胜《阿娜尔古丽》),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背后站
立的成人,这时的儿童成为社会角色的符号和代码,为作家“发声”,为传递作家的主
观意图而存在,戴着成人强加在头上的光环,却掩盖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征,
因此这一类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是理想的也是单薄的。
二、“象征型”的民族交往小使者
“民族团结”是新疆永恒的文化主题,这取决于各民族杂居多年的社会现实,也
取决于各民族和谐共处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政治需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有世居
少数民族13个,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等少数民族约
占新疆总人口的62%.新疆和平解放后,汉族与当地世居民族、外来迁徙民族共同建设
美好家园,在工作与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各民族少年儿童也相伴共同成长,因
而“民汉交往”、“民族团结”成为新疆儿童文学作家选择书写的一个重要题材。像
冉红的《会唱歌的土豆》、《马背上的小太阳》,虞翔鸣的《森林之谜》,茹青的
《甜甜的沙枣》、《沙海秘宝》,贝新祯的《奶疙瘩的故事》,王维的《热瓦甫和
带键的竹笛》,刘河山的《放风筝的童年》,于文胜的《我和别克的故事》等都是
这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会唱歌的土豆》写了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
吾尔族四个小伙伴共同探寻土豆唱歌的地质秘密,《马背上的小太阳》写俄罗斯族小
姑娘被哈萨克父母抚养长大,《甜甜的沙枣》写回族娃娃帮助汉族小朋友,《热瓦
甫和带键的竹笛》写维吾尔族和汉族小男孩的友谊,《我和别克的故事》写“我”
和哈萨克同学别克之间的恶作剧与和解,《森林之谜》和《沙海秘宝》也写了各族
儿童共同探险的故事。作家的思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描写各民族儿童之间的密切交
往,歌颂民族团结,但是塑造的儿童形象大不相同。个别作家塑造出了习俗不同、性
格各异的少数民族儿童典型(比如《会唱歌的土豆》为新疆作家开启了很好的路
子),而在大多数作家笔下,各民族儿童只是顶着一串少数民族姓名的“朦胧的群
像”,他们即使交换名字也不影响全局。究其原因是作家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隔
膜,对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一知半解,更多通过印象和拼接来完成对遥远的少数民族
少年儿童的文化想象。
茹青的《甜甜的沙枣》和于文胜的《我和别克的故事》算是民汉儿童交往题材
作品中的佼佼者,塑造出了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甜甜的沙枣》中什么都要问妈
妈被强强看不起的、制止强强欺负小弟弟的、叫来妈妈给强强缝补裤子的温和大度的
回族娃娃尕兵,《我和别克的故事》里人高马大的、身上一股酸奶子味跳进河里也
洗不掉的、被“我”恶作剧用图钉扎了屁股强忍委屈、后来还骑马帮我渡河的哈萨克
小学生别克。在这两部作品中,尽管作者一再突出主人公的绝对地位,渲染主人公的
优秀品质,然而掩饰不了的是---少数民族儿童依旧是一个“他者”(萨特语),他
们高高地、远远地站立在作者和读者的彼岸,具备那些成人们希望儿童具备的优秀道
德品质,而与之相对的,作者写得活灵活现的恰恰是用来陪衬少数民族儿童高大形象
的汉族儿童,他们是《甜甜的沙枣》中那个爱逞强、自尊心强、内心纠结的强强,
是《我和别克的故事》中欺负别克又思念别克的“我”.“他者”的塑造暴露出汉族
作家潜意识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及对表现对象的不自
信,充分诠释了“主题先行论”的艺术贫弱。一个从作家的心中梦中伴着血与爱流淌
出来的艺术形象绝不可能被置于彼端,更不可能双脚悬空,这或许正是跨民族跨文化
艺术形象塑造的真正难题。
与以上“儿童交往”题材略有区别的是《奶疙瘩的故事》。这篇小说采取爷爷的
成人视角,回忆了“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关禁闭,送饭的哈萨克小巴郎急中生智
向屋里扔石子,高喊着“向反革命开火”、“看看我的子弹有多厉害”,得到看守人员
的赞赏,“我”为童心蒙蔽而悲哀,捡起子弹细看才发现竟是奶疙瘩!那孩子每天都
来“开火”,而“我”就靠着这奶疙瘩维持了生命。
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成人与儿童的交往,读之真实感人,作者笔下的小巴郎形象虽
只有寥寥数笔,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他既是民汉团结的亲善使者,又凭借善良与
机智的童心完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良心救赎,让特殊年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与知识分子的愤懑怨怼通过童心化解为轻盈温暖的回忆,转化为民汉之间历久弥新的
深情厚谊。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并非是典型化的,而是象征型的。
三、“儿童性”超越“民族性”的真孩子
与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描摹本民族儿童形象时得心应手、却几乎从不刻画汉族或其
他民族儿童相似的是,新疆汉族作家也极少以少数民族儿童为表现对象,出于自身的
使命感和对家园的热爱,勉力尝试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创作,但人物形象多偏于符号
化、扁平化,缺乏有性格、有成长的生动立体的儿童典型。
80年代中期冉红的中篇小说《会唱歌的土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原来汉族作家
是可以将少数民族儿童写好的。十一岁的哈萨克男孩阿登和八岁的柯尔克孜男孩小不
点,这两个形象一点也不比另外两个汉族主人公艾疆和蛋蛋逊色。阿登是个顶天立地
的小男子汉,好强好胜脾气急,他起先不让小伙伴参观他们少年宫科技小组的实验,
看到大家失望地散开又赶紧改口:
“不是科技组的也让看”,充分反映了小孩子既爱炫耀又怕孤独的特性;他发现自
己错误地嘲笑了艾疆之后,“他用肩碰碰艾疆,憨厚地笑笑”,还偷看艾疆的脸色,这
分明是男孩子之间请求和解的特殊方式;阿登和艾疆本来跟踪着阿孜卡尔爷爷去找蛋
蛋,但是被路上美丽的景色迷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泳去了,这是儿童典型的“见
异思迁”.小不点是两个哥哥的“小跟班”,最擅长撒娇,大家求爷爷带他们去找蛋蛋
时,他娇憨地一口一个“好爷爷!”“爷爷是老雷锋,我们是小雷锋!”艾疆看爷爷
坚决不答应,准备采取迂回策略以退为进,阿登不理解大骂艾疆“装好人!”小不点
也紧跟着附和:“艾疆是叛徒!艾疆是两面派!
”这是20世纪80年代小孩子之间最厉害的攻击语言,很有时代感和生活原型。小
不点好奇马耳朵为什么能转动,就用树枝捅马耳朵,不料马受惊把他重重摔到地上,
本来他昏昏沉沉的,可看到身边一只跳跃的长尾雀,又来了精神,“他除了饿了想
吃,困了想睡,就是想玩儿,玩起来可以忘记一切……”这不正是童稚时代的各民族
小朋友的共性吗?大家一起摘核桃时,小不点还瞅着机会向阿登解释:“阿登,马耳
朵我只捅了一下,不会聋的。”将他不愿承认错误又内心不安、讨好小哥哥的心理惟
妙惟肖地展现出来。
小不点因为贪吃误了事哥哥们怪罪他时,他委屈地大喊:“你们不也吃了吗?”
为了找蛋蛋,小不点脚下磨出了血泡,嘴里哼唧着,但还坚持着……读完这些,一个
个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儿童形象站立在我们眼前,触手可及。毫无疑问,他们是成
功的、典型的儿童形象,但他们是否是成功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不难看出,作家在
极力靠近少数民族的生活,力图还原他们的生活环境,文中涉及到的天山、矿石、胡
杨林、天鹅湖、毡房、马奶子酒、炖羊肉、馕、葡萄干、冬不拉……无不体现新疆的
少数民族风情,作家将人物、故事、环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十分自然和谐。
但是,如果同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创作相比,如维吾尔族作家帕尔哈提·卡孜木
的长篇儿童小说《一瓶沙子》,哈萨克族作家杰恩斯·热斯汗的三部曲成长小说《托
姆帕克成长记》,那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民族气息,以及更具备“民族性”
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是汉族作家很难模仿和企及的。这里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
“民族性”与“儿童性”,哪个是“第一性”、哪个是“第二性”的问题。我们要塑造
一个真实生动的儿童形象,如果不具备“儿童性”,那他只能是一个“缩小的成人”
(鲁迅语);如果只具备“民族性”,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戴着小花帽骑着小马驹名
叫买买提的“纸人”,而不是活泼泼站在我们面前的真的儿童。
所以,“儿童性”是跨越国家跨越民族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的“童心”、
“童趣”、“童真”都是相通的---“儿童性”是先于“民族性”的“第一性”.因
而,冉红的作品并不是胜在“民族性”,而是胜在“儿童性”上,比如孩子们看到奇怪
的解释不了的事物都爱喊“鬼”,土豆发出嘎嘎声,就说土豆里有鬼,这是典型的儿童
思维,和人类的原始思维相近;作品还胜在她的“童真”,如孩子们蹲在土台上嘻嘻哈
哈抓光点玩,还配有儿歌“月亮光光,你别躲藏,到我手里,给你奶糖。”这是一幅
多么生动惬意的美好画面啊。少数民族儿童的“儿童性”也在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
闪耀着星点光辉。
如冉红《马背上的小太阳》中的俄罗斯族小姑娘达拉波孜因为纯真诚实不懂得掩
饰,一再暴露行踪给父母带来麻烦。肖嗣文《小鹰》中哈萨克小男孩谢莫孜玩髀什
(羊拐骨)耍赖,被好友揭穿后不服气,大叫他的外号“阿克萨克(瘸子)”嘲笑
他,之后非常后悔。胡尔朴《花的故事·稚朴》讲哈萨克小巴郎为了书本费卖鸡蛋,
开始一毛一个,死活不讲价,但当他数够付书本费的鸡蛋时,兴奋地拿了钱撒腿就
跑,连剩下的鸡蛋和篮子都不要了,这买卖可亏大了,这是用儿童的思维和行为来体
现童真。茹青的儿童剧《会飞的巴郎》更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维吾尔小学生巴哈提
起初不愿做与三好学生无关的事,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管别人的闲事,他认为自己是要
做大事的人,后来慢慢懂得了助人为乐。作品将“三好学生”这个抽象概念充分地形
象化,并展现了孩子的心灵成长,让小巴郎的形象真的“飞”了起来。
结语
综观新时期以来新疆汉族儿童文学作家塑造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他们代表了儿
童文学汉族作家关怀各民族儿童的自觉使命感和美好愿望,具备一定的时代特征、教
育意义和审美价值。而反观“理想化”、“象征型”、“儿童性大于民族性”的以上
三类少数民族儿童形象,恰恰能一一对应地揭示出新疆汉族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少数民
族题材的三大问题:政治宣传意味浓、不够真实、不够民族。这些形象大多是类型
化、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即便具备了一定的“儿童性”,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更别
提塑造“无意思之有意思”(周作人语)的真“顽童”形象了(冉红的作品本有此
趋势,但并未超越,亦无人继承)。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因为跨越民族文化
的种种困难,书写少数民族儿童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家已日渐罕至,看来新疆儿童文学
作家想要塑造出能立足于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形象库中的“这一个”,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本文发布于:2023-03-16 02:32:22,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89051423045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土豆歌.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土豆歌.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