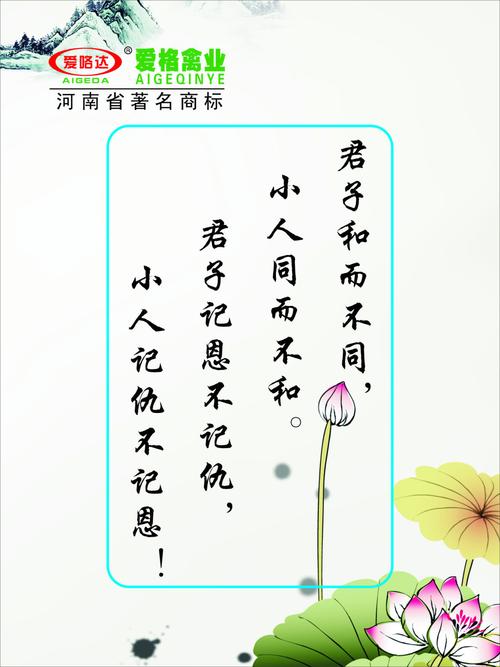
徐
兆
寿
张
承
志
的
文
学
世
界
一、创作的分野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张承志是一位诗人。他
所有的小说和散文,对我来说,就是一首首或优
美或壮阔的长诗。最早读他的《黑骏马》,黝黑色
的古老情韵几乎覆盖了我对草原的感念,内在
世界里一根不可名状的琴弦就那样一直悠扬至
今,或有若无,像是时间空间里突然飘来的另维
存在。后读《北方的河》,似乎与我年轻的心贴得
更近。浪花四溅,一路豪言壮语,一人可与整个
世界抗衡。壮丽的理想。那里面有我。那是壮阔
的时代魂魄。
一九八九年的一天,当我在西北师大图书
馆里看到《中国作家》第四期上张承志的小说
《错开的花》时,我还是认为那是诗。但已分野。
前面三章与最后一章真的错开了。对于小说中
的“我”来说,前面三章的经历是为最后的历程,
但对于读者的我来说,最后一章跃出了小说,凭
空现出万仞悬崖。那时的惊愕犹如荒野遇刺般
一时无法承受。已不是我所熟悉和喜爱的张承
志。另一个张承志出现了。终于,一九九一年以
其散文《告别西海固》和小说《心灵史》彻底地告
别了过去。当我在办公室里当着同事的面忍不
住泪水盈眶时,我的手里正捧着《心灵史》,但即
使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坦白,我并没有读完它。
它仍然是诗,鲜血的诗,叛逆的诗。此后,我再不
忍去读它,我宁愿永留那泪水涌流时的感动。是
同年读发表于《中国作家》第四期的《告别西海
固》时,我读懂了一些张承志。我只能说,那时只
是读懂了一些,不能说我真的读懂了他。
即使到今天,写下这些有关张承志的文字
徐兆寿
张承志的文学世界
216
评
论
时,我仍然不能说真的读懂了他。他的冒险,他
的叛逆,他的独往,他的愤怒,以及他泣血而疯
狂的自语,我都嫉妒却无法复蹈。他走得太远,
我不能抵达。民族与文化的界限阻挡了我。不能
亲历,便难以体味。不能近距离地看他,便只能
远距离地审视他。从他的文字,从他的诗里,从
他倾洒在草原和西海固的血液里辨别他,解读
他。一个作家,当他将饱含着心血的神圣文字捧
给世界时,他就变成了一种风景,任凭世人评
品。他也一样。
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的作家不是很
多,这与我哲学的爱好、北方气质的心性、O型
血的性格有关。张承志的文字正好打动了我,大
地、草原、沙漠、激情、偏执、愤怒……这些北方
的血性感染着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我
生活的兰州乃至整个西北,有一种张承志的气
息不时地在大学校园里、文学青年喷着啤酒的
卧谈中和一些回民聚集的摊点上,浓烈地一闪。
常常有人与我高谈张承志。他的很多作品不是
以文字示我,而是以这样的心灵或语气示我。因
此,我没有读过的作品往往以更为强烈的印象
迫于我。
但他对我还是熟悉和陌生的。在浩茫的文
学中,有些作家是你能够一眼看穿并越过他的,
他们思想有限,性情温和,随遇而安,文字也如
你想象的一样。有些更为聪明的作家你看不穿
他,但你能越过他,因为他们只有经历和写作的
智慧,却没有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只有极少数的
作家天生是冒险者,以身相许以文学和信仰,激
情似电,文风凌厉,心灵如黑炭,思想如江海,要
越过他是极为艰难的。你只有似他一样,才能与
他比肩。你即使不能与他相比,你也愿意一试。
张承志就是最后这种作家。我愿一试,去解读
他。
也许对于张承志来讲,其内心的分野是从
一九八四年他进入西海固时开始的,那时他还
是一个浪漫的骑手。但西海固之行,显然是另一
文化世界的初次遭遇。他的文化背景发生了位
移,至少,他拥有了比其他作家多一重的文化背
景。在此之前,他与同时代的其他知青一样,怀
着对草原的挚爱、对时代理想的憧憬写下浪漫
的诗篇《黑骏马》、《北方的河》、《骑手为什么歌
唱母亲》等,但自西海固之行之后,可以想象,作
家另一重文化的背景即他作为一个回民的背景
开始日渐清晰。正是这两重背景的叠影,塑造了
一个新的张承志。一九八五年发表于《中国作
家》第二期的《残月》便是证明。陈思和先生说:
“张承志……成为一名边缘性的民间知识分子。
这以后他的创作风格骤变,《九座宫殿》、《残
月》、《黄泥小屋》……直至《心灵史》的出现,无
论从题材内容、语言形式还是写作观念,都与以
前迥然不同,它以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来展示
一个特殊地域、特殊的民间社会以及生活在其
中的特殊的民族的精神文化。张承志的这一民
间精神的追求,随着九十年代初的长篇历史叙
事《心灵史》的发表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但在早些时候发表的短篇小说《残月》已经包含
了其基本的精神特征和审美追求。”他还说:
“《残月》与张承志在一九八五年以后的创作风
格相一致,由粗粝、硬健、并不流畅的语体构成
了特殊的叙事文风,作家故意放弃其早期小说
里浪漫又诗意的表达方式,在粗粝、质朴、强悍
的话语背后站立的是同样质朴、强悍的民间群
体。”(1)
作于一九九〇年八月但发表于一九九二年
《中国作家》的《天道立秋》是另一份证词。在那
篇小小的散文中,我看到一个做着礼拜却对中
国古人崇拜的天道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他说:
“我是证人,我证明天理的真实。”他似乎告诉人
们,他与中国古人暗合了,他退出现代。他与当
下的中国文坛分道了。事实上,张承志与当代中
国主流文学的关系走过了一段起初合流、后来
慢慢分流到最后的绝对分野。
今天再来读《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有一
种久违了的感觉,那便是与理想和激情的遭遇。
前者仍然会深沉有力地拨动你心灵深处的某一
根琴弦,使你温柔、辽阔、深沉、悠远。小说会将
你自然地塑造成一位从远古而来的行吟诗人,
弹着马头琴,寻找着亘古的爱。后者则使你激情
昂扬、澎湃汹涌、孔武有力,一个征服者的形象
赫然而立,理想和英雄之流激荡着你的胸腔。假
如再读到张承志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
亲》时,对张承志的早期定位便十分清晰了。完
全是一个诗人的歌唱。这哪里是小说?根本就是
一首首叙事诗,甚至是一首首抒情诗。诗化小说
的特点不但是张承志早期写作的显著特点,而
且是其后期小说与散文随笔的气质。
在创作《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时,整个文
217
徐
兆
寿
张
承
志
的
文
学
世
界
坛实际上都弥漫着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
义的情怀,比如此时朦胧诗人北岛、舒婷、江河、
杨炼、顾城、梁晓斌等都写下了众多同类主题的
诗歌。理想之火在中国的夜空上升。然而,很快
地,这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在退却,最后诗坛让给
了以平民意识和个性意识为主的口语诗和先锋
诗,小说界也一样,先锋小说顿时解构了此前的
历史宏大叙事和集体抒情。此时的张承志显然
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然后他依然固执地行
走。一九八七年发表和出版的《金牧场》虽然比
此前的小说变得更为复杂,抒情中有难以抑制
的痛苦,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是一个诗人在痛苦
地歌唱。评论家王必胜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
“张承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热情歌者,对人生价
值和理想赋予高扬的时代精神,赞美灿烂的人
生。但他不是轻歌曼舞地颂扬,而是从艰难人生
历程中,从奋斗进取者坚韧甚至痛苦的跋涉中
来褒扬人生理想,赞美人生奋斗的业绩。同时,
又多从作家自己心灵体验和感受出发,在解剖
自我灵魂时,抒发对奋斗者的复杂而深沉的壮
烈情怀。”(2)
如果说在《黑骏马》中,作者还非常重视小
说的抒情意识和审美追求的话,《北方的河》已
经在趟过一条理性的河,到了《金牧场》时,作者
的理性已经超过了抒情。它显示出作者急于想
转型。后来,作者在回顾《金牧场》时,他认识到
在这部作品中企图包容的思想太多,以至于思
想大于形式,文体反而为驳杂的内容所累,简直
是一部失败之作:“装二十年经历于一个金牧场
的设计,今天看来是失败了。因为,不应该强求
把二十年思索获得的思想装进一个框架。但是
从反面又应该说,小说形式的不成功,也许是因
为小说形式不能容纳它的含量。”(3)事实上,《金
牧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其浓烈的诗化特点,二
是其行将爆发的宗教情怀。这是张承志在那个
先锋艺术时代一次颇具野心的先锋试验,自此
之后,他开始渐渐放弃小说叙述,转而开始随笔
散文的写作,而这种随笔散文自始至终也有两
个特点:一是诗化特点,二是学者式的理性批
判。
《心灵史》是一个分界线。尽管张承志心灵
的转变早在此前已经在进行(4),《金牧场》便是
其印迹,但是,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心灵史》才
是真正的界限。八十年代有几个重要的文学思
潮,张承志其实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一是文本
的实验,《心灵史》、《金牧场》可以说是这方面
的实验,特别是《心灵史》,评论家们对其是否
小说一直争议较大,若是把它放在先锋小说中
去看,就不足为争了。二是为“文学史写作”、
“为后世写作”;三是为中国文学填补“史诗”的
空白。海子的写作就是这三种思潮的影响所
致,张承志的《心灵史》也一样。《心灵史》就是
一部诗史,他在《告别西海固》里说:“就这样,
我被一套辈辈都有牺牲者的家史引着,一刀剖
开了乾隆盛世……我决心让自己的人生之作
有个归宿,六十万刚硬有如中国脊骨的哲合忍
耶信仰者,是它可以托身的人。你就这样完成
了,我的《心灵史》。”张承志有明确的写作对
象,他要为哲合忍耶创立一种心灵的图腾。这
种写作类似于《古兰经》。
正是在这个时候,张承志的写作便与当下
所有的写作者有了质的区别,而这也是张承志
从中国“五四”以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走
向宗教意味文学范式的重要标志。《心灵史》之
后,张承志显然陷入两种情怀之中:一是为自己
的信仰而慢慢放弃艺术的追求,转而进入宗教
的追求中;一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背景,参照
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传统文化对与己对立的现
存世界进行批判,甚至决裂。在《心灵史》之后连
续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荒芜英雄路》和《清洁的
精神》,可以明显地看出后一种倾向。而此之后
他放弃小说创作,以散文和学术文章继续写作,
其内心的文化冲突已经逐渐高涨。
二、心灵的转变
在当代文坛上,大概再没有一个人像张承
志那样发生数次深刻而执拗的心灵转向。他起
先是一个红卫兵,然而他去了大草原,在那里,
他的心灵发生了巨变。然后他回到都市,写下一
系列的诗篇。正在他走红的时候,西海固神秘地
带走了他,他的心灵发生剧烈的地震般的转折。
他又写一系列激愤的篇章。近些年来,就像一座
火山在喷吐之后终要归于平静一样,他写下鲜
花与废墟。
张承志在接受美国学者的采
访时,他毫不隐讳地说: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我虽然不是一名头
218
评
论
头,但是‘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创作发明的。要
是任何人问我,我创作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我
会毫不犹豫地说‘红卫兵’。”(5)
这种语气里似乎有一种炫耀,有一种得意,
而这种炫耀和得意似乎也正好应对了那些批判
他的人对他的一系列攻击:“一种狂热的文化冒
险主义的心理/文化表征”(6),“孤傲发展为自
负,他显得偏激狭隘,难以容人”(7)等。
从心理学上来讲,张承志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是一个具有言语暴力倾向的人。从他一系
列的杂文、随笔和文化散文中可以充分地看到
这种心理。这是由他自身的文化冲突所决定的。
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大陆道德的沦丧与他个
体的追求发生冲突,他过去所接受的历史、现实
文化与他正在接受的伊斯兰文化发生冲突,他
的日常生活与他的宗教追求也在慢慢发生冲
突,他过去耀目的文学成就和评价与他当下众
说纷纭的评论(而且批评的声音似乎更大)发生
了冲突。他急于想让人们接受他,承认他,于是,
他怒不可遏地向他所认为道德沦丧的大众、向
价值混乱的知识阶层、向与他的价值取向相对
立的异质文化宣战,像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一
样。
他似乎过分地强调了“我”的存在。他总是
在文章中激愤地强调:“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
坟。”(《告别西海固》)“我不从属于任何政党或
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
了这种思想。”(《墨浓时惊无语》)他也总是在辩
解:“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心灵史》出版
后,一直致力于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
狂。”(《墨浓时惊无语》)“一九九一年的我突然
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试
血。”(《致先生书》)大概谁也没想过,张承志为
什么激愤?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辩解?批判者是不
愿意看见一个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诗人到处指
手画脚,更不愿意看见一个文化异己者的走红。
文人的心理不过如此。于是,自《心灵史》出版
后,张承志遭受的批评与非难是难以想象的。正
如张承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被称为一个“宗教
狂”,一个文化冒险者,一个专制主义的代表。在
大量的对宗教怀有不同意见的批评者那里,在
那些文化虚无主义者的眼里,张承志成了众矢
之的,而更多的人则在观望。因为这些原因,张
承志的思想只能是“无援的思想”,而他的道路
也必然是“荒芜英雄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
只有自己站起来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信
仰。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一个人不能自己说自
己的好,这样肯定自我是不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的。张承志犯了中国人生活的大忌。这是他被批
评的另一重原因。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一个
人有了冤,你也最好不要自己说自己冤,更不能
骂你的对手,而要别人站起来为你辩解,你始终
不说话,那样,你才是真正的君子,才是有智慧
和修养的圣人。可张承志又犯了大忌。他非但自
己为自己辩解,还大骂对手,甚至在骂对手时,
将大多数也骂了。这些大概是张承志当时的心
理和备受批判的一些社会文化心理吧。
这也是张承志向宗教心理过渡的必经的一
步。这种心理在很多人身上都曾经存在过。卢梭
在晚年写的《一个孤独者的散步》就是一部愤慨
之作,没有了先前的优雅与宽容。尼采曾说“我
为什么如此聪明”,他在准备重估人类一切价值
之时,竟然疯了。尼采的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可以
说是最具语言暴力倾向的文字,自从他与瓦格
纳决裂后,他的语言就像一把利剑,不断地向着
基督教心理越刺越深。事实上,鲁迅当年也一
样。面对虚弱的国民,他说自己的文字就像投枪
和匕首,把自己的对手咒骂为“落水狗”之类。
“决不宽恕”———鲁迅的这一宣言在深受儒家文
化、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看来,有些过。张承
志在写《心灵史》之前,他曾说:“我也写了几本
书,蘸着他人不知的心血。但是我没有看到过读
者对我的保卫,只看到他们不守信用地离开。在
我对自己的生命之作抉择了以后,我不能不渴
望读者的抉择。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
我而去,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以后,我便认定了我
真正的读者,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一
想到这部书将有几十万人爱惜和保护,我的心
里便充满了幸福。这才是原初的、作家的幸福。
为了夺取它,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任何苦楚都
是可以忍受的。我举了意。”(8)这使我们想起鲁
迅对自己文字的态度:“速朽”。他一方面大概是
与张承志有共同的心理,看到人们“不守信用地
离开”,对民众极度失望;另一方面,却与张承志
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理,那就是鲁迅前面的路是
虚无的,他在《过客》那篇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
楚了,但张承志却选择了宗教———这一对他来
说非常真实的道路。所以,张承志对文学的态度
219
徐
兆
寿
张
承
志
的
文
学
世
界
与一般人不同,他要让人们忠实于他,不背叛
他。他觉得自己的文字是真理,而他则是要“几
十万人爱惜和保护”的圣人。他不愿意接受(或
者难以接受)非议和非难,而这种心理一方面
是与他的文化信仰相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
是其性格所致。自从他接受了伊斯兰文化信
仰,张承志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传统
文化观念之下的张承志,而是一个杂合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伊斯兰文化的张承志。在他身上,
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将进行一次大
的综合和融汇。这可以从他的《清洁的精神》中
看出。
正是从这样一个心理背景下走出来的张承
志,在后期才写出了更具魅力的散文集《夏台之
恋》、《鲜花的废墟》。从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
张承志已经由九十年代的激愤、凌厉逐渐转向
沉郁、深邃、浑厚,虽然其抵抗强权文化的立场
不变。这是值得人们去研究的。
看到这样一个张承志后,我们再回过来看
看他到底怎样看待自己的红卫兵心理。他在接
受美国学者的采访时分析道:“红
卫兵最宝贵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造反精神。这里
面有好的和坏的一面。好的就是他们彻底攻击
已经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坏的就是他们坚持
‘成分论’。批判坏的一面、保留好的一面是困难
的。因此,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红卫兵并不困难。
困难在于当每个人说它好的时候,你指出它不
好,反之亦然。”“在中国,红卫兵的事情还没有
拿出来讨论。还不能自由地那样做。原因是,在
‘四人帮’的日子里,没人敢说‘文革’是坏的。因
此,也就没人敢说红卫兵是坏的。连讨论这类事
都不做。同时,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责
备‘文革’中的一切事情,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
红卫兵的恐怖想象。”
这段话仍然是在他处于激愤阶段的一九九
五年讲的。可见,在那个时候,张承志那样“自
豪”地说自己是“红卫兵”一词的创造者时,他并
不是完全的沾沾自喜,而是充满了一种理性的
态度。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二十世纪是
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
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
便如此我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后果给我们的
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9)事实上,
这种理性的分析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
学者锁晓梅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张承志论》中对
这一方面有充分的论述,她写道:
在早期作品《刻在心上的名字》中已显露出
他对红卫兵原则与精神的深刻反思。这篇作品
由两条线索构成,第一条线索为:小刚(红卫兵知
青)想要一个红卫兵一样的名字,牧民桑吉阿爸
则给他讲述了传说中的吉尔格拉为寻求吉祥的
名字而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向草原,草原得以
滋润,人民因而得到幸福的传说故事,他也因此
获得了追寻的吉祥名字。通过这则富有启迪意
义的故事,阿爸启发小刚:只有为人民谋求幸福
才可以获得理想中的名字。接着第二条线索出
现:草原上刮起肃清“内人党”的狂风,乌力记大
哥也被卷人狂风之中,小刚由此陷入自己信奉
的革命理想与个体的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冲突
之中,最终是红卫兵精神压倒了朴素的情感,使
乌力记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而去,这使他与牧民
之间产生很深的隔阂,在深刻反省的同时,他通
过行动为自己赎罪:他与其他知青一起卖力地
打井以弥补对桑吉一家造成的伤害,井终于竣
工,他也得到桑吉一家的原谅,主体心灵也因此
得以救赎并获得“阿拉丁夫———人民的儿子”之
名。至此两条线索归至一处,主体此时顿悟到了
革命的前提和原则:红卫兵的前提是人民的利
益和对人民的尊重与信任。若失去这一前提,红
卫兵精神犹如无弓之矢,只能是无方向的乱射,
将会造成不良后果……他强调红卫兵的错误之
处是失去了“为人民”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
神。(1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张承志对红卫兵精
神并非很多人批判的那样充满了执拗,而是不
断地在反思。他不愿意与流行的观点一致。但其
狂热的宗教情绪和义愤的文字给批评者留下了
话柄。从张承志后期的变化可以看出,那些批评
他虽然不会接受,但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地改变
了他。尤其是他后期皈依宗教后,他的心绪明显
地走向了宽容。这使人不难想起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在青春时期对
上帝充满了怀疑和反叛,发表了很多让他后来
不可思议的言论,也做了很多让他后来难以置
信的事情,但他一直在追求真理,从未放弃过,
最后,在经历种种心灵的磨难之后,他重新回到
了上帝的身边。张承志虽然没有写过类似于《约
220
评
论
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小说,但他个人似乎一
直在不断地完成这样一种心灵的转向。他早期
的草原系列小说充满了忏悔之意和感恩之情,
是因为他接受了草原民族的佛教文化。后期,他
接触到了自己的母族文化伊斯兰,还没有完全
皈依宗教时,他成了一个文化和道德的斗士。也
许人们没有注意到张承志力图想皈依的那种迫
切愿望。这在《心灵史》的代前言里面就有表现: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
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
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
容的感情。”“我找到了。”(11)这是一种心向宗教
的心理,一种终于想摆脱“恶”一心向善的感念。
最后,他在逐渐皈依宗教后,他的灵魂有了依附
感,开始走向成熟和平和。
关于这种皈依,有论者认为,这是张承志
“寻父”的结果。由于张承志早年失怙,所以他从
《北方的河》开始就始终在寻找精神上的父亲,
同时,在草原系列作品中呈现了强烈的恋母情
结。“这样,《北方的河》以后,张承志的寻父之旅
就没有走向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走向了它的
边缘,由草原走向了从新疆天山山脉到甘宁青
黄土高原广大地域的伊斯兰世界,创作了《残
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一直到《心灵
史》等小说。如果说张承志的草原小说其主人公
大多是女性,那么很自然的,在这里则主要是一
个男人的世界。而在此之前,从《春天》、《大坂》、
《凝固火焰》到《北方的河》,等等,他已经塑造了
一个个男子汉形象。既然张承志还没有寻到父
亲,还在寻父的途中,那么,面对世俗化潮流,匹
马单枪、立志抵抗的张承志就要极大地调动自
己的主观意志和英雄气概。”“他对自我的定位
始终是‘儿子’。”直到《心灵史》为止,“张承志已
经找到了他的‘父亲’———生活在大西北黄土高
原的伊斯兰回教的分支哲合忍耶。”(12)
这种论述是符合张承志的精神追求和内在
心理轨迹的。也可以说是他从此岸的世俗无常
世界终于找到了彼岸的永恒世界。
三、为谁写作
人们常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的
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每个
人都想为时代立言的时代。张承志就是那个时
代的弄潮儿。《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充分地表
现了这种色彩。前者更多地表现了诗人的气质,
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了其哲学的思辨。毋庸置疑,
张承志在那个时代的写作目的非常明了:为人
民写作,为大众立言,为时代立行。在那个时代,
个人的追求与中国集体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
那时的写作既为他自己,也为大众。这个大众便
是他所说的“人民”。
但是,自接触伊斯兰信仰之后,张承志的创
作目的开始发生转移。他把读者慢慢地从漫无
边际和目的的大众移向了少数人,最后定位在
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群体,或他的追随者们,甚至
按他的说法,就直接圈定在哲合忍耶教派内。在
他的《心灵史》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他
这样写道:“我便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背
叛的读者———哲合忍耶。”然而,张承志的内心
还是在犹豫。这是他过去所接受的文化所决定
的。于是,他又说:“还有你们———我并没有忘记
你们,我的汉族、蒙古族,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
追随者们。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忘记你们。我
用汉文写作,我落草于北京,我远离我的哲合忍
耶———也许直接援助我的正是你们。你们不能
够因为看见我走进了那片黄尘弥漫的沙沟,就
以为我舍弃了你们。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
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
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
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
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完后发现,
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
卖的货真价实。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
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各种异
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与
你们一块寻找人道。”虽然在他的内心里,他依
然是居高临下,所有赞成他的不过是他的追随
者而已,他自负的心理难以遮掩,但是,终于还
是笔锋一转,写道:“对于我在一九七八年童言
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人嘲笑的‘为人
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
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
信。”这两句直接告诉人们他的创作目的的转
移。他认为以前的他太单纯了,现在他要深刻,
所以他宁可选择少数人。然而,他又认为,这种
对少数人的选择并非真的少数人,也并非真的
只指哲合忍耶民族,而是广泛的心灵:“为了你
221
徐
兆
寿
张
承
志
的
文
学
世
界
们———哲合忍耶以外的世界能读得通顺些,我
在这篇前言里尽量介绍了一些常识。我和哲合
忍耶几十万民众等待着你们。我们把真正的期
望寄托给你们———汉族人、犹太人、一切珍视心
灵的人。发掘出被磨钝的感性,回忆起消逝了的
神秘瞬间,正视着你们经常说到的爱心和人
道———理解我们吧。”(13)
他最终解释了后期创作目的:从哲合忍耶
走向世界,直到伊斯兰教的起源之一犹太教那
儿。他的目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他完成了
一次宏大的转移,而这次转移竟然是从一个极
小的群体和一个名叫沙沟的地方开始的。
在这次转移中,他的创作与其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的创作有了大的区别。那时,他与整个中
国主流文化是合一的,现在,他开始走向边缘。
他与时代的主流文化不再合流。泛泛的由原来
的国家集体意识之下的人民性消失了。由他个
人认定的新的民众产生了。
应该说,这是他创作目的的第三次转移。在
这一次转移中,他个人的信仰与他所认定的目
的也是一致的,但与目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分流
了。这也符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知
识分子的心理转向。在此之前,由于单一的价值
观、世界观、集体理想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知识
分子个人的理想与中国的国家理想相一致,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几次运动的影响,中国
的知识分子接触到了来自世界的多元文化和价
值观,并且在改造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
面遭遇了一些挫折,中国的知识分子便慢慢地
理性起来,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中
寻找定位,另一方面,又多从西方文化和整个世
界多元文化中重新整合自己的价值理想。先锋
文学在很大意义上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和助
力。九十年代以来,一部分作家转向中国传统的
儒家,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外省书》和
《九月寓言》;一部分作家转向中国传统的道家,
如贾平凹的一部分作品;还有一部分则转向基
督教,如北村的《愤怒》、余杰的部分作品;还有
一部分则转向多元混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余
秋雨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散文写作者。在这种
转向中,转向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则寥
寥无几,但张承志是一个异数,他转向了中国文
化不怎么熟悉的伊斯兰文化。
从后期张承志的几部散文集《夏台之恋》、
《鲜花的废墟》来看,他的行踪主要集中在寻访
伊斯兰文化的发生、发展脉络。在这些文字和声
音中,我们不难听出他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代表
第三世界民众向一切强权文化进行斗争。
他的目光从西海固的沙沟越过中国,越过
阿拉伯,又从阿拉伯回视整个被强势文明———
基督教文明所浸淫下的其他文明,特别是一直
与基督教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伊斯兰文明。
四、意义与价值
对于张承志前期的创作,评论界已经评说
得很充分了,也没有多少异议,但对于其中期
创作则莫衷一是,其时的作品主要有《金牧
场》、《心灵史》、《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
《荒芜英雄路》等。有些选本里内容大概有些重
复,但大致的作品就是这几部。这些作品因为
张承志的宗教精神而受到很多非议。在此之后
的作品在数量上越来越少,主要文学作品集中
在散文集《夏台之恋》、《鲜花的废墟》。对于后
期作品,评论界则注意得很少,对于它的评价
也不多。
表面上看,张承志中后期的创作与文坛主
流越来越远,其影响似乎也越来越狭窄,但文学
的价值似乎正在这种“远离”中。张承志这两个
时期的长篇小说主要是《金牧场》和《心灵史》。
这两部作品在评论界有很多杂议。我个人认为,
第一部作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想把二十多年来
的想法集于一体,反而过于沉重而庞杂,有思想
大于形式之感,和主题先行之缺憾。这也就是后
来作者为什么要删减重新出版的原因。第二部
作品《心灵史》在文本价值和题材开拓等方面是
很有价值的,但因为所载历史之沉重,所负使命
之强烈,所在乎的读者太鲜明,以及他所追求的
“永恒”功利之色彩太强烈,致使这部作品仍然
具有主题先行之特点,反而使作品显出一些狭
隘来。但除了以上缺憾之外,这两部作品在当代
中国文学中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文学史意义,
尤其是《心灵史》。其后期作品主要是散文、随
笔,这些作品一方面仍然具有其鲜明的诗化审
美风格,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自《心灵史》以后
的斗士的形象,使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中仍然
独具魅力。
张承志后期作品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首
222
评
论
先在于鲜明、高昂、后趋理性的精神向度。在以
新写实主义、欲望化叙事为主导的伪现实主义
创作和只强调文本形式的创造而不需要精神高
地的现代主义创作中,张承志这两个时期的作
品是非常独特的,几乎与前两者是对立的。他个
人的理解也如此。他认为自己上承鲁迅,下启新
的时代。的确,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能够
站在时代的远处而对当下社会诸现象尤其是文
学道德现象进行鲁迅式的批判的作家寥寥无
几。在《金牧场》和《心灵史》两部长篇中,作家向
读者倾诉和展现的是其鲜明的精神向度———伊
斯兰文化为主体的精神,一种伊斯兰精神中鲜
明的排外主义倾向和高昂的牺牲精神,还有他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那儿继承来的“清
洁的精神”。关于这种“清洁的精神”,可以理解
为荆轲刺秦王式的反专制主义,也可理解为许
由拒绝尧帝时的那种绝对的个体主义和道家精
神,还可理解为中国儒家和道家共同赞赏的许
由、屈原式的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先知精神。总
之,这种精神在此后的散文写作中,一直成为张
承志的主要精神倾向。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因为
过分地强调自我,所以遭遇很多人的不快。余杰
便是站出来的一个。余杰在《皇帝的新衣———关
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一文里写道:“他越是
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
阵的恐惧;越是一尘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
获得极为世俗的发行上的成功。”(14)在这篇文章
里,余杰对张承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红卫兵这
一把柄上。针对这一点,张承志回答道:“他们从
来不会完整地引用我的文章哪怕是一个自然
段。他们把文学的抒情与政治混淆起来。是不是
宣扬一种思想就得为它的所有后果负责?是不
是给毛泽东与红卫兵说一点最起码的公道话就
得为那场浩劫负责?是不是宣扬哲合忍耶就得
为伊斯兰教的一切恐怖主义负责?”关于这一
点,在前文中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事实上,两
者都是思想的斗士,但为什么两者又显得水火
不容呢?刚刚成长起来的余杰只是写了一些读
书札记,还算不上是研究,对张承志的整体把握
也不到位,更何况当时的张承志正是其精神的
疯狂期,也是众人批判的主要对象。其实那时他
们的批评还有些意气之争。但从根本的文化精
神上分析,余杰与张承志的对立是避免不了的,
前者后期渐归基督教精神,后者则归入伊斯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迟早是对立的。这
是他们所皈依的文化的历史所决定的。
其次是丰富了当代文学的题材。伊斯兰文
化在中国是一个始终没有与传统文化混同合一
的世界文化,中国人对其了解并不多。尽管在近
百年来也有不少人写穆斯林的生活,来反映伊
斯兰文化,但人们熟悉的很少,霍达的《穆斯林
的葬礼》算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近年来,宁夏的
石舒清等回民作家的作品多反映回民的生活,
有一些影响,但这些作品也都是站在目下流行
的文化立场上来写作的,只是描摹一些风物、人
情,还没有像张承志这样直接站在伊斯兰文化
精神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作品。在“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今天,张承志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题
材的大胆开拓和深掘。在中国,穆斯林生活的区
域不仅仅在西北———西北只是他们集中生活的
一个区域,还分散在北京、山东、广东、西南各
地,而伊斯兰文化又是世界四大主流文化圈(基
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中国
的儒道文化圈)中的一种,应该有人去写,去丰
富中国和世界的文学。
假如我们有兴趣去读张承志的后期作品,
便会又一次地惊讶。张承志在后期的行走与写
作主要集中在以伊斯兰信仰为中心的第三世
界。他认为,基督教世界是目前整个人类的强势
文化,但也是强权文化,它压迫着第三世界的文
化,如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以及
其他一些弱势文化。第三世界的文化需要苏醒、
自醒和自信,但获得这些的一个前提就是反对
基督教强势文化。这种思想与同样是穆斯林的
后殖民思想的代表萨义德的观点是一致的。基
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有共同的源泉———犹
太教,但是,两种文明在历史上始终处于水火之
势。围绕巴勒斯坦,曾经有著名的十次十字军东
征,当代又有无数次与中东之间的战火。历史积
怨与文化对立太久。张承志在逐渐走入伊斯兰
世界之后,也便逐渐走进反对基督教文明的世
界,但是,张承志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出对话、宽
容、和平的概念。这是一种进步。
当然,张承志的文化观念是需要重新评估
的,一些是符合于人类普遍追求的正面价值的,
还有一些是需要商榷的。比如,张承志在文学中
始终充斥着的英雄主义观念,一方面有专制主
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男权文化的象征。“英雄”
223
徐
兆
寿
张
承
志
的
文
学
世
界
一词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从母系文化向男权文化
过渡时的一个产物,也是人实现自我,要求别人
服从的一种本能。这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有进
步意义,但在强调两性平等的今天应该重新审
视。比如,对红卫兵、“文革”、毛泽东以及日本军
国主义的一些观点,是应该从文化上深度梳理
的,不应该简单地评价。张承志是一个成长于
“文革”时期,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转型于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个作
家,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他所探讨的一系列
文学主题其实都是当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文化命
题。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的浸染,
最后又沉迷于伊斯兰文化。应该说其文化视野
是深广的。但是,也恰恰在这些时期,中国人对
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些片面,传统文化意识也没
有苏醒,身处其中的他自然也带有这样一些时
代的缺憾。这些缺憾恰恰就表现为其过分的情
绪化的表述,而缺乏必要的理性精神。因此,张
承志在其文学中所表现的一系列文化精神是有
缺憾的,这是值得注意的。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371页。.
(2)王必胜:《金牧场:诗化哲学》,《昆仑》
1987年第5期。
(3)张承志:《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含
义》,《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年1期。
(4)张承志自己认为是在1984年,他在《告
别西海固》中说:“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
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
舞,我们在上坟。”
(5)聂茂编译《知青作家群体谈“文革”》,翻
译者称,他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图书馆借到一
本英文专著《初升的太阳———与中国“迷失的一
代”作家对话录》(Leung,Laifong,Morning
Sun———InterviewswithChineWritersofthe
,NewYork,London,
England:,1994).http://www.e-
/Article/?Arti-
cleID=346.
(6)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
喜剧》,《文学自由谈》1995年2期。
(7)陈国恩:《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文
学评论》,1995年。
(8)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马进祥编
选:《张承志回族小说》,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3页。
(9)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以笔为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0)锁晓梅:《张承志论》,兰州大学图书
馆,2007年版,第33页。
(11)张承志:《走进大西北之前》,周政保、
殷实选编:《五人美文选》,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98页。
(12)吴三冬:《张承志论》,《文艺争鸣》,
2009年第6期。
(13)张承志:《走进大西北之前》,周政保、
殷实选编:《五人美文选》,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98页。
(14)余杰:《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第299页。
责任编辑金珠
224
本文发布于:2023-03-03 16:08:47,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7830928115353.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文学世界.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文学世界.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