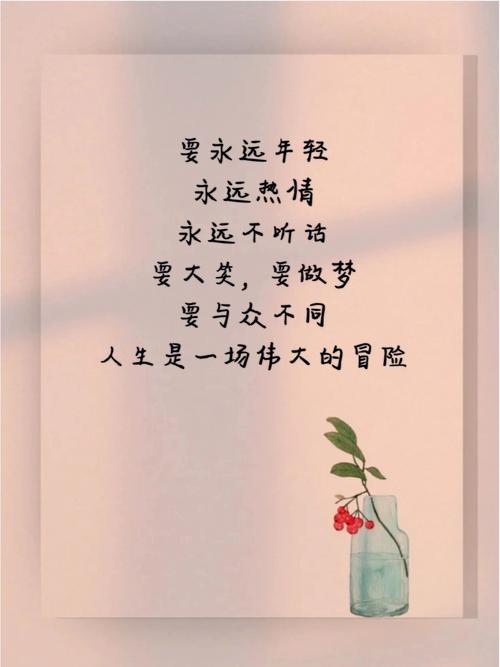
关于“黄金十年”的再思考
摘要:提到近代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很难用积极的词汇来形
容那个时代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导致了至今中日之间也是问题与摩擦
不断。但是,在近年的中国学界,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样一个说
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谓的“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是美国历
史学家任达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
可谓不新颖独特,让人们对于近代的中日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究
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存在,那么对于那
段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讲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何谓“黄金十年”
关于“黄金十年”这样一个概念,最先提出的的任达教授,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在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一书中清楚地谈了这个概念的由来:1986年夏
天他在《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十
年蜜月”这一概念。对此,东京大学的平超生罚款标准 野健一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用“十年蜜
月”一词是不适当的,因为从当时日本的行为来考虑或者判断的话,完全是对本国利益和
安全的关心,用十年蜜月一词就会暗示着中日之间存在着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实际上
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到了1986年底,任达应时任日本亚洲学会会长薛龙博士的邀请,写
出了《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正式形成,从
而也为围绕“黄金十年”这一概念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奠定
了基础。
任达教授认为,中国在1898年到1910年这十二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
成就便无法取得。与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的而非
侵略的角色。不管怎么样,从1898年到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地相对和谐,堪
称“黄金十年”。[1]7
二、以日为师——“黄金十年”出现的契机
有关“黄金十年”形成的背景,要分成清政府和日本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清政府,出
现的“外交窘境”是重要的原因。甲午战争中,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给老师狠狠的上了一课,
整个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耻辱。《马关条约》的签订,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大大加深
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日本的举动同时也刺激了列强敏感的神经,早就觊觎中国东北的
俄国率先发难,联合德、法两国,共同要求日本不得染指辽东半岛,否则将实行武装干涉。
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嘴边的肥肉吐了出来,另外又向清政府榨取了3000万普通话标语 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大喜过望,不但给俄、法、德三国的数十名外交家颁发了奖
章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做出的贡献,而且与俄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国内的亲俄浪潮也掀起来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通过与俄国的结盟以“共同防御”日
本。时人有曰:“慈禧与李鸿章固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
无不以连俄拒日为言矣”。[2]94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经过维新而摆脱落后走向
富强,鲜明的提出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有驻日参赞黄
遵宪及著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但在当时他们的意见并未成为主流,无论是掌握大权的
中央政府或者是颇有实权的地方督抚,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在《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关系看起来进入了蜜月期,清政府满心希望
在俄国的帮助下能够摆脱危机。但俄国及其西方伙伴却做出了一系列伤害中国的行为:
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报复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为借口,占据了长期以来
梦寐以求的胶州湾及青岛炮台;俄国随即在15日以又以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为借口,进
驻旅顺、大连。之后,列强开始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几乎将中国的领土瓜分殆尽:俄国的势
力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两省的一部分,日本在福建,法
国在广西和云南、广东两省临近越南的地区。这其中,俄国的侵略行径尤为恶劣,不仅辽东
半岛完全落入其手,甚至整个东北也都成为其势力范围。无疑,列强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
恐慌及戒备,对于俄国人也不再信任。在这个时候,日本人“适时的”的出现,并主动伸出
了“橄榄枝”。
日本方面的主动看似非常费解,但实际分析起来就会很清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
强盛,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也开始加深。甲午一战打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种
种利益,实力骤然增加,引起列强的不满和担心。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然不容许日本
继续强大,因此出现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西方列强这种削弱日本、限制其发展的行为,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日本学
者、专家、乃至于普通民众感到了危机,社会各阶层开始对近代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展开了
一系列激烈辩论。
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在近代国家发展道路上就一直存在究竟是成为“大陆国家”还
是“海洋国家”、是奉行“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的争论。尽管历届日本政府均
把扩张侵略政策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但很多时候,协调外交、均势外交政策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
因此当一心“脱亚入欧”、想要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遭到当头一棒后,日本社
会各阶层都开始进行反思,思考日本的国家定位:脱亚入欧,成为侵略邻国的急先锋;还是
融入亚洲,成为东亚盟主,提携中朝两国。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作为对日本的警告,明白无疑的表明了西方列强的态度,那就是
绝不允许日本过于强大。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日本政治家们开始奉行一种新的国家战略:“清
国保全论”。具体来讲,就是由日本来帮助中国觉醒、改革,增强其实力,抵抗列强的瓜对牛弹琴 分
和侵略,从而得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清国保全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不仅像东亚
同文会这样的组织将其作为组织纲领,甚至日本政府也在一定时期内将其作为既定国策。[3]62
在一时期,大量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乃至政府高官,不断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宣传
“同文同种”,拉近中日双方的关系,号召“清国保全”。著名的近卫笃麿公爵在1898年初
发表的《太阳》中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要求日本摆脱战后对中国的鄙视心理,
通过旅游、社会接触、土地调查等直接了解中国。他提出不应犹豫观望,使白种人对黄种人
的侵略得以加速进行,以阻止迫在眉睫的大规模种族冲突。[4]52
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所写的一篇评论中也提到:
中国战败后的四五年来,一朝反省,对日本人的态度已由轻蔑嫌恶转为尊敬,开始重视向日
本学习。为此,“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效的方法”,并呼吁“日本帝国
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避免破坏彼国委托人之大事业”。[5]44
诸如此类,日本民间积极要求寻求中日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作为日本官方的代表,
当时的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观点无疑更具有代表浙字组词 性,他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内阁
期间,表明了他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为“大隈原则”:他认为日本长期
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以
酬往昔师导之恩义”。[6]56
三、“黄金十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
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
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
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一场“文化反哺”由此开
始。
派遣留学生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
药、建筑等自有“销售总监 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以来,中国
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
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一部分的日本,而是
中国。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
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
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
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000
名左右)。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
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7]105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
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
问等)。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
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
同消同长。至于留学日本的原因,在此不做赘述,以下两段史料就很能说明问题。“六君子”
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
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
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
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8]7
这些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们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
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
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
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
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
籍。这些被翻译的书籍成为了中国思想革命的源泉。同时,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
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
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黄金十年”很重要的实例是清末新政,而清末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在这一
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
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
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涵盖了教育、军事、警察及监狱、
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等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四、对于“黄金十年”的反思
“黄金十年”是任达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
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的确不无启发。但是按照他的
想法,把中日关系的“黄金期”定位于1898年到1907年之间的标志是什么,原因何在,这些
都没有很明确的进行解释说明,而且把日本在这段时期中日关系扮演的角色夸大为“无私帮
助的伙伴和朋友”,日本对中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热情”的,并且认为“我无法接受
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纪转换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即使在日俄战争时,我也不能说日本
对中国有侵略企图。太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有各种矛盾的看法,而且太多日本契约教师和顾问
在为中国尽力,我实在不能认定日本对中国有任何企图。”[1]2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从当时
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亲密无间,日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
的侵略企图。
试举一两个例子说明。
1900年,中国发生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为了镇压义和团并且进一步操纵清政府,
从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攻占了北京。在这
次侵略战争中,日本不但派出海军舰艇,水兵由大沽登陆,更派出陆军三千八百多人,从大
沽向天津进攻,成为侵略军的主力部队。此后侵华日军增加到八千多人,8月14日攻进北京,
北京的整个北城和东城北部成为日军占领区。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和约》,成为清政
府与外国签订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卖国契约。此次日本出兵中国,除先后在天津、通州、
北京以及其他所到之处抢劫白银367万两外,又从《辛丑和约》赔款的数额45000万两中分得
34793000两。此外,还取得了在中国境内留驻“华北驻屯军”的特权,但日本并未就此满足,
又于1903年10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取得了日本轮船在中国沿海和内
河任意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开辟长沙、奉天、大东沟(今丹东西南)为通商口岸,不
仅进一步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并且为准备和俄国争夺东北地区创造
条件。
时间到了1904年,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日俄战慰问信格式范文 争了。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成为日俄两国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
这两个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出动了百万大军,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惨烈厮
杀。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及一切权益,
以及南满铁路连同其支线的权利和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日本所得的此项利权,经清
政府与日本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概行允诺”之外,
日本又取得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十六个城市开为商埠、改建安奉铁路和鸭绿江右岸森
林采伐权等等。[2]156这样,东北三省南部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这里要特别提到
的是1906年10月日本在旅顺正式成立的“关东都督府”和同年11月正式成立的“南满铁道株
式会社”。前者是政府机构,除了对所谓“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外,还兼有军事权力;后
者在名义上是一个民营的企业组织,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府官办的庞大经济侵华机构。这两
个机构在后来的日本更大规模侵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能证明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不愉快肯定不止上述两例,
但是这两例足以说明,任达教授所定义的中日“黄金十年”委实难以成立。只能说日本采取
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给与中国帮助,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通过武
力的手段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事实上,日本最后发现,自己的企图通过与清政府在“新政”
期间长达十多年的合作,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让大量的留日学生,在新的政府中
也将成为中流砥柱,“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
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
地扩张势力于大陆”的计划完全落空了。[9]37清末新政由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统治,安抚民心,自然地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结束;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却成为
最坚决的抗日、反日人士。其最主要的原因,除了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危机中国的独立生存
等外因以外,最直接的是在于他们留学期间,受到了日本的教育,加深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国家观念。这些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祖国,驱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势力,才能有独立生存可言;因而在回国之后,他们成为了最坚决的抗日、反日论者,领导
人民觉醒。日本妄图凭借“清末新政”时期的“中日亲善”“友好合作”来扩大在华影响,
独占中国这一战略目的的失败,导致了其对华政策的转变,由之前较为“温柔”、“含蓄”的
交流,转变为直接、粗暴的侵略。
所谓“黄金十年”的中日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
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反哺”,
只是再次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
永恒的利益”,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日本又确实“关系密切地使其他外国人嫉妒”,所以不
妨称从“文化反哺”的角度将其定义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1](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8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
[3](美)费正清,马里乌斯•詹森[M].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日)实藤惠秀[M].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
[5]张之洞.劝学篇[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M].上海: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5
[7]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0
[8]1895年—1914年中日关系特点及发展趋势[J].苟维,才智2008年17期
[9]浅析甲午战争后十余年间中日关系的特征[J].湛贵成,历史档案2007年01期
本文发布于:2023-03-20 22:41:31,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fanwen/zuowen/676bba2d96e02fb34bb835d3c61a1cf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国内蜜月.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国内蜜月.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