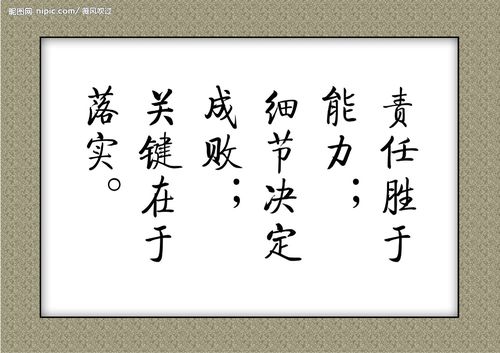
被塑造的经典——清代文评专书中的归有光
诸雨辰
【摘要】归有光是清代文学评论中的焦点人物,其形象在清代学者的批评总结中完
成了“经典化”的历程.清人对归有光的讨论大致延续钱谦益与王夫之的批评理路
展开,重点关注了归有光文章的文辞与义理两个层面,而讨论的对象则是归有光的
《史记》评点及其自身文学创作.在清代复杂的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论争中,归有光
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其形象也不断地被重塑着.支持者赞其文法可学,反对者批其
文章无道,而对其他问题则皆视而不见,彰显了文学经典化历程的曲折走向.
【期刊名称】《求是学刊》
【年(卷),期】2017(044)002
【总页数】8页(P131-138)
【关键词】归有光;经典化;《史记》评点;多维解读
【作者】诸雨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2
归有光是晚明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力抵七子派的复古文学,开一代风气之先。
除了其文章写作外,归有光的《史记》评点也启发了后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发展,
使他成为清代文学与理论言说中绕不开的人物。
目前对归有光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归有光思想观念、文学特色的研究,
包括他与同时代其他文人的关系等,这是归有光研究的主流。其中较著名者比如刘
尊举从震川论文及写作实践中总结出其“质实”的文学思想[1];吴正岚分析归
有光对文学、伦理、政治等的观念意识,并将其思想观念的来源上溯到欧阳修经学
的影响[2];孙之梅分析了归有光对现实政治与文学等问题的态度,认为归氏在
明清之际具有扭转学风的意义,其中特别提到了钱谦益和顾炎武对归有光的发掘之
功[3]。另一个角度是从后人对归有光的接受来研究其思想与文学,比如何天杰
在对归有光与“唐宋派”文人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归有光并非唐宋派的一
员,“唐宋派”概念的形成是后代文人评说及近代文学史叙事的结果[4]。此外,
黄霖、杨峰等人从《震川先生集》的清人评点中整理清人对归有光的看法,对钱谦
益、黄宗羲、尤侗、陈维崧、吕留良、何焯、方苞、姚鼐、曾国藩、林纾、徐世昌
等20余家的归文评点进行了细致梳理,得出了切实可信的结论。①参见黄霖《论
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1期;杨峰《〈震川先生集〉的清人评点述评》,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
年第5期。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分析归有光思想观念之
渊源,还是辨析归有光与唐宋派的关系,乃至挖掘归有光在明清学风转移过程中的
历史意义,对归有光的研究都处于一种“再发现”的状态。这些研究的逻辑前提是
归有光的形象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完整地认识,震川思想与文论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归有光形象“偏离”了其原初形态呢?这就需要首先考察
归有光成为经典的过程。
归有光去世后,首先对其古文提出肯定的是王世贞和王锡爵,他们分别作《归太仆
赞序》与《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②王锡爵之作系归有光弟子唐时升代作,而
借王锡爵之口说出。。王世贞说归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5](P975)。王锡爵则称赞归文说:“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
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5](P981)
二人对归文都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然而尽管有文坛领袖与内阁大学士的称赞,归
有光的文章却并不为人熟知,除了其政治地位不高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归文还
没有精良的本子,以致其子孙一直“悼震川遗文不大显于世”[6](钱谦益《归
文休墓志铭》,P1160)。直到钱谦益与归昌世、归庄父子等历时三十年搜集整理
之后,才将《震川先生集》整理完成。可以说,钱谦益是晚明推动归有光成为“经
典”的第一人。
钱谦益对归有光的强调主要在文学方面,他突出了归有光对复古派与竟陵派的批评,
这受到钱谦益本人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简要介绍了归有光的
生平后,就切入对其文学的评价:
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
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
[7](P559)
一方面是肯定归有光的《史记》评点,一方面是肯定其诗文成就可与宋六家相提并
论。在此之后,钱谦益重点拈出归有光斥责文坛领袖王世贞为“妄庸之人”的一段
公案,又突出了归有光反对七子派复古文学的思想观念。
与钱谦益不同,同时期的王夫之则对归有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其《夕堂永日绪
论·外编》中对归有光有多次评价,其中无一佳评:
钱受之谓黄蕴生嗣归熙甫,非也。熙甫但能摆落纤弱,以亢爽居胜地耳。其实外腴
中枯,静扣之,无一语出自赤心。蕴生言皆有意,非熙甫所可匹敌。
陈大士史而横,金正希禅而曲。若其离此二者,别寻理际,独至处自成一家,固贤
于归熙甫之徒矜规格也。若经义正宗,在先辈则嵇川南,在后代则黄石斋、凌茗柯、
罗文止,剔发精微,为经传传神,抑恶用鹿门、震川铺排局阵为也?
以“外腴中枯”评归熙甫,自信为允。其摆脱软美,踸厉而行,亦自费尽心力。乃
徒务间架,而于题理全无体认,则固不能为有无也。且其接缝处矫虔无自然之度,
固当在许石城、张小越之下。[8](P3273、3273、3281)王夫之坚持以“外
腴中枯”评价归有光的经义文章,认为其虽然表面上摆脱纤弱文风,但是骨子里缺
乏对义理的体认,只是个空架子。更关键的是归有光还就专意于搭架子,这引起了
王夫之的极度反感,认为正是归有光、茅坤等人的文法败坏了文风,进而也败坏了
士风。钱谦益说归有光得《史记》之风神脉理,王夫之就批评说那只是铺排局阵的
空架子;钱谦益说归有光诗文超凡脱俗,上达欧、曾,王夫之就说那是“外腴中
枯”,徒有门面,没有欧、曾的学理修养。可以看到,王夫之对归有光的评论与钱
谦益可谓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应该说,王夫之对归有光的评价是过苛的,至少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样是讨论
时文,清初另一位儒者吕留良就称赞归文在文法上“于曲转中,但见其腕力之遒雄,
径路之昌达”[8](《吕晚邨先生论文汇抄》,P3344),在学问上则能“精乎
理,熟乎经,驰纵乎古今文字之变化,而后能顺心脱手,快然出之而不疑”[8]
(《吕晚邨先生论文汇抄》,P3330)。在此基础上,吕留良甚至把归有光放到与
朱熹一般的高度,他不止一次地把归文与《朱子集注》相提并论,称赞说《集注》
圣在不可改易一字,而近人“惟归震川先生行文见得此意,其至平极淡处,都从道
理千锤百炼而出”[8](《吕晚邨先生论文汇抄》,P3324)。吕留良也是易代
之际的思想家,同样学本程朱理学,而其与王夫之面对同一个古人竟然有如此霄壤
云泥的评价,实在令人错愕。比起来还是黄宗羲的批评折中而公允一些,他作《明
文案》,在序中称“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9](P18)。基本上肯定
了归有光在明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但也不刻意拔高到欧、曾、朱的程度。
钱谦益应该是出于学风、文风的相近而推崇震川,吕留良可能是表扬震川有些过分,
然而如何看待几乎不合实际的王夫之的一番话呢?在黄霖看来,很可能是出于明清
易代之际的民族情绪,因为“大力吹捧归有光的钱受之(谦益),是归有光学生唐
时升的学生辈,是个大名鼎鼎的降清贰臣,像这类‘归煕甫之徒’,王夫之是从心
底里十分厌恶的”[10]。这种解释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无论如何,在归有光去世不久的明末清初,就开始了归有光文章的经典化历程,其
发轫者是钱谦益,肯定的角度一是文法、二是文章。而这引起了来自思想界的回击,
王夫之尖锐地抨击归有光文章胸无义理,徒务间架。当然,思想界内部也有吕留良
为代表的另一端声音以及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和派。然而可以鲜明地看到,在归有光
走入人们视线的开始,批评的声音就聚焦在了文法、义理这两个关键要素上。而这
也成为一种背景式的批评场域,影响了后代文人士大夫对归有光形象的塑造。
清代文评专书中的归有光批评大致上延续了晚明清初对归有光的评价,主要沿着与
《史记》相关的文法以及归文内在特征两个方向展开。
首先看与归评《史记》相关的论说。根据韩梦周的《史记例意跋》,清代流行的归
评《史记》至少有桐城方氏本、武陵胡元方本、桐城张叠来本、汪武曹藏本等十余
个版本,可见其流传范围相当之广,在韩梦周看来,“为震川之学者,不可不读
《例意》也”[11](于学训《文法合刻》,P439),对此书做了相当高的评价。
与韩梦周类似,方宗诚也说:“方望溪《左传义法举要》,归震川《圈点史记意
例》,读《左》、《史》者不可不阅。”[8](《读文杂记》,P5718)他们都
把归有光的《史记》评点视为读《史记》的必读书,可见归评《史记》的影响力。
归评《史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刺激了清代文论的生成,桐城派的刘大櫆和姚鼐均从
文法的角度高度肯定了归评《史记》对《史记》文法的发现之功。比如刘大櫆在其
论文“十二贵”中提出“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丘壑远大。丘壑中,
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8](《论文偶记》,P4111)其理论
来源就是归有光对《史记》“大手笔”,“连山断岭,峰头参差”,“长江万里图”
等的点评之辞。虽然刘大櫆没有给出评价性的话语,但其认同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更直接地称赞归有光的是姚鼐,他讨论作文之法说:
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而入之。
韩昌黎、柳子厚、欧、苏所言论文之旨,彼固无欺人语。后之论文者,岂能更有以
逾之哉!若夫其不可言喻者,则在乎久为之自得而已。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
者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可借一部,临之熟读,必觉有大胜
处。[11](《惜抱轩语》,P399)
姚鼐说文法有可以言喻之法,比如韩、柳、欧、苏论文之法,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
峰。而在此之外,还有需要自己体会的不可言喻之法,没有现成的文法可以参照,
而必须心领神会。当然,领会不可言喻之法还有一个很好的途径,那就是阅读归有
光的《史记》评本。因为归评《史记》的圈点都很有启发性,通过细心揣摩其圈点
与评语,就可以领会不可言喻之法,所以姚鼐奉劝后学都应借一部归评《史记》来
熟读。
姚鼐还把归有光和方苞的《史记》评点做了一番比较。方苞也有一系列讨论《史记》
的文章,比如《书封禅书后》《又书封禅书后》《书史记十表后》《书史记六国年
表序后》以及一系列《史记》列传的“书后”等,其中重点申明了方苞的“义法”
理论: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
“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
之文。[12](《又书货殖传后》,P58)
这段文字提出了“言有物”与“言有序”两方面的标准,并且要求“义”与“法”
互成经纬,整合为一,堪称方苞“义法说”的纲领性文字。而姚鼐则对方苞的《史
记》读法并不十分满意,他认为如此论《史记》其实并没有超越归有光:
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
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
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11](《惜抱轩语》,P401)
以“义法”论文,固然是方苞所得与创新,但是在姚鼐看来这是简化了《史记》的
文学精神,因为“义法说”并没有彰显出《史记》的远大、疏淡与非凡之处。而道
出《史记》大手笔、大波澜等审美意趣的恰恰是归有光的《史记》评本。姚鼐认为
在文学性的发现上,归有光的评点可谓后无来者。
在刘大櫆、姚鼐等人称赞归评《史记》的同时,当然也出现了对此书的讨伐斥责之
辞,其中的代表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篇中,章学诚用了有些夸张的叙
事性文字描述了友人左良宇对此书的重视。而在章氏看来,明代嘉靖、隆庆年间,
文道已经断绝,归有光站出来抨击王世贞等人的复古是对的。但是仔细考察归有光
之文,又没什么内涵,所以他对归有光的基本评价是:
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
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13](P334)
正因为不能“闳中肆外”,所以在章氏看来,归有光只得《史记》皮毛,完全没有
体会司马迁的深意,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章学诚所看重的“史学”功夫与“史识”修
养。
章学诚相信“文成而法立”,法不能独立于文而存在,文的关键在道不在法,所以
他用“法无定法”的理论驳斥归有光:
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
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
[13](P337)
当然与此同时,章学诚也网开一面,补充说如果是“不知法度之人”,那么看看归
评《史记》也有好处,毕竟能领会一些道理,提升写作技巧,但是绝不能像某些人
那样把这本书视为必读的“传授之秘”。[13](P337)章学诚主要是站在强调
文道的基础上批驳归有光的,他在《文理》篇中专门搬出程颐“工文则害道”以及
程颢“记诵为玩物丧志”的话作为论点,强调“尊德性”才是行文的根本。同时,
他又举出左思、张籍等人的例子,批评他们号称钩玄提要、号称苦思利索,其实不
过是“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根本没什么可贵之处。[13](P336)
也许是因为在友人住处发现了归评《史记》并引申出一番讨论,为了给左良宇留一
些情面,章学诚对归有光的态度还比较宽容,总体上有所肯定。但其立论的思路显
然接续了王夫之非议文法的观点,作为史学家,章学诚轻视文辞而独尊义理的态度
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无论是刘大櫆、姚鼐的肯定还是章学诚的批驳,至少在一点上他们能达成共识,
那就是归有光钻研《史记》文法的努力,提升了他自己的文学水平,所以他能成为
有明一代的文章豪杰。而对归有光文学风格的发现与塑造,也是归有光散文经典化
的关键一步。
《史记》是叙事文学的经典,所以清人评价归有光的叙事文时,往往以得《史记》
之法来概括归文。比如张谦宜说:“震川志传行状,其佳者真得《史记》之洁。”
[8](3931)在《茧斋论文》中,张谦宜做了多次举例:
归太仆作《寒贱二孝传》、《困死张自新传》,神芒奕奕,使人欲歌欲哭。伟哉熙
甫!吾谓在潜溪、荆川以上。此无他,以己之心血,渗他人之肺腑,故死者可生,
微者必显。得《史记》之髓,岂在字句之形似哉!
《李廉甫行状》,“采大木”一节,是大文章,可补国史。提撮节目,核而不烦,
中间夹叙他功绩,亦详略相配,故事多文净,不见棘手。此即《史记》八书手段。
若不知此诀,平铺涣散,岂复成文!
南阁记家庭往事,酸沁心脾,字字真挚,句句质核,《史记》之精魄也。《两孝子
传》、《张自新传》不须烹炼,心血淋漓,荆川尚逊其峭洁。[8](P3901、
3931、3931)在张谦宜看来,《李廉甫行状》体现了“详略相配”的叙事之法,
在文法上远胜一般的平铺直叙之文,可谓得《史记》之法。而《寒贱二孝传》和
《困死张自新传》之所以能令人感动,就不仅仅是模仿《史记》的字句问题了,而
是因为归有光能“皆与之疼痒相关,肝胆相照,然后用苦心细笔,一一搜抉而出”
[8](P3900),在共情这一点上得《史记》之神髓。当然,归有光更为打动人
心的是描写亲情的作品,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为代表,“酸沁心脾,
字字真挚”的评价确非虚言,其中同样有情感体验的成分,同样是《史记》之精魄。
叙事之外,还有评家从精神层面论述归有光与《史记》的关系,比如姚鼐赞赏归有
光的风格说:
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章之正传也。
[8](薛福成《论文集要》,P5798)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
[11](《惜抱轩语》,P402)
桐城后学吴铤在其《文翼》中也说:
《史记》风韵跌荡、悠扬妙远不测处有三种:一则苍然而来,一片写去,渺渺绵绵,
高韵深情,令人味之无极;欧阳永叔、归震川风韵得自《史记》者,惟此类为多。
[11](P601)
把归有光和欧阳修对比,点出其平淡苍然之中寄寓的深情绵邈的风韵。又说:“震
川作记,能于柳州外,别有妙远不测之致,均为有得于庄周、《史记》之遗。”
[11](P600)把归有光和柳宗元对比,点出其“窈然而深,如行小港中,忽擢
入千顷湖陂,与天为际”[11](P600)的深远之美。此外,持类似看法的还有
吴德旋,所谓“(归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记》者,乃其最高淡之处也”[8]
(《初月楼古文绪论》,P5048)。方宗诚也说:“归熙甫能于闲事作闲语,而风
韵却自
淡远,是得自《史记》者。”[8](《古文方》,P6054)这些评论无一不从归
文的自然淡远着眼,平淡之中见深情,这可以说是清人对归文的基本评价。①此评
价又广泛见诸归有光文集的评点之中,包括董说、陈维崧、吕留良、方苞、姚鼐、
彭绍升、张士元、施景禹、徐世昌等。参见黄霖《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但是正因为以自然疏
淡为主,所以文章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语言上质而偏俚的问题,最直接提出这一批评的是方苞。方苞自己的古文
理论标榜“言有物”和“言有序”,行文追求“雅洁”。在他看来:
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
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
亦至是而止与?”[12](《书归震川文集后》,P117-118)
方苞认为归有光做到了“言有序”,但是于“言有物”还远远不够,而且语言也不
够雅洁,“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延续方苞观点的还有姚范,他分析归有光文章说:
“震川惟《陶节妇》最胜,然‘岁月遥遥’等句流于轻便,太史公文法无此。”
[8](《援鹑堂笔记·文史谈艺》,P4129)指出其文章中某些句子“流于轻便”,
不够典雅。类似的还有曾国藩,他也认为:
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
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14](《书〈归
有光文集〉后》,P227)不满于归文如“芥舟”之琐碎小气,并以“裁以义”云
云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这些论述与方苞的思路是高度一致的。而有趣的是他们
的归因,他们都认为归有光散文的问题是“专主于为文”而不务义理导致的,这种
看法着实承继了王夫之的批评模式。
文辞“近俚而伤于繁”的问题,甚至是一向对归有光赞赏有加的吴铤也承认“震川、
梅崖集中实多牵率应酬之作,而辞句或伤于烦缓,记律或失之谨严”[11]
(《文翼》,P662)。此外,他还转述了其师吴德旋以及朱仕琇的话,指出吴德
旋和朱仕琇二人也认为方苞所论并非尖刻之辞。但是,为了给归有光辩护,吴铤还
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那些宏大、典雅的词汇本身并不适合归有光要表达的
亲情,所谓“句奇语重之文,岂可施之乡邻戚友间乎?”[11](《文翼》,
P631)而且,在他看来即便是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那样的唐宋八大家也难免于
时有“质而近俚”之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家。
除了词俚的问题,以自然淡远为文还容易导致文章气弱。方宗诚就对此发出了警告:
自姚氏以阳刚、阴柔论文,于是有两派。其实,阳刚不参以阴柔则气必剽而词必激,
阴柔不参以阳刚则气必弱而词必平。近时讲桐城派者主归熙甫而少矫侯、魏,往往
毗于阴柔,虽廉卿、挚甫及佩南皆不免。[8](《古文方》,P6064)
桐城后学学归有光,结果导致“毗于阴柔”的弊病。这里虽然是讨论归文的影响,
但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归文少阳刚之气的不满,所以他说,“试观望溪之高古、惜抱
之清醇、伯言之盘折,何尝有此病”[8](《古文方》,P6064),认为方苞、
姚鼐等人才真的值得作为榜样来学习。
词语平淡而骨气阴弱,这一缺陷还极易与归有光的时文成就混合在一起,成为对其
古文的又一类批判。归有光是明代时文大家,这点大家都公认,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不少人认为他的时文功底拖累了古文。包世臣就持这种看法,他说:
然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
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弥近。子居当归、方邪许之时,矫然有以自植,
固豪杰之士哉。其两集目录,述古人渊源所自,当已。然与人论文书十数首,仍归、
方之肤说,将毋所与接者庸凡,不足发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8]
(《艺舟双楫》,P5257-5258)包世臣批评归文属于“繁芜无骨势”一类,并认
为其原因正在于以时文之法为古文,所以后来之辈也只是“程其格式”而已。作为
恽敬及阳湖派的拥护者,包世臣甚至连方苞也看不上眼,认为他与归有光一样是
“邪许”之辈,他们的理论都是浮浅之说,直到恽敬以骈文和考据矫正古文之法,
才算得上是“豪杰之士”。
而除了在推崇恽敬的时候贬低归有光外,包世臣对归有光几乎无处不贬。他自述阅
读归文的体会,“世臣三十年前,曾览其集,于中酬应之作,居十五六,莫不以架
式腔调为能事,此固不得不尔。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摆脱此四字也”[8]
(《艺舟双楫》,P5278-5279),严厉批评归文的“架式腔调”。又说归有光等
人“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诵读,皆为制举之资,遂取八家下乘,横空起议,照应钩
勒之篇,以为准的。小儒目眯,前邪后许,而精深闳茂,反在屏弃。于是有反其道
以求之者”[8](《艺舟双楫》,P5205-5206)。简直把归文说得一文不名。
当然,从包世臣批判“照应钩勒”这点来看,他的批判逻辑确也同样是出自王夫之
一端的。
归有光散文及其文论在清代始终处于被推崇同时又被批驳的双向重构之中。当然无
论是正面肯定还是反面驳斥,他们都共同成就了归有光散文的经典化历程,正如吴
承学所说:“经典从不同的角度遭到反叛与背离,既是反经典的活力,也是经典的
潜力,还可以说是经典与反经典共同构成的合力。”[15]这一历程的结果,是
归有光终于进入清人的文统序列,成为与唐宋八大家并列而下的存在。朱景昭的论
述最为明确,他说:
尝谓古文之源有二:其一出于《左氏》,变而《国策》,而《史记》,以至韩、柳、
孙、李、欧、王、三苏之属,其传最盛。其一出于《国语》,匡、刘以降则南丰、
新安而已。元、明以来,惟归熙甫学曾而未至,侯近苏,魏近欧,汪仅标格,方则
求兼而未成者。近则姬传先生出入韩、欧,其体颇备,大抵皆八家之支流,无溯源
于《左》、《国》者矣。[8](《论文刍说》,P5753)这段话明确地在从《左
传》《国语》以至唐宋八大家、明清文士的文统序列中确定了归有光的文学史地位。
至此,归有光散文的经典历程已经基本完成。
然而重新回顾这一历程,可以发现清人的论述始终没有脱离钱谦益与王夫之的言说
框架。一方面是称赞其文辞,一方面是讥讽其无道。至于归有光其他方面的思想与
贡献,比如防备倭寇、论水利等实学思想则基本上无人问津,即便论述也多附着于
对单篇文章的只言片语式评点之中。又比如范泰恒在《经书卮言》中提到归有光辨
《古文尚书》为伪书[8](《经书卮言》,P4136),可见其还有一定经学修养。
然而这些论述却淹没于大量关于归有光之文辞、义理等是非问题的争论中,没有引
起更多人的注意。并不是归有光没有这方面的贡献,而清人对此有意无意地“视而
不见”却正有他们的现实目的。
实际上,归有光的经典化历程从一开始就被卷入一个批评的场域,并始终伴随着清
代的文学流派与学术流派之争而展开。方苞评价归有光文辞好而义理不足,这是要
为自己的“义法说”来张本;批评归文质而近俚,也是为了标举自己“雅洁”的古
文风格,是其开宗立说的需要。然而在后人看来,方苞对归有光的批评却有那么一
点言不由衷,毕竟他的文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归有光。而从姚鼐开始,桐城一
派就极力标举归有光的《史记》评点具有重要的文法价值,并且抬高归有光散文的
地位,他们已经把归有光视为桐城派的远祖。而当人们把归评《史记》和方苞的
《左传义法举要》相提并论时,这种同源的意识显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桐城派在姚鼐时代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正是考据派在学术领域占领话语权的时代。
章学诚此时欲以史学融合义理之学,并获得学术话语权,就需要与考据、辞章之学
相抗衡,搬出归有光作为靶子就成为一种打击辞章之学的上佳选择。与章学诚的逻
辑极为相似,蒋湘南批评归有光“有笔无文”[16](P135),包世臣批评归有
光以时文为古文,这都是在消解古文在当时的影响力,从而为以学问为依托的阳湖
派开路而提供理论支持,毕竟批评文人粗疏无学是学者型文人的常见套路。
有趣的是,面对从学术方面引发的攻击,桐城后学一度缺乏应对策略,吴德旋及其
学生吴铤依旧延续姚鼐的路线,还在标榜归有光文法总结到位、文章自然疏淡,只
是批评得更为细致,由姚鼐的宏论进入到具体的微观层面而已,这种回应基本上处
于失语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复兴桐城古文的曾国藩恰恰选择了与史家和考据
家相似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归有光文章没有义理,所写之事过于琐碎小气,以此
反衬他的阳刚之文。
可以看到,支持还是反对归有光、尚文辞还是尚学术,这些根本就不是原则问题,
就连桐城派自己也都没有因为实际继承归有光而对他抱定坚守态度,各家都是借着
言说归有光的话题来为自己立论。换言之,归有光在清代文评的言说场域中,实际
上是一个符号性的角色,归有光这个名字的所指是固定的,但却不是重要的(只是
明中后期一位文士而已),重要的是归有光的能指产生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诚如黄
霖所谓,批评归有光成为各种理论的“试金石”[10],这使得经典化这一过程
本身成为文学场与学术场乃至政治场等诸多场域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
的关于“真理”的讨论,也早就变成了文学家、学问家在文学话语权问题上争夺阵
地的一面旗帜而已,这成为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一种吊诡现象。
至此,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为什么归有光会成为经典,或者什么使归有光成为经典了。
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问题是“谁的经典?”换言之,作家作品一旦进入到这个多重
文化场域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环境中,其发展的方向就已经无法预测了。能指的
狂欢取代了所指本应具有的本质属性,所指将失去(或部分失去)其本质性,而成
为能指争夺话语权的符号工具。这揭示出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另一面向:成为经典
即意味着丧失个体的完整性,意味着任由某个侧面被放大而其他侧面被遮蔽。归有
光在清代文评中的经典化历程,正鲜明凸显了他被发现同时又被遮蔽、被推崇同时
又被扭曲的过程。深情绵邈、自然淡远、言之无物、烦琐气弱……每个文评家都从
他身上“拆”下一个部件重新组合,成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同时,每个文评家又都
不断把自己认同的部件组“装”到那个归有光身上,最终使得归有光的经典化历程
成为一艘“忒修斯之船”,彰显着文学经典化历程的曲折走向。
【相关文献】
[1]刘尊举:《归有光崇尚“质实”的文学思想》,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2]吴正岚:《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孙之梅:《归有光与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
[4]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
期.
[5]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王水照:《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0]黄霖:《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第1期.
[11]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12]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5]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载《文史哲》2010年第2期.
[16]蒋湘南:《七经楼文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本文发布于:2023-03-11 09:39:57,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fanwen/zuowen/1678498798213538.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清代文.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清代文.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