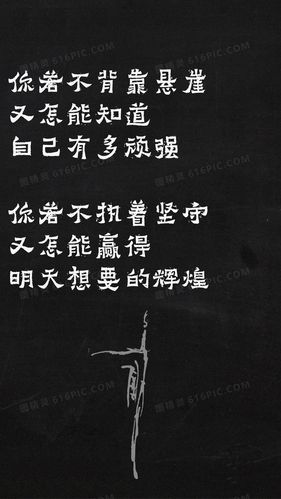
被诬当死(公元692年)
⼗⼋唐朝-22.6.2.1被诬当死(公元692年)
公元692年,壬⾠,武则天天授三年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三年正⽉,亲祀明堂。”
(天授三年正⽉(戊⾠朔初⼀,691年11⽉26⽇),武皇后(武则天、武曌,69岁)亲⾃到万象神宫祭
祀。)
《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长寿元年正⽉戊⾠,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长寿元年正⽉戊⾠(初⼀,692年1⽉25⽇,旧唐书作“春⼀⽉”),夏官尚书杨执柔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
《新唐书卷⼆百三⼗七•列传第⼀百四⼗六上•西域上》:“死,武后⽴其⼦璥。”
(毗沙都督尉迟伏阇雄死后,武后扶⽴其⼦尉迟璥(通鉴作“尉迟瑕”)为于阗王(武则天天授三年
(691年)腊⽉)。)
《资治通鉴卷第⼆百五•唐纪⼆⼗⼀•则天顺圣皇后长寿元年》:“春⼀⽉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
举⼈,⽆问贤愚,悉加擢⽤,⾼者试凤阁舍⼈、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
郎。试官⾃此始。时⼈为之语⽈:“补阙连车载,拾遗平⽃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沈
全交续之⽈:“⼼存抚使,眯⽬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
法,太后笑⽈:“但使卿辈不滥,何恤⼈⾔!宜释其罪。”先知⼤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然
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
之⽤。”
(春季⼀⽉丁卯(初⼀,692年1⽉24⽇),太后(武则天、武曌,69岁)接见存抚使所荐举的⼈员(遣存
抚使见上卷天授元年(690年)),⽆论有才能与否,都加以任⽤,才⾼的试任凤阁舍⼈、给事中,其次的试任
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考异》⽈:“天授⼆年(691年)⼆⽉,⼗道举⼈⽯艾县令王⼭龄等
六⼗⼈,擢为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四⼈为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四⼈为著作佐郎
及评事,内黄尉崔宣道等⼆⼗⼆⼈为卫佐。”疑与此只是⼀事)。试任制度从此开始。当时⼈编顺⼝溜说:“补阙
接连⽤车载,拾遗平平常常⽤⽃量(《容斋随笔》以为此语出于张鷟);可以⽤耙⼦搂的侍御史(《释名》
⽈:齐、鲁谓四齿杷为欋),可以⽤碗模扣出来的校书郎(苏轼诗:“但信椟藏终⾃售,岂知碗脱本⽆模。”)。
”有个被荐举的⼈沈全交补充说:“⾯浆糊⼼的存抚使,眯了眼睛的圣神皇。”御史纪先知将他擒获,弹劾他诽谤
朝政,请求在朝堂上对他施杖刑,然后依法治罪。太后笑着说:“只要使你们⾃⼰称职,何必怕⼈家说话!应该
宽免他的罪。”纪先知⼤为惭愧。太后虽然滥⽤禄位以笼络天下⼈⼼,但对不称职的⼈,也随即撤职,或加以判
刑或处死。她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以驾御天下⼈,政令由⾃⼰作出,明察事理,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杰
出⼈材也竞相为她所⽤。)
武则天重视科举制,⽽轻视依靠特权进⼊官僚集团者。689年,她⾸创殿试贡⼠的作法,并⼤量提拔下层官
吏到中央政府,包括狄仁杰这样的优秀官吏,并不断调动他们的职务,严厉惩罚其中的被指控者,其中也不乏
冤案。
《新唐书卷⼆百⼗⼆•列传第⼀百三⼗四•酷吏》:“郭弘霸,舒州同安⼈,仕为宁陵丞。
天授中,由⾰命举,得召见,⾃陈:“往讨徐敬业,⾂誓抽其筋,⾷其⾁,饮其⾎,绝其髓。”武
后⼤悦,授左台监察御史,时号“四其御史”。
再迁右台侍御史,⼤夫魏元忠病,僚属省候,弘霸独后⼊,忧见颜间,请视便液,即染指尝,验
疾轻重,贺⽈:“⽢者病不瘳,今味苦,当愈。”喜甚。元忠恶其媚,暴语于朝。
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不胜楚毒死。后屡见思征为厉,命家⼈禳解。俄见思征从数⼗骑⾄
⽈:“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惧,援⼑⾃刳腹死,顷⽽蛆腐。是时⼤旱,弘霸死⽽⾬。⼜洛阳桥久
坏,⾄是成。都⼈喜。后问群⾂:“外有佳事邪?”司勋郎中张元⼀⽈:“⽐有三庆:旱⽽⾬,洛桥
成,弘霸死。””
(郭弘霸(旧唐书作“郭霸”;《旧唐书卷⼀百九⼗⼀•列传第⼀百三⼗六•酷吏上》),舒州同安⼈,出⼊仕
担任的是宁陵县县丞。
天授中(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郭弘霸被召到洛阳觐见。郭弘霸奴颜婢膝地对武则天
说:“往讨徐敬业,⾂誓抽其筋,⾷其⾁,饮其⾎,绝其髓。”武后⼤悦,授左台监察御史,时号“四其御史”。
郭弘霸再迁右台侍御史(天授⼆年(691年)),⼤夫魏元忠病,御史们约定⼀同前往探望,郭弘霸故意⾛
在最后,露出⼀副为难的样⼦,在下想看⼀下魏元忠的便液,⽤⼿指沾起⼀点,放到⼝中“品尝”起来,验疾轻
重,贺⽈:“⼤⼈粪便的味道如果是甜的话,可能病还不会好;在下刚才尝了⼀下,味道略带苦涩,说明⼤⼈的
病很快就好了。”喜甚。魏元忠厌恶他谄媚,逢⼈就揭露这件事(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
郭弘霸曾经审理芳州刺史李思征谋反案,将李思征活活折磨死了。后来,郭弘霸经常梦见李思征浑⾝是⾎,
⼿提利刃向他索命,命家⼈请道⼠前来给他驱邪。不⼀会⼉,他恍惚中看见李思征带着数⼗名骑兵冲来,厉声
喝道:“你枉害于我,今天我来取你的头颅!”郭弘霸吓得魂飞魄散,抽出佩剑剖腹⾃尽,顷⽽蛆腐。当时,洛阳
地区很久没有下⾬,⾮常⼲旱。郭弘霸死的当天,天就下起了⼤⾬,并且洛阳城内的⼀座桥也正好修复竣⼯
了。城中百姓们都⼗分⾼兴。武则天问群⾂说:“这两天外⾯可有什么好事吗?”司勋郎中张元⼀说:“好事倒是
有三件,⼀件是久旱之后,天降⽢霖;⼆是坏了的洛阳桥⼜修好了;三是侍御史郭弘霸死了。”)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春⼀⽉,冬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春⼀⽉(新唐书作“长寿元年正⽉戊⾠”,初⼀,692年1⽉25⽇),冬官尚书杨执柔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新唐书卷⼀百•列传第⼆⼗五》:“执柔,恭仁从孙,历地官尚书。武后母,即恭仁叔⽗达之
⼥。及临朝,武承嗣、攸宁相继⽤事。后⽈:“要欲我家及外⽒常⼀⼈为宰相。”乃以执柔同中书门下
三品。未⼏,卒。”
(杨执柔,杨恭仁的从孙,历地官尚书。武后武则天的母亲,即杨恭仁叔⽗杨达之⼥。及临朝,武承嗣、武
攸宁相继⽤事。武后⽈:“我要让武家和外家的⼦侄在武⽒王朝常有⼀⼈为宰相。”乃以杨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
天天授三年⼀⽉戊⾠初⼀,692年1⽉25⽇)。未⼏,卒。)
《为杨执柔让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表•李峤》:“⾂某⾔:伏奉恩制,命⾂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受命
祇惧,载惊魂爽,⾂执柔诚惶诚恐顿⾸顿⾸死罪死罪。⾂闻任官择⼈,哲王之所不易;陈⼒审分,忠
⾂之所宜守。固当使宠私路绝,公直道⾏,然后能谤讟不兴,缉熙有寄。⾂材⾮上达,地则外姻,攀
⽇⽉之末光,承⾬露之馀渥,遂得持衡天阙,摄职⽃枢,尘⼋座之政本,忝三军之戎务。⾼秩厚位,
徒辱于庸虚;弱雾轻埃,竟微于答效。盘桓宠禄,僶俛岁时,⽢受维鹈之刺,宁怀振鹭之举?⽽圣慈
⽆已,天造弥隆,复使参掌国钧,预闻执政,抚已惭悸,扪⼼震越。夫以衡⽯万机,盐梅三铉,参翕
辟之元造,辅丹青之景化。⾃⾮媵莘占渭,出昴乘箕,安可寅亮帝图,弼谐邦教?⾂之蒙蔽,久尘听
览,岂⾜以傍允物情,上回天鉴,承⾈楫之远托,当股肱之重寄?伏愿暂停旒纩,俯择刍尧,搜访才
良,⽤平分之道;屏绝私昵,收曲成之惠。则域中多幸,天下⾄公,岂惟匪服免讥,⾂⽆器满之惧;
固亦得贤斯在,朝有楝隆之吉。⽆任惭悚之⾄,谨诣朝堂奉表以闻。”
()
《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庚午,贬任知古为江夏令,狄仁杰彭泽令。流裴⾏本于岭南。”
(庚午(初三,692年1⽉27⽇),武后(武则天、武曌,69岁)将任知古贬为江夏县令、狄仁杰贬为彭泽
县令。流放裴⾏本⾄岭南。)
《旧唐书卷⼋⼗九•列传第三⼗五》:“俄⽽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本等七⼈被构陷当
死,则天谓公卿⽈:“古⼈以杀⽌杀,我今以恩⽌杀。就群公乞知古等,赐以再⽣,各授以官,伫申
来效。”俊⾂、张知默等⼜抗表请申⼤法,则天不许之。俊⾂乃独引⾏本,重验前罪,奏⽈:“⾏本潜
⾏悖逆,告张知蹇与庐陵王反不实,罪当处斩。”有功驳奏⽈:“俊⾂乖明主再⽣之赐,亏圣⼈恩信之
道。为⾂虽当嫉恶,然事君必将顺其美。”⾏本竟以免死。”
(不久,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本等七⼈(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本、司农卿裴宣礼、前
⽂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被酷吏构罪陷害,按罪名当处死刑。武则天对公卿
说:“古⼈以杀⽌杀,我今以恩⽌杀,各位公卿为知古等求情,我赐他们第⼆次⽣命,各⾃都授予官职,等他们
明⽩⽽为朝廷效⼒。”来俊⾂、张知默等⼜不听从,请求以⼤法加罪,武则天不同意,来俊⾂就单对裴⾏本,复
查他以前的罪证,上奏道:“裴⾏本私下⼲着叛逆勾当,告张知謇与庐陵王谋反⼀事不实,罪当处斩。”徐有功反
驳来俊⾂上奏道:“来俊⾂违背英明君主有使⾂下再⽣的恩惠,损害了圣⼈的恩信之道。作为⾂⼦虽然应当嫉
恶,但是事奉君主⼀定要顺应君主的美好愿望。”裴⾏本因徐有功的⼒辩⽽免死(武则天天授三年⼀⽉庚午初
三,692年1⽉27⽇)。)
《旧唐书卷九⼗三•列传第三⼗九》:“未⼏,为来俊⾂诬构下狱。时⼀问即承者例得减死,来俊
⾂逼协仁杰,令⼀问承反。仁杰叹⽈:“⼤周⾰命,万物唯新,唐朝旧⾂,⽢从诛戮。反是实!”俊⾂
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尚书必得减死。德寿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
杰⽈:“若何牵之?”德寿⽈:“尚书为春官时,执柔任其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皇天后⼟,
遣仁杰⾏此事!”以头触柱,流⾎被⾯,德寿惧⽽谢焉。
既承反,所司但待⽇⾏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冤,置绵⾐中,谓德寿
⽈:“时⽅热,请付家⼈去其绵。”德寿不之察。仁杰⼦光远得书,持以告变。则天召见,览之⽽问俊
⾂。俊⾂⽈:“仁档不免冠带,寝处甚安,何由伏罪?”则天使⼈视之,俊⾂遽命仁杰⼱带⽽见使者。
乃令德寿代仁杰作谢死表,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谓⽈:“承反何也?”对⽈:“向若不承反,已
死于鞭笞矣。”“何为作谢死表?”⽈“⾂⽆此表。”⽰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贬彭泽令。
武承嗣屡奏请诛之,则天⽈:“朕好⽣恶杀,志在恤刑。涣汗已⾏,不可更返。””
(不久,狄仁杰为来俊⾂诬构下狱。当时⼀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可以减免死罪,来俊⾂便⽤这道命令
狄仁杰认罪。狄仁杰回答说:“⼤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旧⾂,⽢愿听任诛戮。谋反是事实!”来俊⾂便对
他稍加宽容。来俊⾂的属官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定能减免死罪了。我已受⼈指使,想略找⼀个升迁阶
梯,烦您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王德寿说:“尚书你从前在礼部任职时,
杨执柔担任礼部司员外⼀职,你把他牵连出来就⾏了。”狄仁杰说:“天神地神在上,竟要狄仁杰⼲这种事!”说
完⼀头撞在柱⼦上,⾎流满⾯;王德寿害怕因⽽向他道歉。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待判罪执⾏刑罚,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求守者得笔砚,从被⼦上撕下⼀
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绵⾐⾥⾯,对王德寿说:“天⽓热了,请将绵⾐交给我家⾥⼈撤去丝绵。”王德寿不之
察。狄仁杰的⼉⼦狄光远得到帛书,拿着去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得到太后召见,武则天看了帛书,质问来俊
⾂,他回答说:“狄仁杰等⼊狱后,我未曾剥夺他们的头⼱和腰带,⽣活很安适,假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
反?”武则天使⼈前往查看,来俊⾂临时发给狄仁杰等头⼱腰带让使者验看。来俊⾂⼜令王德寿代仁杰伪造狄仁
杰等的谢死罪表,让使者上奏太后。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道:“你承认谋反,为什么?”回答说:“不承认,便
已经死于严刑拷打了。”太后说:“为何作谢死罪表?”回答说:“⾂⽆此表。”太后出⽰所上的奏表,才知道是伪造
的。故得免死。贬彭泽令(武则天天授三年⼀⽉庚午初三,692年1⽉27⽇)。
武承嗣仍坚持请求处死狄仁杰,武则天⽈:“朕爱惜⽣命,不好杀戮,⼀贯慎⽤刑法。免死诏令已下,不可
追回了(新唐书云:“时同被诬者凤阁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贷。御史霍献可以⾸叩殿陛苦争,欲必杀仁杰等,
乃贬仁杰彭泽令,⾢⼈为置⽣祠(御史霍献可⽤头叩⾦殿⽟阶苦苦⼒争,要⼀定杀掉狄仁杰等,于是贬谪狄仁
杰为彭泽令,彭泽⾢⼈为仁杰⽴长⽣祠)。”)。”通鉴云:“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于太后
⽈:“陛下不杀裴宣礼,⾂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流沾地,以⽰为⼈⾂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
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对太后说:“陛
下不杀崔宣礼,我请求死在陛下眼前。”他⼀头撞在宫殿台阶上,流⾎浸湿地⾯,⽤以表⽰作⾂下的不袒护⾃⼰
的亲戚。太后都不听从。霍献可时常⽤绿帛包扎伤⼝,略为显露于帽⼦下⾯,希望太后看见认为他忠诚)。
”)。)
《旧唐书卷⼀百九⼗⼀•列传第⼀百三⼗六•酷吏上》:“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
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昌左丞卢献等六⼈,并为其罗告。俊⾂
既以族⼈家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降敕,⼀问即承,同⾸例得减死。及胁仁杰等反,仁杰叹
⽈:“⼤周⾰命,万物惟新,唐朝旧⾂,⽢从诛戮。反是实。”俊⾂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
⽈:“尚书事已尔,得减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
⽈:“若之何?”德寿⽈:“尚书昔在春官时,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仁杰⽈:“皇天后⼟,遣
狄仁杰⾏此事!”以头触柱,⾎流被⾯,德寿惧⽽⽌焉。
仁杰既承反,有司但待报⾏刑,不复严备。仁杰得凭守者求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
绵⾐,遣谓德寿⽈:“时⽅热,请付家⼈去其绵。”德寿不复疑矣,家⼈得⾐中书,仁杰⼦光远持之称
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愕然,召问俊⾂⽈:“卿⾔仁杰等承反,今⼦弟讼冤,何故也?”俊⾂⽈:“此
等何能⾃伏其罪!⾂寝处甚安,亦不去其⼱带。”则天令通事舍⼈周綝视之。俊⾂遽令狱卒令假仁杰
等⼱带,⾏⽴于西,命綝视之。綝惧俊⾂,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已。俊⾂令綝少留,附进状,乃
令判官妄为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进之。
凤阁侍郎乐思晦男年⼋九岁,其家已族,宜⾪于司农,上变,得召见,⾔“俊⾂苛毒,愿陛下假
条反状以付之,⽆⼤⼩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仁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不承
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何谓作谢死表?”仁杰⽈:“⽆。”因以表⽰之,乃知其代署,遂出
此六家。”
(如意元年,地官尚书狄仁杰、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昌
左丞卢献等六⼈,为来俊⾂诬构下狱。来俊⾂既以族⼈家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降敕,⼀经审问即承认谋
反的⼈可以减免死罪。来俊⾂便⽤这道命令狄仁杰认罪。狄仁杰回答说:“⼤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
旧⾂,⽢愿听任诛戮。谋反是事实!”来俊⾂便对他稍加宽容。来俊⾂的属官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定能
减免死罪了。我已受⼈指使,想略找⼀个升迁阶梯,烦您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为什么要我这样
做呢?”王德寿说:“尚书你从前在礼部任职时,杨执柔担任礼部司员外⼀职,你把他牵连出来就⾏了。”说完⼀
头撞在柱⼦上,⾎流满⾯;王德寿害怕因⽽向他道歉。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待判罪执⾏刑罚,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求守者得笔砚,从被⼦上撕下⼀
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绵⾐⾥⾯,对王德寿说:“天⽓热了,请将绵⾐交给我家⾥⼈撤去丝绵。”德寿不复疑
矣,家⼈得到帛书,狄仁杰的⼉⼦狄光远持之称变,拿着去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得到太后召见,武则天看了
帛书愕然,质问来俊⾂⽈:“你说仁杰等已承认犯了反判罪,那为什么今天他⼉⼦⼜来诉冤呢?”来俊⾂⽈:“假
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反!我安排他们的⽣活很安适,未曾剥夺他们的头⼱和腰带。”武则天令通事舍⼈周
綝前往查看。来俊⾂令狱卒临时发给狄仁杰等头⼱腰带带,让他们站在西侧,叫周綝视察。周綝惧怕来俊⾂,
不敢正眼观看,只是往相反的东⾯望着,对来俊⾂唯唯诺诺罢了。来俊⾂令周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伪造
狄仁杰等的谢死罪表,让周綝代署上奏太后。
凤阁侍郎乐思晦的⼉⼦才⼋九岁,遭来俊⾂夷灭全家(思晦死见上年),被籍没⼊司农寺为奴,要求上告特
别情况,获得太后召见,⾔“来俊⾂苛刻狠毒,希望陛下把那些称反叛的假状⼦⼀⼀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不论哪
⼀个⼤⼩官员所有状⼦都是⼀个样。”太后听后稍有醒悟,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承认谋反,为什么?”回答
说:“不承认,便已经死于严刑拷打了。”太后说:“为何作谢死罪表?”回答说:“没有。”太后出⽰所上的奏表,
才知道是伪造的,狄仁杰等六⼈得以免死(武则天天授三年⼀⽉庚午初三,692年1⽉27⽇)。)
《新唐书卷⼀百三⼗六•列传第四⼗⼋》:“会来俊⾂构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狱,将抵死,
敕峤与⼤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知其枉不申,是谓见
义不为者。”卒与⼆⼈列其枉,忤武后旨,出为润州司马。”
(那时来俊⾂诬陷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三⼈下了狱,将要被诛杀了。武后令李峤与⼤理少卿张德裕、
侍御史刘宪复核。张德裕⼼中明⽩他们是冤枉的,但因怕得罪来俊⾂,不敢提出不同看法。李峤说:“哪有明知
他被枉判⽽不为之申明的呢?孔⼦说:‘见义⽽不为,是为⽆勇。’”于是和他们两⼈⼀同列举事实,说明其冤
枉(武则天天授三年⼀⽉庚午初三,692年1⽉27⽇)。为此⽽违背了武后的旨意,被贬出为润州司马(通鉴胡
三省注:按峤平⽣⾏事,恐不能如此)。)
《旧唐书卷⼀百九⼗⼀•列传第⼀百三⼗六•酷吏上》:“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夫、左台侍御史。
元礼复教⽈:“在上知侯⼤⽆宅,倘以诸役官宅见借,可辞谢⽽不受。在上必问所由,即奏云:‘诸反
逆⼈,⾂恶其名,不愿坐其宅。’”则天复⼤悦,恩泽甚优。
思⽌既按制狱,苛酷⽇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急认⽩司马,不然,即吃孟青。”⽩司马者,
洛阳有坂号⽩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思⽌闾巷庸奴,常以此谓诸囚
也。元忠辞⽓不屈,思⽌怒⽽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我薄命,如乘恶驴坠,脚为镫所挂,被拖
曳。”思⽌⼤怒,⼜曳之⽈:“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侯思⽌,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数
轻重。如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为抑我承反。奈何尔佩服硃紫,亲衔天命,不⾏正直之
事,乃⾔⽩司马、孟青,是何⾔也!⾮魏元忠,⽆⼈抑教。”思⽌惊起悚怍,⽈:“思⽌死罪,幸蒙中
丞教。”引上床坐⽽问之。元忠徐就坐⾃若,思⽌⾔竟不正。时⼈效之,以为谈谑之资。侍御史霍献
可笑之,思⽌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我已⽤之,卿笑何也?”献可具以其⾔奏,则天亦⼤笑。”
(天授三年(692年),乃拜侯思⽌为朝散⼤夫、左台侍御史。⾼元礼复教⽈:“皇上知你⽆宅第,必定要将
没收来的私宅赐给你⼀所,你可拒绝不受。皇上必问原因,你就回答说,‘我憎恶叛逆的⼈,不愿意居住他们的
住宅。’”侯思⽌依计⽽⾏,武则天听后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很忠⼼,就对他更加重⽤。
侯思⽌既按制狱,苛酷⽇甚。曾经审理中丞魏元忠的案⼦,⽈:“快说谁是⽩司马,不然让你吃孟青棒。”⽩
司马,是洛阳附近的北邙⼭⽩司马坂。孟青,将军姓孟名青棒,即杀琅邪王李冲的⼈(意思是不招供便⽤棒
打。侯思⽌认“坂”为“反”,误以为曾有⽩司马造反!孟青棒曾为⼀将,这侯思⽌还以为是⼀个兵器)。侯思正本
来是个巷⾥中的平庸之辈,因⽽常⽤这样的话去威逼囚徒。魏元忠正直不屈,顶撞了侯思⽌,被倒吊起来。魏
元忠徐起⽈:“我命运不好,譬如从驴背上掉下来,脚挂在⾜镫上,被驴拉着⾛。”侯思⽌愈加发怒,命令接着拖
他,说:“你竟敢抗拒皇上派来的⼈,我要上奏把你杀了。”魏元忠说:“侯思⽌,你如今是国家的御史,必须知
道礼仪轻重。你这样需要魏元忠的头颅,为什么不拿锯来截去,何必让我承认谋反呢!奈何你⾝上穿着朝廷的
官服,拿了皇上的⼿令,不⾏正直之事,可是⼀⼝⼀个⽩司马,⼀⼝⼀个孟青棒,这是什么语⾔!若不是我魏元
忠,没⼈对你指教。”侯思⽌惊慌地站起来,害怕⽽⼜惭愧地说:“思⽌该死,我真的不明⽩这些,多亏了中丞的
指教。”于是把他领上台阶,按照礼数坐下来问话。魏元忠也慢慢地坐下,神情⾃若,侯思⽌这个⼈乡⾳很重,
⼝齿不清。时⼈效之,以为谈谑之资。侍御史霍献可听到后忍不住笑了,侯思⽌便把他告到了武则天,武则天
很⽣⽓,对霍献可说道:“我已经⽤他了,你为什么还要笑他呢?”霍献可具以其⾔奏,武则天也不禁⼤笑。)
《新唐书卷⼀百四•列传第⼗六》:“出为潞州刺史。俊⾂诬以反,流藤州,久得还。⾃筮死⽇,
豫具棺敛,如⾔卒桂阳。有诏州县护丧还乡⾥,赠济州刺史,谥⽈昭。
武后尝问嗣真储贰事,对⽈:“程婴、杵⾅存赵⽒孤,古⼈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龙初,赠
御史⼤夫。
所撰述尤多。”
(后来李嗣真出任为潞州刺史。来俊⾂诬陷他谋反,于是被流放到藤州(武则天天授三年⼀⽉庚午初
三,692年1⽉27⽇),久后才得以返还。李嗣真⾃⼰占筮出去世的⽇期,预先准备好棺材等物,后来果如其⾔
死于桂阳。有诏书命州县护丧返回乡⾥,赠予济州刺史,谥为昭。
武后曾问李嗣真储君之事,李嗣真回答说“:程婴、公孙杵⾅保存赵⽒孤⼉,古⼈赞美其⾏为。”武后明⽩过
来,中宗才得以安稳其位。神龙初年,赠予御史⼤夫。
李嗣真所撰述之作极多。)
《新唐书卷⼀百廿五•列传第三⼗七》:“时选举滥甚,乃上疏⽈:
⽐观举荐,类不以才,驰声假誉,互相推引,⾮所谓报国求贤者也。古之取⼠,考素⾏之原,询
乡⾢之誉,崇礼让,明节义,以敦朴为先,雕⽂为后。故⼈崇劝让,⼠去轻浮,以计贡贤愚为州之荣
辱。昔李陵降⽽陇西溯,⼲⽊隐⽽西河美。名胜于利,则偷竞⽇销;利胜于名,则贪暴滋煽。盖冀缺
以礼让升⽽晋⼈知礼,⽂翁以经术教⽽蜀⼠多儒。未有上好⽽下不从者也。汉世求⼠,必观其⾏,故
⼠有⾃脩,为闾⾥推举,然后府寺交辟。魏取放达,晋先门阀,梁、陈荐⼠特尚词赋。隋⽂帝纳李谔
之⾔,诏禁⽂章浮词,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表不典实得罪,由是风俗稍改。炀帝始置进⼠等科,后⽣
复相驰竞,赴速趋时,缉缀⼩⽂,名⽈策学,不指实为本,⽽以浮虚为贵。
⽅今举⼠,尤乖其本。明诏⽅下,固已驱驰府寺之廷,出⼊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
俗号举⼈皆称觅举。觅者,⾃求也,⾮彼知之义。是以耿介之⼠羞于⾃拔,循常⼩⼈弃疏取附。愿陛
下降明制,颁峻科,断⽆当之游⾔,收实⽤之良策,⽂试效官,武阅守御。昔吴起将战,左右进剑,
吴⼦辞之,诸葛亮临阵,不亲戎服,盖不取⼸剑之⽤也。汉武帝闻司马相如之⽂,恨不与同时,及其
⾄也,终不处以公卿之位,⾮所任故也。汉法,所举之主,终⾝保任。杨雄之坐⽥仪,成⼦之得魏
相,赏罚之令⾏,则请谒之⼼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销。请宽年限,以容简汰,不实免官,得
⼈加赏,⾃然见贤不隐,贪禄不专矣。”
(时选举滥甚,,薛谦光乃上疏⽈(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
⽐观举荐,类不以才,驰声假誉,互相推引,⾮所谓报国求贤者也。古之取⼠,考素⾏之原,询乡⾢之誉,
崇礼让,明节义,以敦朴为先,雕⽂为后。故⼈崇劝让,⼠去轻浮,以计贡贤愚为州之荣辱。昔李陵降⽽陇西
溯,⼲⽊隐⽽西河美。名胜于利,则偷竞⽇销;利胜于名,则贪暴滋煽。盖冀缺以礼让升⽽晋⼈知礼,⽂翁以
经术教⽽蜀⼠多儒。未有上好⽽下不从者也。汉世求⼠,必观其⾏,故⼠有⾃脩,为闾⾥推举,然后府寺交
辟。魏取放达,晋先门阀,梁、陈荐⼠特尚词赋。隋⽂帝纳李谔之⾔,诏禁⽂章浮词,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表
不典实得罪,由是风俗稍改。炀帝始置进⼠等科,后⽣复相驰竞,赴速趋时,缉缀⼩⽂,名⽈策学,不指实为
本,⽽以浮虚为贵。
⽅今举⼠,尤乖其本。明诏⽅下,固已驱驰府寺之廷,出⼊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皆
称觅举。觅者,⾃求也,⾮彼知之义。是以耿介之⼠羞于⾃拔,循常⼩⼈弃疏取附。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
断⽆当之游⾔,收实⽤之良策,⽂试效官,武阅守御。昔吴起将战,左右进剑,吴⼦辞之,诸葛亮临阵,不亲
戎服,盖不取⼸剑之⽤也。汉武帝闻司马相如之⽂,恨不与同时,及其⾄也,终不处以公卿之位,⾮所任故
也。汉法,所举之主,终⾝保任。杨雄之坐⽥仪,成⼦之得魏相,赏罚之令⾏,则请谒之⼼绝;退让之义著,
则贪竞之路销。请宽年限,以容简汰,不实免官,得⼈加赏,⾃然见贤不隐,贪禄不专矣。)
《旧唐书卷⼀百五•列传第五⼗⼀》:“天授中,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谦光上疏⽈:
⾂闻国以得贤为宝,⾂以举⼠为忠。是以⼦⽪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
托政于王猛。⼦产受国⼈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
益信,⾏间毁⽽⽆疑,此由默⽽识之,委⽽察之深也。⾄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叔,韩信
⽆闻于项⽒,⽑遂不齿于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主受不肖之⼠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
尧资⼋元⽽庶绩其理,周任⼗乱⽽天下和平。由是⾔之,则⼠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也。何者?⽐
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之⼩计,忘⾂⼦之⼤猷,⾮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
翘翘之望者也。
⾂窃窥古之取⼠,实异于今。先观名⾏之源,考其乡⾢之誉,崇礼让以励⼰,明节义以标信,以
敦朴为先最,以雕⾍为后科。故⼈崇劝让之风,⼠去轻浮之⾏。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难进易
退之规。众议以定其⾼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之彰露,亦乡⼈之
厚颜。是以李陵降⽽陇西惭,⼲⽊隐⽽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
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知礼;⽂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多儒。燕
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室。由是⾔之,未有上之所好⽽下不从其化者也。⾃七国
之季,虽杂纵横,⽽汉代求才,犹征百⾏。是以礼节之⼠,敏德⾃修,闾⾥推⾼,然后为府寺所辟。
魏⽒取⼈,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祗重门资。奖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雅爱
属词;陈⽒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为务。逮⾄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
论之于⽂帝⽈:“魏之三祖,更好⽂词,忽君⼈之⼤道,好雕⾍之⼩艺。连篇累牍,不出⽉露之形;
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朝廷以兹擢⼠,故⽂笔⽇烦,其政⽇乱”。帝纳李谔之
策,由是下制禁断⽂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
炀帝嗣兴,⼜变前法,置进⼠等科。于是后⽣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名
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于故⾮;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有乖事
实。乡议决⼩⼈之笔,⾏修⽆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
攵,驱驰府寺之门,出⼊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
⼈,皆称觅举。觅为⾃求之称,未是⼈知之辞。察其⾏⽽度其材,则⼈品于兹见矣。徇⼰之⼼切,则
⾄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秦嘉耿耿
之辞。纵不能抑⼰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戋戋,荣⾼物表,校量
其⼴狭也!是以耿介之⼠,羞⾃拔⽽致其辞;循常之⼈,舍其疏⽽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
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谦逊者亦⽆贪贿之累。
⾃⾮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
门,邀仕者皆戚施⽽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今访乡
闾之谈,唯祇归于⾥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窃级,假其不义之赂,
则是⽆犯乡闾。岂得⽐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之赏拔,夏少名⾼,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
减,便即告归。以此收⼈,恐乖事实。何者?乐⼴假笔于潘岳,灵运词⾼于穆之,平津⽂劣于长卿,
⼦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
亦⽆裨附之益。由此⾔之,不可⼀概⽽取也。⾄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捴;周勃虽雄,乏
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戏下之军,亦⽆免主之效。⽃将长于摧
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泉聚⽶,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解。⼋难之谋设,⾼祖追
惭于郦⽣;九拒之计穷,公输息⼼于伐宋。谋将不长于⼸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表,妄
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校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
之良策,不取⽆稽之说,必求忠告之⾔。⽂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观⾏,终亦循名责
实,⾃然侥幸滥吹之伍,⽆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多其⾏,拙于
⽂⽽⼯于事。”此取⼈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经国之⼤才,为军
锋之⽖⽛,作词赋之标准。⾃可试凌云之策,练穿札之⼯,承上命⽽赋《⽢泉》,禀中军⽽令赴敌,
既有随才之任,必⽆负乘之忧。⾂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夫提⿎挥桴,临难决疑,此
将事也。⼀剑之任,⾮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
当。此岂⼸⽮之⽤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武帝⽈:“恨不得与此⼈同时。”及相如⾄,终于⽂园
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保任。杨雄之坐⽥仪,责其冒荐;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
令⾏,则请谒之⼼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然朝廷⽆争禄之⼈,选司有谦捴之⼠。仍请宽
⽴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事,以别是⾮。不实免王丹之官,得⼈
加翟璜之赏,⾃然见贤不隐,⾷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硃穆,势不云远。有称职
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然举得贤⾏,则君⼦之道长矣。”
(天授中(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薛谦光为左补阙,时选举颇滥,薛谦光上疏⽈:
⾂闻国以得贤为宝,⾂以举⼠为忠。是以⼦⽪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
猛。⼦产受国⼈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益信,⾏间毁⽽⽆
疑,此由默⽽识之,委⽽察之深也。⾄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叔,韩信⽆闻于项⽒,⽑遂不齿于平
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主受不肖之⼠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元⽽庶绩其理,周任⼗乱⽽天
下和平。由是⾔之,则⼠不可不察,⽽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
润⾝之⼩计,忘⾂⼦之⼤猷,⾮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窃窥古之取⼠,实异于今。先观名⾏之源,考其乡⾢之誉,崇礼让以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
最,以雕⾍为后科。故⼈崇劝让之风,⼠去轻浮之⾏。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
其⾼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之彰露,亦乡⼈之厚颜。是以李陵降⽽陇西
惭,⼲⽊隐⽽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
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知礼;⽂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多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
室。由是⾔之,未有上之所好⽽下不从其化者也。⾃七国之季,虽杂纵横,⽽汉代求才,犹征百⾏。是以礼节
之⼠,敏德⾃修,闾⾥推⾼,然后为府寺所辟。魏⽒取⼈,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祗重门资。奖为⼈求官之
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雅爱属词;陈⽒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为务。逮⾄
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帝⽈:“魏之三祖,更好⽂词,忽君⼈之⼤道,好雕⾍之⼩艺。连篇累
牍,不出⽉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朝廷以兹擢⼠,故⽂笔⽇烦,其政⽇乱”。帝纳
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炀
帝嗣兴,⼜变前法,置进⼠等科。于是后⽣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名之策学,不
以指实为本,⽽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虽渐⾰于故⾮;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有乖事实。乡议决
⼩⼈之笔,⾏修⽆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
出⼊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皆称觅举。觅为⾃求之
称,未是⼈知之辞。察其⾏⽽度其材,则⼈品于兹见矣。徇⼰之⼼切,则⾄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
风薄。是知府命虽⾼,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
与夫⽩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戋戋,荣⾼物表,校量其⼴狭也!是以耿介之⼠,羞⾃拔⽽致其辞;循常之
⼈,舍其疏⽽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
有竞利之⼼,谦逊者亦⽆贪贿之累。⾃⾮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则怀禄者必
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
不由兹。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窃级,假其不义
之赂,则是⽆犯乡闾。岂得⽐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之赏拔,夏少名⾼,语其优劣也!
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
归。以此收⼈,恐乖事实。何者?乐⼴假笔于潘岳,灵运词⾼于穆之,平津⽂劣于长卿,⼦建笔丽于荀彧。若
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裨附之益。由此⾔之,不
可⼀概⽽取也。⾄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捴;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
失指纵之机;使萧何⼊戏下之军,亦⽆免主之效。⽃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泉聚⽶,知隗嚣之可
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解。⼋难之谋设,⾼祖追惭于郦⽣;九拒之计穷,公输息⼼于伐宋。谋将不长于⼸
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校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之良策,不
取⽆稽之说,必求忠告之⾔。⽂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观⾏,终亦循名责实,⾃然侥幸滥吹之
伍,⽆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多其⾏,拙于⽂⽽⼯于事。”此取⼈得贤之道
也。其有武艺超绝,⽂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经国之⼤才,为军锋之⽖⽛,作词赋之标准。⾃可试凌云之
策,练穿札之⼯,承上命⽽赋《⽢泉》,禀中军⽽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负乘之忧。⾂谨案吴起临战,
左右进剑,吴⼦⽈:“夫提⿎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剑之任,⾮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
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之⽤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武帝⽈:“恨不得与此⼈同
时。”及相如⾄,终于⽂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其所任故也。
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保任。杨雄之坐⽥仪,责其冒荐;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则请
谒之⼼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然朝廷⽆争禄之⼈,选司有谦捴之⼠。仍请宽⽴年限,容其采访简
汰,堪⽤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事,以别是⾮。不实免王丹之官,得⼈加翟璜之赏,⾃然见贤不隐,
⾷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硃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
然举得贤⾏,则君⼦之道长矣。)
《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亥,杀右卫⼤将军泉献诚。”
(⼄亥(初⼋,692年2⽉1⽇),杀右卫⼤将军泉献诚。)
《新唐书卷⼀百⼀⼗•列传第三⼗五•诸夷蕃将》:“献诚,天授中以右卫⼤将军兼⽻林卫。武后尝
出⾦币,命宰相、南北⽛群⾂举善射五辈,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钤卫⼤将军薛
吐摩⽀,摩⽀固辞。献成⽈:“陛下择善射者,然皆⾮华⼈。⾂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后嘉
纳。
来俊⾂尝求货,献诚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后后知其冤,赠右⽻林卫⼤将军,以礼改葬。
”
(泉献诚(渊盖献诚,莫离⽀献诚),天授中以右卫⼤将军兼⽻林卫。武后(武则天)拿出⾦银财宝,命令
选拔宰相、南北衙禁卫军优秀射⼿五⼈⽐赛射箭,中者以赐。内史张光辅举献诚,泉献诚让给右⽟钤卫⼤将军
薛吐摩⽀(通鉴作“薛咄摩”),薛吐摩⽀⼜让给泉献诚。泉献诚便上奏说:“陛下命令选拔优秀射⼿,现在选出
的多不是汉族官员,我恐怕四夷轻视汉⼈(泉献诚,⾼丽泉男⽣之⼦。薛咄摩,薛延陀之种,故云然),请求
停⽌这次⽐赛。”太后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
......下⽂含有敏感词,删去
《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庚⾠,司刑卿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庚⾠(⼗三,692年2⽉6⽇),司刑卿李游道任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新唐书卷⼀百三⼗•列传第四⼗⼆》:“如意元年,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武后营神都,昭德规创⽂昌台及定⿍、上东诸门,标置华壮。洛有⼆桥,司农卿韦机徙其⼀直长
夏门,民利之,其⼀桥废,省巨万计。然洛⽔岁淙啮之,缮者告劳。昭德始累⽯代柱,锐其前,厮杀
暴涛,⽔不能怒,⾃是⽆患。”
(如意元年(⼋⽉戊寅⼗五,692年10⽉1⽇),李昭德授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武后营建神都洛阳,李昭德规划创建⽂昌台及定⿍、上东诸门,规模华丽壮观(通鉴云:“初,隋炀帝作东
都,⽆外城,仅有短垣⽽已,⾄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当初,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605年三⽉),没有
外城,只有低矮的围墙⽽已。这时候,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营建东都外城)。”)。洛⽔有两座桥,司农卿韦
机迁建其中的⼀座正对着长夏门,民众便利,废置另外⼀座桥,节省开⽀数以万计。然⽽洛⽔每年冲注侵蚀这
座桥,修缮者不胜⾟劳。李昭德开始垒起⽯头代替⽯柱,迎⽔的⼀⾯砌成尖形,以劈开汹涌的波浪,⽔不能猛
冲桥墩,从此桥不再损坏。)
《新唐书卷⼆百三⼗七•列传第⼀百四⼗六上•西域上》:“龙朔后,⽩兰、舂桑及⽩狗羌为吐蕃所
⾂,籍其兵为前驱。⽩狗与东会州接,胜兵才千⼈。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万,以其地为
朝、吴、浮、归⼗州,散居灵、夏间。”
(龙朔以后,⽩兰、舂桑及⽩狗羌被吐蕃所⾂服,吐蕃在战争中⽤其兵为前驱。⽩狗与东会州相接,强兵才
千⼈。居于西北的,天授年间(武则天天授三年⼆⽉⼰亥初三,692年2⽉25⽇)归附,有⼆⼗万户,列其地为
朝州、吴州、浮州、归州等⼗州,⼈民散居于灵州、夏州之间。)
《新唐书卷四•本纪第四》:“⼆⽉戊午,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戊午(廿⼆,692年3⽉15⽇),秋官尚书袁智弘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三⽉,五天竺国并遣使朝贡。”
(三⽉,五个天竺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本文发布于:2023-03-11 05:27:25,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fanwen/zuowen/1678483646211352.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魏元忠.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魏元忠.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