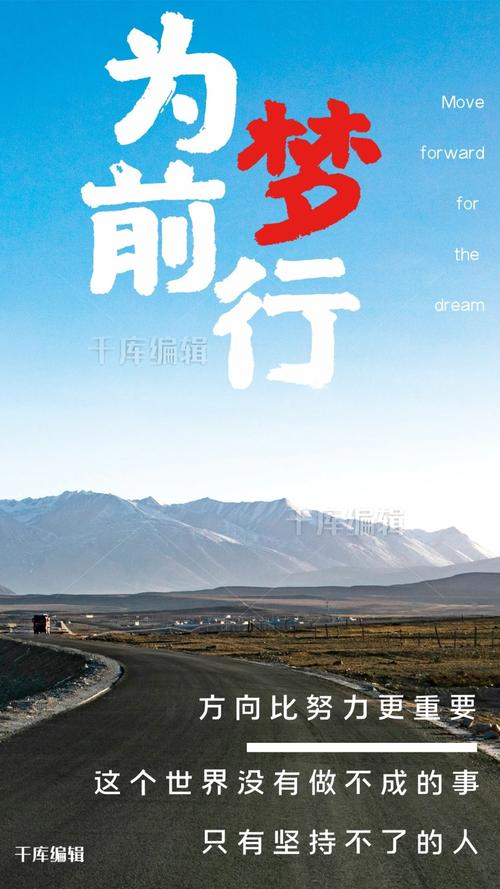
1
【小溪流向远方】草地上开着花扩句
【小溪流向远方】草地上开着花扩句
一条小溪,唱着歌流过村边。它就源自上头不远处的沙山脚下,村里人说它
是沙山的乳汁,雨季后被沙山挤压出来的。因获得了自由,这小溪便有了叮叮咚咚
的欢唱。伊茹婶住在小溪的那边。
阿郎住在小溪的这边。
每天清晨,他们俩在小溪边相遇,她在那岸,他在这岸。
伊茹婶儿,担水呀。每次阿郎先打招呼,村里懂事的孩子都先向长辈问候。
是啊,阿郎,你也担水那,小小的年纪真能干,啧啧啧。伊茹婶儿咂舌,夸赞十
三四岁的阿郎。那会儿伊茹婶三十多岁,脸白白净净,眼睛大大亮亮,是个农村中
少有的漂亮女人。
那条清清亮亮的溪水,就那么从他们中间撒着欢流过。有几块石头丢在溪水
中,供人踩着过溪,浅浅的水从石上淌过时发出汩汩的嘻闹声,似是唱着歌。石缝
间有泥鳅滑过,那阿郎便赤着脚下到溪里,捉那泥鳅。溪底的沙子翻上来,水就浊
了。那伊茹婶笑着嗔怪,这孩子,婶儿没法舀水了呢。
给,这泥鳅,给你。阿郎把捉到的筷子粗的泥鳅递向伊茹婶儿。
我也不是猫,要你这泥鳅做啥?伊茹婶站在那里,等候溪水重新变清亮,脸上
仍旧挂着清澈的笑容。
我就给你嘛。阿郎固执,把手里的泥鳅索性放进了那伊茹婶的木桶里去。获
得自由的小泥鳅,像只精灵般在那木桶里的水中钻来钻去。
格格格格,你这孩子,真是的。伊茹婶爽朗地笑着,舀完水挑上水桶就走了,水
桶里装着那条泥鳅。
阿郎望着她的背影,不知是想留住她多说会儿话,还是怎么的,在其身后轻声
说一句,我阿爸说你是个妖精!
是吗,真逗,俺勾谁的魂了?吸谁的髓了?是你阿爸没安好心眼儿吧,格格……
伊茹婶儿肩上担着水转过头,笑嘻嘻地回道。
阿爸还说,还说……你当过萨满巫女……不是好人……
那又怎么啦……你那阿爸打的啥主意俺知道,你回家问问他吧。伊茹婶说完,
2
舞蹈般地扭着她的细腰丰臀,担着水走了。
这么好看的伊茹婶儿,怎么会是妖精呢……阿郎站在那里,喃喃自语。
伊茹婶是东岸那两间土房的主人奥佬叔的媳妇。不知是因奥佬叔是个痨病鬼、
还是她小时跟随娘当过萨满巫女的原故,伊茹婶嫁过来很多年都没有生孩子。在
农村,新媳妇过门第二年便开始被人关注肚子,打问有了没有?还没消息?第二年
第三年还没有,便有人提供多种建议:去庙上吧,找喇嘛念念经;上医院吧,说是玻
璃管里给你们养孩子;报上还说有个方子??伊茹婶哪儿也没去,哪一方子都没求,
一副由它去的样子。五年八年过去了,依旧挺着瘪瘪的肚子,鼓鼓的奶子,肥肥的
臀,在村中男人流火流水的眼前晃过,让那些男人们忍不住吐一句,这骚瘪娘们
儿!“骚瘪”一词,在村里专指不下犊的母牛而言。一晃十年过去,伊茹婶头顶的
“骚瘪”桂冠依旧没能摘掉,跟比她大十多岁的的痨病鬼丈夫奥佬叔过着寂寞的
日子。倒没见她有多愁颜,依旧在村路上洒着爽朗的笑声,姑娘般地晃臀扭腰地走
过。有多少男人打过她的主意哟,上边来的干部,村中的头头脑脑,还有近村近邻
好色徒,据说有人成功过,也说没一个得手的。她就像一块肥肉,只是在男人的舌
根牙间滚来滚去但没一个能吞下她的。痨病鬼临死时还说,我老婆对我好,对我一
个心,没得说,俺知道……
阿郎挑着水走进这边的自家院子时,发现他阿爸桑布躲在院墙后头,正在偷
窥溪边东岸处。
阿郎把水倒进缸里时说一句,你不该说人家是妖精的。
回家来准备往灶锅上贴大饼子的阿爸,回过头瞟一眼儿子,怎么啦?
没怎么。阿郎闭住了小嘴巴。
默默啃完大饼子,爷儿俩各自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这时阿郎又冒出一句
说,阿爸,等奥佬叔死了,你就把伊茹婶儿娶过来,给我当娘吧!
你这孩子,胡勒勒啥呢!他阿爸喝斥。
你不是也一直很惦记她嘛!
他阿爸扔过来一只鞋子,阿郎抱着头逃门而去。嘴里还嘟囔着什么。
阿郎从小没娘,心中真的渴望哪天伊茹婶变成他的娘。其实,阿爸桑布何尝不
这么想过?也早就下过手,还没等奥佬病鬼登腿前就试过了,趁一次夜里去奥佬家
办事时大胆动手动脚,结果被伊茹婶扇了一巴掌赶出了家门。
3
那次事后没过多久,还没等奥佬叔病死,桑布他自己却先蹲进了班房。当时是
“运动”后期,时任村“贫协”(全称“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他“运动”了很
多人,有命案,村里秋后算账,抓走他判了二十年,然后丢下孤伶伶的阿郎到远方
某地劳改去了。
没几天,那痨病鬼奥佬也终于在众望所归中死去了。
出这些变故之后,来小溪边担水的阿郎和伊茹婶,神情很是凄楚,落寞,相对
无言,默默地舀水。
伊茹婶儿……就剩下你一个人了……阿郎忍不住这么说。
是啊,孩子。伊茹婶儿扬起发黑的眼眶,望了一眼阿郎,心疼着说,我还好说呢,
可你一个人,一个小孩家,这日子可咋过呀?
没事,我早就学会一人过了,他在家时也没管过我啥。往后我不上学了,去队
里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这个阿郎别看小小年纪,心中却挺有打算。
伊茹婶摇摇头,叹口气,半天无声。
这时又有泥鳅从石上滑过。
婶儿,我给你逮泥鳅,看着活泛……阿郎还要赤脚下溪。
不、不、不,千万别逮它!上次你为我逮的那条,傍晚我就把它放生了。唉,可
是我那痨病鬼,还是撇下我走了。伊茹婶望着那条如一根线般流淌的溪水,轻轻叹
气。她感觉自己的命,也犹如这条浅浅的、水没不过脚踝的小溪般的薄而苦,从上
头沙山下受挤压渗出,在荒地上寻寻觅觅、似断似续地流到这里,又七曲八拐地冲
下游探路而去,不知去往何处,全由不得自己,完全听凭于老天爷的雨量、路途的
阻隔、还有人与畜的拦截占用。
阿郎何尝不是也如这条小溪般苦命。
又过了些日子,村里出劳力就把这条小溪在其下游几十米处给拦截了,筑起
了一道小土坝。说是要搞新农村,蓄水种稻子。下来蹲点的干部说,咱北方农民不
能老啃窝窝头,也要吃雪白的大米干饭!村民底下撇嘴,上边的人一闲,就下来折
腾农民。
这么一弄,阿郎和伊茹婶挑水不大方便了。土坝里拦的水淹了他们原先挑水
的溪边,二人只好绕到更上头的流活水的地方去舀干净水。
有一天黄昏,阿郎割草回来,夏天酷热,他在岸边丢下草捆,撸掉裤子便一头
4
扎进了那一汪坝水里。他从这边岸的水深处往对岸扎猛子游,如一只水蛤蟆。自
打筑起那道拦水坝后,村中的孩童每天都在这里玩水,各个成了水精怪,当然也有
丢了性命的。
他闭住呼吸,在水底漫游着,惬意又自在,如一大泥鳅。
突然,他感觉自己撞上了一个软绵绵、滑溜溜的什么东西上。张着的嘴巴里,
似乎也咬进了一个肉嘟嘟的疙瘩。他大吃一惊,慌张地冒出水来,同时听见一个女
人在尖叫。
你这冒失鬼!往哪儿游啊?没看见一个大活人在这里洗澡呐?
是伊茹婶。
趁黄昏人少看不见,她也下到水坝里洗澡,还脱光了上边的内衣,裸露着她那
白白肥肥的大奶子,还有美丽无比的胸脯。
伊如婶儿……我……阿郎脸涨得通红。
你还挺会咬,一下子咬住了婶的奶头呢!格格格……
阿郎更是无地自容,扑通一声又扎进水里,向西岸逃命般游去。
慢点游,别呛着水!没事的,婶在逗你呢!
从身后传来伊茹婶那亲切的如母亲般的呵护声。
可岁数已有十六七的阿郎,对异性早有过分敏感的触觉,并容易产生幻想。从
此,他牢牢记住了伊如婶那白白肥肥的裸奶和美丽诱人的胸脯,更不能忘记撞进
他嘴里那颗滑溜溜的奶头。
这时间一晃,又过了十来年。这年头打发日子就是弹指间的事。
伊茹婶始终没再改嫁,丈夫奥佬死后一直独自一人在溪岸老房里熬着日子。
而这阿郎呢,都快三十岁了,也始终没讨到个媳妇,成了老光棍一条,在溪西
岸一人生活。这跟他那还在劳改的父亲没留下好名声不无关系,提亲的人一听桑
布的儿子便摇头离去。另外一因是改革开放后,村里女孩们一窝风全涌到城里去
了,打工的打工,三陪的三陪。现在农村里没有女孩,后来男孩也没有了,去城里边
打工边追女孩。只留守些中老年男人女人在墙角屋前晒太阳,穿着从城里捎来的
花哩胡哨的衣裤,有的眼上还戴个墨镜,互相攀比其丫头儿子如何如何的。阿郎也
出去打过工,包工头扣薪,打一架一赌气便跑回家来,继续刨他的地,称自己不是
去城里打工的料儿。
5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讨不到老婆,就被人瞧不起,加上受其父恶
名所累,遭村民冷眼,致使其性格渐渐变得内向、抑郁,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成天
萎萎靡靡蔫蔫巴巴的没神样子。
初冬的一个傍晚,阿郎干活儿回来刚进院,就听见从小溪东岸边传来伊茹婶
喊救命的尖叫声。
他丢下手中的东西就跑出去。
只见伊茹婶正在水坝东岸一个冰窟窿里挣扎。原来她赶自家的小牛犊来饮水,
调皮的牛犊不听话要逃,一下把她拽进了饮水的冰窟窿里。
初冬的水坝水面已结了一层冰,当阿郎风一样从冰面上跑过去时,那层薄冰
面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散射状地冰裂开去,从缝里涌出水。但阿郎脚步飞快,冰
裂缝追不到他的脚下,只从他身后凹陷着尾随。他如一条步伐轻灵的狗,不顾一切
地穿越着,当他赶到东岸时,那伊茹婶已精疲力竭正往冰窟水里下沉。他慌了,一
伸手就揪住她的头发和衣领往上拎,接着拼了命拉拽。可水浸透伊茹婶棉衣,变得
死沉死沉,怎么也拉不上来,索性,他“扑通”一声跳进冰窟里,从下往上托举那
个变得无比沉重的伊茹婶儿。冰水刺骨般寒冷,水淹到他脖子处,碎冰碴割得他脖
子渗出血,当拼尽气力把伊茹婶推上岸时,他自己也已经嘴唇发紫全身冻僵,快不
行了。零下二十来度,又是在冰窟冰水里,感觉身上的血都快凝固了。他把半昏迷
的伊茹婶背回她家里,弄了火,见她缓过来就说,婶儿,你快换衣服,我也回家换一
下,以后到冰窟边可千万当心啊。说完,正要离开时伊茹婶就叫住了他,并撑着身
子翻箱子,随后扔过来她丈夫奥佬叔穿过的棉衣棉裤说,就在这儿换了吧,外边太
冷,你这么着走到不了家就冻僵的。
阿郎迟疑了一下,还是听话地接过衣服走到外屋换下,再说他就是回自个儿
家也无别的棉衣可换。这时伊茹婶儿也已换了衣服,走出来张罗着烧火做饭,嘴里
说,今晚你就留在我家吃饭吧,婶儿给你做点好吃的,感谢你救命之恩。
伊茹婶儿不由分说杀了一只鸡,还烫了一壶酒。
不怎么会喝酒的阿郎,一高兴便喝醉了,烂醉如泥地躺在伊茹婶的热炕头上
睡过去。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那伊茹婶也赤裸着身子,和自己同睡在
一个被窝里。
他想爬起来跑,却被伊茹婶那只温柔的手按住了。
6
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他脑袋嗡的一下,浑身的血液也顿时热起来。在
膨胀的下身子刺激下,他的胆子也随着壮大,一转身就抱住了那个梦寐以求的美
丽无比的白白胴体,如一头初见腥的猛兽。
轻一点,傻孩子。伊茹婶也似乎中了电般呻吟着哼叫。
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他空有男人的蛮力,却头一次睡女人,不知道怎么弄法,
手忙脚乱的,稀哩糊涂搞不清哪儿是哪儿,辨不得山在哪里水在何方。还好由伊茹
婶耐心指引,就逐步贴近了生活,深入浅出,找到节奏感,头一次完成了做一个男
人的初夜大事。首尝禁果,没想到男女做事原来如此美妙无比,他就变得贪婪了,
还是伊茹婶适时制止了他。悄悄说,往后日子长呢,孩子,不要一次就吃撑了。
那阿郎哧哧地傻笑,嘴说,嗯,听娘的。
不知为什么,他居然把伊茹婶儿喊成娘,从此不再改口。
伊茹婶捂嘴乐,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拣”来的孩子。
由此,三十岁的光棍阿郎便与四十五六的寡妇伊茹婶好上了。或许是天命或
许是地缘,这两个一直在溪边相遇,隔溪相居的苦命人,经过很多年后因机缘巧合
就这么“捏”到了一起。那个寡妇伊茹,自打丈夫奥佬死后真没沾过任何男人,快
成一朵凋谢枯萎的花时,如今却意外得到看着长大的邻居大男孩儿深爱,有一种
重新获得生命和再次焕发青春的感觉。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而阿郎,
这个讨不到媳妇的老光棍,一个生活畸形而暗淡的人,则是有一种否极泰来换了
人间的感觉,也许他是从那次撞进水中洗澡的这个女人怀里开始便有了某种幻想
并朦朦胧胧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吧。
娘,这一天我好像盼了很久很久……他如是说。
是吗,你这孩子,是不是早有了坏念想呀。伊茹婶逗他,如释重负的样子。
不不,早先一直盼着你给我当娘,后来……后来……
后来想着给你当媳妇啦?唉,给你当媳妇,婶儿可是太大了……伊茹婶轻叹。
不大,不大,我觉着正好,娘。阿郎倒是心满意足。
从一个窝窝囊囊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真正的男人,这都是经历了这次质的
跨越之后发生的事情。他现在意气风发,满脸红光闪烁,果真应了那句话:男人的
自信是从女人肚皮上获取的。
一开始他们十分小心,甚至偷偷摸摸,悄悄享受着两个人突然获得的这一幸
7
福,不想让外人打扰。毕竟差着辈伦,相差着较大的岁数,在农村这是个问题。他
们的情事,就象一棵从磨盘下边七曲八扭伸出来的小草,有些畸形,带着一股稚黄
和嫩绿。村人眼睛当然是“雪亮”的,人们很快发现阿郎家的烟囱不怎么冒烟了,
半夜有人看见他翻墙而入伊茹寡妇家,一早又偷偷溜出,伊茹寡妇家的农活也全
由他包了。村里闲话就出来了,阿郎索性就认了伊茹为干妈,公开地堂而皇之出入
她家。这更激起有些好事之徒的捉奸热情,有人甚至半夜蹲守伊茹家门口,如逮偷
鸡的黄鼠狼一般。
走,娘。咱们去乡政府!
干啥呀,孩子?
登记,结婚,我娶你为妻!阿郎被村中人的举动激恼了,一字一句铿镪有力地
说。
不成啊孩子……伊茹婶摆手又摇头说,我那死鬼的族人非用唾沫水淹死我不
可!
伊茹婶胆怯了。觉得自己已经越了雷池,不能再惹众怒,何况阿郎还年轻,自
己已是土埋半截的人,不能夺走他一辈子时光。他的日子还长着呢。
名不正,言不顺,则成了“奸情”。伊茹婶很快头上顶了一个勾引年轻男人的
“狐狸精”恶名,她那两间土房在村人眼中也被视为不洁之地,那些正而经的老
男老女们路经她家时,都要啐一口才觉过瘾。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在人们白眼中不清不白地延续了几年。
娘,你给我生个儿子吧。
有一次阿郎突然这么说。
伊茹婶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轻轻说,孩子,娘不能生育,让你失望了。
为哈?
婶的娘给婶儿下过药。萨满巫女不能生小孩子。伊茹婶一脸愧疚的样子。
可你娘自己却生下了你。
我不是娘的亲生女,是花钱买的养女。
原来是这样。阿郎有些愕然。心中有一丝丝的说不出的滋味。
一阵缄默。两人相对无话。一时不知说啥好。
也好,我就跟娘一起清静地过日子。
8
咱们的日子,还继续这样过吗?片刻后,伊茹婶这样问。
当然了,咋啦娘?阿郎卷颗烟抽时回头看了一眼伊茹婶。
没什么,唉。伊茹婶不由得叹气,琢磨着说,阿郎,你是不是该成个自己的家了?
说啥呢,娘,这里就是我的家。
说完,阿郎就下地干活去了。
这一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阿郎的那个去劳改的阿爸被释放回来了。
两条间接人命案,换了他二十年岁月。父子俩如一对陌生人般相视无言。
父亲的回来,致使阿朗的生活出现了麻烦。
桑布也很快发现了儿子的异常状态,村人也适时地通报了阿郎和伊茹寡妇间
的“奸情”。曾经的不可一世的村“贫协”主席桑布,二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没
改变其脾气秉性,好像倒越发的暴烈乖戾了。他冲儿子大发雷霆,骂儿子丢人,丢
尽了祖宗的脸面,做了这种混账丢人的事情,使得他没脸在村中待了等等。
好啊,那你再回去那个劳改农场好喽!阿郎忍无可忍,回嘴,又补了一句,好像
你给祖宗们争了多少面子似的!
你个不孝儿子!我抽死你!桑布又像小时候那般操起皮鞭。
阿郎一把拽过他的鞭子,咔嚓一声撅折了鞭杆儿,扔在地上。尔后丢下一句话,
我还不愿意跟你这样……一起过呢!他咽下中间的杀人犯或劳改犯之类词,毕竟
是亲生父亲嘛,然后卷上自个儿的铺盖,就去住了伊茹婶的东下屋。伊茹婶赶他也
不走。他称自己跟伊茹婶都是自由的单身男女,要正经八百地一起过日子,别人管
不着。他明天就带着伊茹婶去登记结婚。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伊茹婶还是不肯跟他结婚,还是坚持说原
先那句话。
趁阿郎下地干活儿,他父亲桑布却主动来找伊茹寡妇谈了一次话。
你这老妖精,趁我不在家,居然勾了我儿子的魂!
想勾的话,你在家也挡不住的!你们这些烂男人,哪个不想被老娘勾住魂啊?
包括你这老色鬼!伊茹婶回敬他。
你还真是老驴吃嫩草,胃口越来越高了呢!
不,你说错了,是小牛舔老河泥!越舔越来劲儿!伊茹婶索性放下脸来反唇相
讥。她这种经历过无数男人骚扰的老寡妇,要是拉下脸来什么都不怵,什么话不敢
9
说?
好、好、你有种!明天我就告派出所你勾引良家男人,抓你个奸!
抓你个头哦!别人早试过了!你要是真那么干,我也反告你对我图谋不轨,想
强奸过我,让你再蹲个三五年笆篱子!哈哈哈……伊茹婶大笑着看他。
你!
谈判也就此僵住无法进行下去。
突然,那个桑布老汉扑通一声给伊茹寡妇跪下了。颤抖抖地求着说,姑奶奶,
求求你了,放了我儿子吧!他是我家一脉单传的男人,我要让他娶妻生子、传宗接
代啊!放手吧,姑奶奶……你实在需要个男人来陪,那就我来陪你吧――他最后居
然说出了这样话来。
你还配?滚!你这下流无耻的老东西!你以为姑奶奶是缺了男人才找你儿子的
吗?哼,回去问问你的儿子吧!
伊茹寡妇挥着扫帚疙瘩把桑布老汉赶出了家门。
晚上,阿郎从田里回到伊茹婶的东下屋,发现她神色阴郁,就问,娘,谁惹你生
气了?是不是我阿爸他来过?
没有……没事的,娘就是这个样子,今儿个天发阴,娘脸上就挂暗了――伊茹
婶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不过伊茹婶从此总显得心神悒郁的样子。
几天后,她去了一趟医院,后又去了一趟库伦庙。
回来以后,她就躺下了。病恹恹的,茶饭不思。阿郎侍候她像儿子又像丈夫。
等一天的事忙完,静下来的时候,伊茹婶就从东下屋把阿郎唤进自己屋里说
话。
阿郎,孩子,娘不是赶你走,――但你得一定要走了,不能继续在娘这儿住了。
伊茹婶的脸色十分沉静,眼睛望着别处。
阿郎一时错愕。感到措手不及。
出啥事了,娘?
没出啥事。只是娘的下身子――长了个东西。医生说,拿刀割掉,喇嘛说需去
五台山朝拜“阿日亚布鲁”佛。我想了,还是去五台山吧,娘不愿意好好的身子挨
刀割肉的……
10
怎么搞的吗?娘,这是真的吗?这……这怎么搞的吗?不成,娘,你真想去五台
山,我陪你去!
那哪成?我的事,往后你就不用再操心了,我自己一个人想清静一下。伊茹婶
说得十分果决,甚至有些冰冷。
阿郎心里不是滋味,很伤心。他不解娘怎么一下子变得换了一个人似的,叫他
不认识了。他怎么求怎么说都无动于衷,连她的身子也不让碰了,称自己身子已不
干净,那种事更不要再想了。
无奈的阿郎,只好含着眼泪搬回了自己家住。
每天一有空,阿郎就站在小溪的西岸冲东岸出神。望着那两间熟悉的土屋,心
里百味杂陈。回想着跟伊茹婶相好的这些年来的每一天每一夜,他心里不由得流
泪又流血,如刀铰般难受。
那个突然铁了心肠的伊茹婶则每晚当月亮升高的时候,也出现在小溪东岸土
坎上久坐,冲那一捧被拦住的小溪水出神,脸色就如那一汪清水般沉静,双眼一动
不动地凝视,似是要望断了那秋水。心如止水,大概说的就是她这种状态吧。
几天后,她向来看望她的阿郎说,她要回一趟娘家村,串串门,让他帮着照料
一下她的家和农田。阿郎奇怪,从来没听说伊茹婶的娘家还有啥亲戚。不过,三天
后伊茹婶也悄然回来了,跟往常一样,慵懒而又陌生,不多说一句话。淡淡地笑一
笑,淡淡地说着些不关痛痒的话,淡得如旁边的小溪水。人跟人之间,没了情的日
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又过了些时日,一心想着让儿子传宗接代的阿郎父亲桑布,不知从什么地方
领来了一位媒婆,要给阿郎介绍对象。
大嚼大撕着桑布老汉炖的母鸡,那个五十多岁的肥圆如一只滚球般的媒婆,
不说要介绍的女方情况,却扯了很多闲篇,甚至旁敲侧击地打探阿郎和伊茹寡妇
间的私情。
没那些事,都是大家瞎猜瞎传的!我儿子才三十多,伊茹寡妇都是个五十岁老
太婆,扯得上吗?我儿子人好心善,好帮别人忙,帮她种个地打个柴什么的有,其它
的没有,邻居嘛,相互帮忙是正常的。这回桑布老汉竭力保护儿子的名声,为其辩
护。
刚好从外边干活儿回来的阿郎,听见了那媒婆东拉西扯的话。
11
他进屋来就掀了桌子。
给我滚!我不娶啥老婆,用不着你来介绍女人!爷再告诉你,我跟那个老寡妇
还真有一腿,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回听明白了吧!
气得他老父亲一个劲儿跺脚骂街。那个胖脸变得如猪肝色后又成白骨色的老
媒婆,吐一句神经病,气哼哼地骑上毛驴走了。
村人知道了阿郎赶媒婆的事之后都摇头。
中邪了,你儿子肯定是中邪了!大家又把矛头对准伊茹寡妇。
狐狸精哟,被狐狸精迷住心窍啦!请喇嘛念念经,祛祛邪吧!
那个桑布老汉还真去了库伦庙上,请来了一个什么符咒黄纸,偷偷压在儿子
的枕头下边。
几天后,当阿郎去东岸土屋时,那伊菇婶轻叹一口气,仍是淡淡地说道,你赶
媒婆就赶媒婆罢了,干吗还扯上我呢?你婶儿活的不易呢,名声好坏对我虽已无所
谓,可现在咱们没那个关系了,你不能再在外边扯这个话儿啦……也不能再守我
这个五十岁病老太婆了,要不然别人真的以为你被什么勾住魂了呢……
那晚,阿郎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般蹲在伊茹婶家门口,哭了很长时间。默默地
流着泪。那伊茹婶依门框站着,瞅着他,眼神依旧那么淡淡的幽幽的,脸上毫无表
情。任其哭够后,漠然地说,回家去吧,回家睡一觉就会好的。一切都会随风飘逝
的,世上没啥东西能经得住风吹……
伊茹婶的这句话,在阿郎的耳边回响了很久很久。
又过了几天,阿郎的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自称是哪个哪个村的,名叫阿
润,她丈夫当年曾经跟阿郎一起到城里打过工,并说出名字。阿郎有些诧异,依稀
记得有这么一个工友,人挺愣,曾带头跟包工头闹过。
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我没干多久就回来了。他还好吧,还在外头打工
那?
不打了。
咋啦?
没啦。
唔……阿郎一愣,咋回事?
12
出事故啦。三年前的事了。那个叫阿润的女子,脸上已经没啥伤心的痕迹,上
下打量着阿郎,哧哧地笑了两声。
阿郎有些不自在起来。
那大妹子来找咱们是……
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有人要把俺介绍给你搞对象。那女子阿润倒很大方,性
格也挺开朗,俺当时拿不定主意,俺一个小寡妇,又带着一个小崽儿,本想守着儿
子过一辈子算啦……唉,可在农村过日子,你也知道,没有个男人别提多难了。
阿郎一时手足无措。也十分好奇地盯着那个不难看也不好看的突然冒出来的
小寡妇阿润,还有怯生生地躲在其身后的那个小崽儿,心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
你也不必为难。我是进城路过你们村,顺路来看看的,要是你没意见,也去俺
村看一看,了解了解俺是个啥人家……
谁……当初是谁要把你介绍给我?阿郎嗫嚅着问。
这……等你想定了,到俺村看看之后,俺再告诉你吧。那个女子阿润倒卖起关
子来,十分大胆地看着阿郎,又说一句,看上去,你还真是一个老实人呢。
或许为摆脱心中的落寞,或许为好奇想知道一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子情况,
以及搞清那个介绍人究竟是谁,阿郎闲着也闲着,就跟着那个阿润去了她们村子
她们家。走时,他还特意朝小溪东岸那两间土房默默望了几眼。可那里静悄悄的,
鸡不叫狗不吠,只是一溜青烟从那土房烟囱里徐徐往上冒着,直上云霄,孤高清冷
斩不断理还续的样子。
唉。阿郎轻轻叹气。
那个女子阿润则瞅着他的样子,抿嘴笑了笑。
阿润的村子可比阿郎的村子生活富裕多了。阿润的家境也不错,她那死去的
丈夫给她留下一笔抚恤费,眼下的生活还过得去。
要是你同意,我去你那儿也行,你过来也行,你来定。阿润拿茶烟招待着他,十
分殷亲。
你还没告诉我,谁向你提的亲。
你心里也没定下来行不行呢。
我有个条件,你肯定没法接受。所以……这事就算啦。阿郎犹豫一下,还是这
13
么说了。
说说看你的条件嘛。
我有个干娘,我要为她养老。如果,我过你这儿来,我就带着她来。阿郎突然
说出这么一个条件来。
格格格……那阿润听后却笑起来,我听说啦……格格格。
你还听说啥了?阿郎脸色微红。
俺要你自己说给俺听。那阿润认真起来,眼睛盯着阿郎。
于是,不知怎么的,阿郎就把自己跟伊茹婶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全告诉给
那个女子听。
倾听完阿郎的自诉,那女子阿润不由得轻叹说,你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诚实
可靠的男人呢,俺姨娘没说错你。
你姨娘?
她就是你的那位伊茹婶儿,前些日子,她来过俺这儿。
这个村子就是她的娘家呀?阿郎听后大为吃惊,心中激荡起波澜。
是啊。你们的事她都跟我讲啦。我不在乎这个。男人跟女人的事,谁能说的
清呢,只要真就好。那阿润倒是个十分明白事理的开朗女子。
阿郎一时无语。
可他的心里,流着泪。流得很痛,很痛。
离开阿润家时,阿郎给她留话说,过几天他就带着他的干娘她的姨娘,过到她
这儿来,由他养活她们两个女人。
那阿润目送阿郎时,心里似乎在说,你还不很了解你的干娘呢。
当阿郎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又有些兴奋的心情,返回村中,第一时间跑到伊
茹婶的家门口报信时,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土房门上,却挂着一把大锁。院落收拾得
干干净净,鸡猪都自由地放出来走动,窗户上遮着帘子,整个院落静悄悄的。
伊茹婶呢?她上哪儿去啦?阿郎焦灼地茫然四顾。
他蹲在门口,等了很长时间,伊茹婶始终没有回来。
一个邻居老汉后来告诉他,今早伊茹寡妇曾对他讲过,她要去五台山,朝拜阿
日亚布鲁佛。
那老汉还告诉他,伊茹寡妇一直坐在小水坝岸上,瞅着那片水发呆,神情怪怪
14
的,好像还默默流着眼泪,眼睛红红的。
娘――!你怎么能走呢?娘――你不应该走啊!
阿郎心里这么呼叫着,胸口有一股撕扯般的疼痛,眼睛往远处的山野上空张
望。后来,变得无奈的他,慢慢走到小溪岸上,也坐在伊茹婶常坐的那个小土坎上,
望着那一汪水忍不住流起泪来,嘴巴痛苦地歪扭着。嘴唇被他咬得渗出血。
他就那么坐着,久久地望着那片冰冷的秋水,默默出神默默流泪。
不由得,他就莫名地愤恨起那堵拦截这条小溪的土坝来。全因这道土坝,拦住
小溪无法自由地奔流,无法自由地歌唱,永远困在这土坝内滞留混沌。
他一直坐到夜里。月光下,望着那片被困住的溪水时,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幻
影:伊茹婶黑衣黑袍的浮现在水面上,栩栩如生,冲他似哭似笑。
顿时浑身一激灵。他“噌”地站了起来,啥也不想跑回伊茹婶院里找来一把
铁镐,开始掘扒那一拦住溪水的小土坝。只见他咬牙切齿腮帮鼓突,愤怒地挥动着
铁镐,似乎发泄着心中压抑已久的无边的仇恨。
那一汪被困的溪水,终于挣挤着往外涌,很快彻底破堤后哗啦啦地冲荡横溢
起来,没有多久就全流走流干净了。这时,变得空空的坝底,赫然出现了穿戴整齐
的伊茹婶尸体。她的脸色安详而慈和,有一种超脱的肃穆。阿郎惊呆了,似是被闪
电击中,浑身抽搐着,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灵魂被穿越的感觉……
他慢慢下到坝底,从那片黑色的污泥上,抱起了面容依然圣洁的伊茹婶,泪流
满面地轻轻低语,我知道的,你不会走的,不会走的……可你错了,你这样做,就以
为放开了我,就以为让我轻松无挂地去你的娘家村成亲吗?你错了,你大错了,
娘……
阿郎火化了伊茹婶,把她的骨灰匣就供奉在她的那两间土房内。他自己也搬
过来住在这里,陪着他的伊茹婶。从此,他似乎是失了语,不再跟村里任何人说话,
尤其见到父亲桑布时扭头就走人,形同陌路。
只有独自面对那方骨灰盒时,每顿饭在骨灰盒灵位前摆上饭菜后,他才说上
几句话:这是你爱吃的小鸡炖土豆还有荞面汤……现在谁也拆不开我们俩了,死
亡也别想,真的,我们永远在一起,娘,永远……
后来那个小寡妇阿润来找过他,他也如面对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冷冷淡淡,没
说一句话。那小寡妇阿润最后红着眼睛,失望地离去。
15
唯有他身旁的那条小溪,没有了土坝的拦截,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自由流淌,叮
叮咚咚地唱着歌,曲曲弯弯地流向远方。
流向很远的不知道的想去的地方。
[责任编辑吴佳骏]
本文发布于:2023-03-04 07:26:00,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s://www.wtabcd.cn/fanwen/zuowen/1677885961132321.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word下载地址:初尝禁果.doc
本文 PDF 下载地址:初尝禁果.pdf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